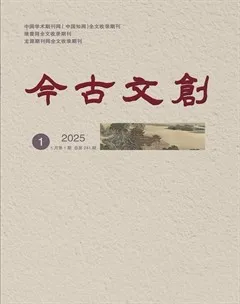游走于鄉村與城市的文學鄉愁
【摘要】田鑫的散文是關于鄉土、關于個體生命經驗的寫作,不同于傳統散文的共時性書寫,而是從歷時性的角度回望鄉土,一方面圍繞自然風土和風俗人情敘述對鄉土的懷念和擔憂,另一方面描寫了作為鄉土反面的城市中人們隱秘、焦慮的生命體驗。作者積極主動探索散文創作的邊界,將流動的生命經驗與創新的寫作方法相結合,展現出散文的新活力。
【關鍵詞】田鑫散文;鄉土經驗;城市;文學創新
近年來,寧夏青年作家田鑫在散文創作領域成績斐然,繼先前出版了散文集《大地知道誰來過》和《大地詞條》之后,2022年9月憑借《小偷》獲得了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縱觀他的散文創作,濃厚的鄉土情結成了作品底色:他的散文多以西海固村莊的自然風物和風俗人情為內容。作者將村莊、自然與個人生命相連接,以平和質樸的筆觸寫下對鄉村的懷念。在鄉村劇烈變化,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當今時代,作者無法對城市困境視而不見,其散文對城市生活的無奈和人們精神的困惑的表達契合時代的聲音。
一、“回味”淡化的鄉土經驗
鄉土生活,始終是許多現當代作家的重要書寫對象。從魯迅、沈從文、趙樹理到莫言、陳忠實等人的創作實踐,鄉土敘事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具有豐富創作資源的文學傳統。眾多作家從遙遠的鄉土中汲取創作靈感,不斷創作出富有鄉土特色的文學作品,如《故鄉》《邊城》《白鹿原》等。如今,青年作家田鑫也沿著這條道路不斷探索著,創作出許多鄉土散文,他的鄉土寫作聚焦于個人的“鄉土體驗”,既包含對“失落”鄉土的懷舊,也涵蓋對現代社會中鄉村與自然的擔憂和反思。
作者通過描寫鄉村人事變化,表達了對鄉土的懷念之情。對親人的離去、家庭關系的變化、鄉民的平凡小事等的描寫是回味和重構曾經的鄉土世界的具體表現之一,作者以悲憫之心,冷靜地書寫了眾多鄉村人物及其悲歡離合。《赤腳醫生》描寫了三爺爺堅強而又無奈的一生;《一棵核桃樹》展現了兄弟之間為了一棵樹而拋棄親情,相互爭斗的故事;《祖母》以幾次“死亡”為線索,勾勒出祖母一生的軌跡,她是村莊“變老”和城市化進程的見證者,也是村莊的縮影;《河流的幾種形式》以時間為線索,展現了祖孫三代之間的親情變遷,將家庭之“根”融入時光流逝之中,表達了對家庭的回望。
生于斯長于斯的鄉民們深受干旱的影響。《河流》寫人們因干旱為了一口水半夜三更起來去等水出來,甚至有時還會大打出手;《河流給不出的答案》寫到人一旦脫離水,便會干枯,成為一抔土,對水需求極大的人類不能沒有水的存在。在這群“被缺水缺怕了”的人們心中,河流是極為重要的,它可以滋潤大地,又可以補給人和牲畜。但河流時而干涸、時而豐腴,河流和雨水的不穩定帶給鄉民們的是不安全感,甚至是恐懼。《河流》中寫道,“村莊里就沒有下過幾次正確的雨”①,對河流的愛與恨是對無力解決的現實狀況的情感反饋,“靠天吃飯”的農民們成了作者筆下鄉土世界的重要角色之一。
時過境遷,當作者再次回到鄉村,曾經給予人們生活資源的河流,已變成他無法開口訴說的秘密。河流污染等自然生態破壞被擺在這位“返鄉者”面前,《河流給不出答案》以“我”想要了解河流的秘密為切入口,細致地展現了河流和岸、河床、樹木以及人類的關系。作者以今昔對比的手法,揭露了缺乏治理的河流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敘述者“我”層層推進對河流秘密的探尋,最后卻發現“河流呆滯無光,河面上堆積著大量的破鞋、塑料紙袋,河床發黑,散發著陣陣惡臭”,面對如此的河流,“我”已經不愿意再“興師動眾地去了解它的秘密”。“我”真的不愿嗎?“我”對變得惡臭的河流的失望,其中蘊含著“我”無法改變河流現狀的無奈以及對造成這一結果的罪魁禍首的失望和批判。其散文的生態意識契合了新時期西部散文具有的生態意蘊,體現了作家對生態危機的反思精神與呼喚和諧美好的自然生態的精神追求。
面對城市的快速發展,大量勞動人口遷往城市,留守老人去留、文化習俗消失等問題已成為鄉村面臨的幾大難題。“鄉下人進城”不僅帶走了鄉村的鮮活,還帶走了村莊日積月累沉淀下來的文化。《省略》以呼吁式的文字告訴讀者如今村莊中生與死的禮俗早已在快捷、迅速的生活中逐漸消失,出生的儀式被簡化為一通電話,死亡的葬禮被省略成哭聲、酒席。對鄉村文化的失傳的書寫體現了作者對鄉村習俗的懷念,也表達了他對鄉村民俗文化失傳現象的擔憂。鄉村的消失不僅代表的是作家個人記憶中的鄉村,更表現了現代化下中國鄉村的普遍問題。
對于定居城市的田鑫來說,鄉村已經成為一種必須不斷回望的存在。他的鄉村寫作將對村莊生活發展的思考置于對人和自然的觀察中,發現了村莊與自然、人與自然之間的異質同構關系,體現了他對鄉村的深切懷念和深刻的鄉土情懷。縱觀西部散文史的發展,這位青年作家的創作已經遠離了80年代西部散文所贊揚的邊緣文化精神。他的散文并不著眼于邊緣文化,更接近主流文化影響下的散文,它們關注中國鄉村的變遷、觀察城市的發展,弱化“邊緣文化精神”②。
二、“揣摩”現有的城市體驗
一直以來,田鑫游走于城鄉之間,其文學作品也同樣如此。已出版的兩本散文集的書寫對象存在從鄉土向城市轉移的傾向,2022年出版的《大地詞條》收錄了較多描寫城市生活和抒發對城市復雜情感的篇目。他的散文不僅濃墨重彩地書寫了個人記憶中的鄉土,而且敘述了他自己在城市中的見聞和思考。“倘若鄉村具有什么優點的話,也是因為它的反面意象——城市,反過來也同樣成立。”③作為鄉土的反面,城市成為眾多作家回望鄉土的“站點”,他的散文表達了對城市生活的憂慮,明暗交疊地體現了作者若隱若現的情感矛盾,即給予他心靈慰藉的鄉土經驗與給他提供更好生活的城市體驗之間的沖突。
文本寫到許多作為鄉土的反面意象而存在的城市景觀,如學區房、廣場、街道、行道樹等。《廣場》中寫到的各種被噪音和香味充斥的廣場周邊亮著各類商業廣告牌,隨處都站立著推銷廣告的兼職者,但是在夜晚最安靜的時候廣場上只有“躺在自動取款機前睡覺的那個人的鼾聲”和“抱著廣告牌的醉鬼”。一方面,作者在城里回望村莊不僅出于對故鄉的懷念,更是在面臨理想城市破滅后做出的選擇。起初人們將城市作為理想的居住之所,但是在城市“土”帶上瀝青和汽油的味道之后,它便不再是村莊里具有野性的土,沒有誰可以忍受得住那被汽車行駛過而留下的汽油味。另一方面,對村莊的思念和回望在另一個層面上是因為作者所擁有的鄉土經驗無法真正地認識城市,甚至兩者還會產生矛盾。許多由鄉入城的人們體驗過快速、繁復的城市生活后,產生或多或少的焦慮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人們逐漸開始選擇回到鄉村。
尋找詩意的家園成為人們更迫切的要求,他們注意到鄉村是一個較為完美的空間,在那里,沒有學區房、工作壓力、交通堵塞等一系列城市問題。身處城市卻心戀鄉土的背后暗藏了對城市“亂象”的不解和無奈,加之作家童年時期的鄉土記憶以及與“鄉”的情感連接,作者筆下的“文學鄉愁”應運而生。
為了應對在城市面臨的困境,他選擇短時間“返鄉”。然而這種“返鄉”并不能真正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城市困境,《清單》一文就提到了“帶回去的是物質的,可見的,而帶回來的,則是巨大的空虛和回憶”;《小偷》中也提到敘述者短時間內“返鄉”而后又重新再進城的情節。散文切實地書寫了鄉村變遷給予了作者怎樣的情感體驗,以冷靜客觀的視角和簡單樸素的文字表達了對家鄉變遷的無奈。重新面對“陌生”鄉村,老鼠的消失、樹木的雜亂、家畜的退場、人的逃離和鄉村的衰敗成為人們所要面臨的又一道難以解開的謎題。生于鄉村,居于城市,散文展現了這類“返鄉者”的最終歸路仍是重返城市,敘述者“我”是如此,多數人也是如此,他們所追求的“詩意的家園”已變了模樣,他們所陷入的精神困境也并非“返鄉”能夠解決的。
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議題,人們對城市生活的體驗不是單一的,個人必然擁有自己的城市經驗。許多人帶著以往獲得的鄉土經驗進入現代城市,并非還能如從前一般如魚得水,就像文本所寫到的,蝸牛并不能適應鋼筋水泥的城市,人們無法從城市中獲得認同感。城市經驗與鄉土經驗的沖突使作者更清楚地了解個人生命經驗在個體、社會中的重要性,作者將這種矛盾沖突寫入文學作品中,不斷在文學創作中消解自我焦慮和精神虛無的難題,進而也在作品中給予人們更加多元的視角和選擇去看待城鄉困境。
三、寫作方式的新與舊
“鄉”與“城”是文學創作的兩大源泉,田鑫的散文創作也離不開這二者。他的散文以飽含深情的眼光打量鄉村的親人舊故、陳年往事,甚至草木鳥獸,語言滲透出惆悵、無奈,但又散發著樸素、靜穆的氛圍,突出的是對漸行漸遠的鄉土世界的書寫,他筆下的鄉村并非停滯的,而是不斷變化的。田鑫的散文創作方式有新有舊,一方面從童年經驗汲取創作源泉,另一方面則是對非常規敘述視角的運用。
作家的創作并非憑空起高樓,個體生命經驗成為文學創作的基點和養分。田鑫筆下的鄉村和城市是帶有他自己生命經驗的文學文本,是不斷更新變化的。藝術就是作家的白日夢,其中可能隱藏著他們的童年經驗。童慶炳曾提出:“童年經驗有兩種,一種是豐富性體驗,一種是缺失性體驗。”④缺失性體驗是作家進入創作過程的巨大推動力,少時喪母給予作者的是精神上的孤獨感和空缺感,散文反復提及喪母事件,甚至還反復描寫母親受傷后的樣子,軟軟的、軟塌的、軟塌塌等詞語的使用都間接地將童年的痛苦釋放出來。作家化解痛苦的方法就是在散文中反復寫母親的死亡,將自己痛苦的情緒充分釋放出來。作者從對母親的懷念入手構建他記憶中的村莊,回憶童年傷痕的同時也建構鄉土記憶,以此建立一個承載了“鄉愁”的甘渭河邊的村莊。
面對新的城鄉問題,如果還保持傳統的書寫方式不變,當下的散文創作是否能夠有新的突破?答案是不容樂觀的。散文創作不僅要在書寫內容上與現實進行更多更豐富的連接和互動,還要在寫作技巧上進行創新。作者不斷積極探索散文的寫作方法,從宏觀層面的散文小說化傾向到微觀的文本敘述視角,可以說,田鑫是一個具有創新思想的青年作家。他的散文多為敘事散文,常以人、事、物為線索展開文本,但散文不同于小說,它是一種內傾性較強的文體,作家往往采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視角組織文本。身為一名散文作家,他也不例外,但仍可從其散文中看見一些特別之處。
“我們”“你”等非常規敘述視角的運用,使得田鑫散文突破了傳統散文的布局,表現了青年作家在文體創新和創作方法上更加獨特的思考。這些非常規敘述視角散見于各個篇目中,集中有所運用的是他的《城市》一文,文本主要敘述者為第一人稱敘述視角“我”,但行文至第三節,敘述視角便成了第二人稱“你”,主要寫“你”在公交車上所觀察和所感受的事情,窺見中國社會的小縮影,“你突然又覺得,一輛公交車就是一座移動的微型城市,車上的每一個人,生命的輪回和軌跡都很逼真”⑤,與張愛玲的《封鎖》有異曲同工之妙。“你”既是前文敘述者“我”,又是閱讀散文的讀者。“你”的敘述陌生化了坐公交這個普通的行為,給予讀者別樣的閱讀體驗,達到讀者與故事之間的距離又近又遠的效果。
最后,文本中以“我們”的稱謂出現的文字,常向讀者表明希望他們給予同情或認同的態度。敘事時有“我們”,“我們說好的,你背過身去,從三開始倒數喊到一再轉過來”;“我們就守在虛土附近,幾個人定定地坐著,等著那只倒霉的兔子”。⑥議論時有“我們”,“作為被隱喻的麥子,我們誰也躲不過歲月的收割”⑦;“我們幼小的身體在水里上下起伏著,逃脫父親們的監視而躲在想象的母體里是一件幸福的事”⑧。在這里,“我們”的敘述人稱將讀者拉入敘事中,使讀者仿佛身處“我”所敘述的生活和場景之中,移情于所敘述的事情之中,從而對文中的人產生憐憫或同情。他不滿足于傳統,希冀找到一條更適合自己的散文創作方法,在小說化的散文的敘事語境中,“你”“我們”的敘述視角極為少見,運用它們進行散文寫作對他的散文乃至整體的散文而言都是具有創新性和啟發性的一步,它們成為作者言說生命經驗的新嘗試,展現了他對如何將自我生命經驗融合于文學創作中的新思考和新突破。
四、結語
田鑫自覺地將個體憂慮卻開闊的生命經驗融注在文學創作之中,堅持以自己的鄉土散文的創作來引起人們對鄉土與城市復雜關系的關注,呼吁人們關注人的心靈世界、關注自然、關注鄉土。據作者近兩年的散文作品可知,他仍保持著對鄉土的關注。鄉土文學由現代一直發展到當今,其中積累的相關創作經驗都是后來作家創作鄉土文學的素材和參照,從這方面而言,作家必須克服照搬以往鄉土文學所積累的創作經驗的惰性,深入文學創作的現實空間,進行一手資料的挖掘和思考。但作為一名青年作家,他的散文創作還有更為廣闊的天地可以開拓,其散文的價值也需要更長的時間加以考察。
注釋:
①田鑫:《大地詞條》,陽光出版社2022年版,第53頁。
②范培松:《西部散文:世紀末最后一個散文流派》,《中國文學研究》2004年第2期。
③(美)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51頁。
④童慶炳:《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頁。
⑤田鑫:《大地詞條》,陽光出版社2022年版,第216頁。
⑥田鑫:《大地知道誰來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頁,第15頁。
⑦田鑫:《大地知道誰來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頁。
⑧田鑫:《大地詞條》,陽光出版社2022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