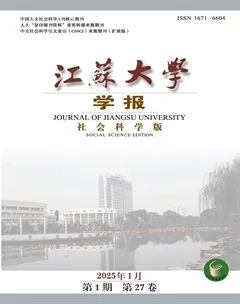論黨內法規的概念與特征
摘 要:盡管無論在黨內法規文本中還是在學者們的論著中都有關于黨內法規概念的相應界定,但這些界定都存在不夠準確的問題。黨內法規應當被作如下界定,即黨內法規是黨內有權機關制定或認可的,體現黨的統一意志,規范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活動,具有特定名稱、形式和內容要求,旨在確保黨的紀律實施,并由黨的組織強制力保障的具有法律性質的黨內專門規章制度的總稱。黨內法規具有法律屬性、政治屬性以及道德屬性,因此呈現出與這三種基本屬性相對應的法律性特征、政治性特征以及道德性特征。新征程中依規治黨的必然性決定了黨內法規研究必須受到重視,黨內法規學雖已被作為法學的一門二級學科,但依然具備發展為獨立一級學科的可能性。
關鍵詞:黨內法規;依規治黨;法律性;政治性;道德性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2BFX008)
作者簡介:劉長秋,上海政法學院紀檢監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溫州大學兼職教授,法學博士,從事黨內法規學、紀檢監察學、生命法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D2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25)01-0075-11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增強黨內法規權威性和執行力,形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現問題、糾正偏差的機制”【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5-66.】。黨內法規作為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的制度成果,同時也是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之治”乃至“中國之治”的“核心密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黨內法規研究受到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已越來越成為一門顯學。目前,有關黨內法規基礎理論的研究已經趨于豐富和成熟。但在另一方面,有關黨內法規的研究整體上依舊較為薄弱,尤其是在黨內法規本體論研究方面。對黨內法規概念及特征的研究正屬其中。立足學術研究,準確界定黨內法規的概念、全面把握黨內法規的特征,不僅是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黨內法規,深入研究依規治黨,從而更好發揮黨內法規作用的基礎和關鍵,也是構建黨內法規學科話語和學科體系,推動黨內法規學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擬就黨內法規的概念及特征加以探討,以期在助力依規治黨深入推進的基礎上,為黨內法規本體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略盡綿力。
一、 黨內法規的概念分析
概念是開展學術研究的基礎,所有學術研究都是從概念開始的,依規治黨研究也離不開對相關概念的探討,尤其離不開對黨內法規概念的研究。黨內法規概念是研究依規治黨的邏輯起點,也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基本保證,“黨內法規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對概念的解讀與應用”【趙子超.黨內法規概念體系的特殊性及構建方法[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5):59-66. 】。但就目前而言,無論是在具體的黨內法規文本中,還是在學者的論著中,有關黨內法規概念的界定都還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 黨內法規文本中的黨內法規概念及其評述
作為一個概念的“黨內法規”是由毛澤東同志在1938年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最先使用的【具體可參見廖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研究反思——以“黨內法規”話語為例》,載《法學家》2018年第5期,第1-14頁。】,之后,在黨的重要會議、文件以及黨的領導人的講話中又多次出現。盡管在黨的歷史上,黨內法規有時被稱為“黨規”“黨法”“黨的法規”或“黨規黨法”等,但其核心內涵與外延并沒有實質性差別,其內涵與實質都是黨內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劉長秋.論黨內法規的含義及其制度建設的要求[J].探索,2019(3):80-86.】。在黨的百余年歷史發展中,黨內法規發揮了“定海神針”般的重要作用,成為黨之所以能夠始終團結一心、領導人民在不同時期都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的核心制度密碼。不過,略顯遺憾的是,作為一個早已在黨內公開并反復使用的概念,黨內法規長期以來都沒有被黨的文件明確加以界定,直到1990年7月《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程序暫行條例》(以下簡稱1990年《暫行條例》)印發,黨的文件才首次對黨內法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規定。它在第2條中規定:“黨內法規是黨的中央組織、中央各部門、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制定的用以規范黨組織的工作、活動和黨員的行為的黨內各類規章制度的總稱。”2012年5月制定并取代1990年《暫行條例》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以下簡稱2012年《條例》)對這一概念進行了修正,依據其第3條:“黨內法規是黨的中央組織以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制定的規范黨組織的工作、活動和黨員行為的黨內規章制度的總稱。”以上概念為人們判定何為黨內法規提供了一個基本參照,也有助于黨內法規的宣傳與普及。但是,這些概念界定皆存在一定不足。
具體而言:(1) 概念未指出黨內法規的內涵。任何概念都是由內涵和外延共同構成的,前者規定事物的“質”,后者則規定事物的“量”,二者共同反映事物的規定性。黨內法規概念也應當如此。黨內法規概念的本質內涵在于“黨內法規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意志的體現”【宋功德,張文顯.黨內法規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7.】。但1990年《暫行條例》與2012年《條例》顯然都沒有對黨內法規的內涵亦即其本質做出明確界定。可見以上概念對黨內法規的界定在實質上有所欠缺。(2) 概念沒有將黨內規范性文件等其他非法律性質的黨內規章制度排除在外,容易使人將黨內規范性文件也作為黨內法規,實際上,黨內法規作為“中國共產黨內部具有法的意義的規則”【李軍.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56.】,只是黨內規章制度中較為特殊的一部分。黨內法規是黨的規章制度中規范化程度最高的制度形態,“具有較高位階,是管黨治黨最為核心的制度形式。”【王偉國.國家治理體系視角下黨內法規研究的基礎概念辨析[J].中國法學,2018(2):269-285.】這意味著黨內法規不是黨的規章制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發揮了法律作用的最關鍵部分。(3) 概念將黨內法規界定為“規范黨組織的工作、活動和黨員的行為的黨內規章制度”,明顯限縮了黨內法規的范圍,弱化了黨內法規的自身本應有的功能。實際上,黨內法規作為一種管黨治黨規范,其功能并不僅僅在于管黨治黨,更在于強化黨的領導,確保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地位。不僅如此,黨內法規調整的對象并不止于黨員行為,還包括黨員思想。“與法律只調整主體的外在行為不同,黨規既調整黨員、黨組織和部分非黨員主體的外在行為,又關涉和影響著普通黨員、黨員領導干部以及‘關鍵少數’黨員干部的內心。”【柯華慶.黨規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35-36.】概念將黨內法規調整對象限縮于黨組織的工作、活動和黨員的行為,顯然忽略了黨內法規對黨員思想的調整功能,弱化了黨內法規的自身本應有的功能。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2019年8月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以下簡稱2019年《條例》)對黨內法規的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依據其第3條:“黨內法規是黨的中央組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黨中央工作機關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制定的體現黨的統一意志、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依靠黨的紀律保證實施的專門規章制度。”相比于1990年《暫行條例》以及2012年《條例》,2019年《條例》對黨內法規概念的界定有了很大改進。該界定不僅指出了黨內法規的本質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意志的體現,而且將黨內法規規范的內容劃定為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并明確指出了黨內法規的保障要素,即“依靠黨的紀律保證實施”;此外,其將黨內法規的規范事項擴展為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活動,避免了將黨員思想排除于黨內法規調整范圍之外的不足。不僅如此,此概念還進一步斂縮了其自身的外延,即將黨內法規規定為一種“專門”規章制度,這就避免了概念外延的泛化,有助于為將黨內非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排除于黨內法規之外提供立法完善或進一步解釋的空間。但遺憾的是,這一概念界定依然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此概念混淆了黨內法規與黨的紀律的關系、未保持應有的開放性【關于該議題,作者已發表過專文論述,詳見劉長秋《論黨內法規概念在〈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中的文本表述》,載《黨內法規理論研究》2021年第1期,第91-107頁。】,對于黨內法規的定義與過去的歷史傳統和當前的制度實踐存在一定的裂隙【段磊.黨內法規淵源論[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33-40.】,以及存在表意不清、指代不明等問題,容易產生對其解讀的“二律背反”現象【柴寶勇,陳若凡.黨內法規制度:概念與范疇的再探討[J].黨政研究,2022(2):38-47.】等。
(二) 學術論著中的黨內法規概念
黨內法規概念在黨內法規文本中的界定為學界把握黨內法規概念進而深入研究黨內法規提供了基礎。正因為如此,大多數學者在研究黨內法規相關問題而需要對黨內法規概念加以明確時,往往都直接引用1990年《暫行條例》、2012年《條例》或2019年《條例》所界定的黨內法規的概念。但鑒于以上概念自身的不足,也有一些學者在其論著中自行對黨內法規概念進行了界定。如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是有權主體依據一定的權限和程序制定的調整黨的內部關系的規范性文件【柯華慶.黨規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39.】;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就是規范黨組織、黨員關系及其行為的一系列制度規范的總稱【王勇.再論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間的關系[J].理論與改革,2017(3):18-25.】;也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是指由中國共產黨各級各類組織制定或認可、反映黨的意志和客觀規律、規制和調整黨內行為和黨務關系的各類規范的總稱【肖金明.法學視野下的黨規學學科建設[J].法學論壇,2017(2):74-86.】;等等。這些界定對于學界進一步深入思考黨內法規現象,準確理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和深入推進依規治黨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這些概念界定要么未指明黨內法規的本質,要么對黨內法規制定主體的界定過于寬泛(如“由中國共產黨各級各類組織制定或認可”或“由中國共產黨制定”),要么對黨內法規外延的界定過于寬泛或模糊(如“用于規范黨內生活與行為規范的所有規章制度”)……都沒有抓準或抓全黨內法規概念界定應當具備的核心要素。
(三) 黨內法規概念的準確界定
筆者以為,從黨內法規最初被提出和使用的歷史背景及場域來看,黨內法規作為黨的統一意志的體現,其概念的提出及其制度建設之強化主要是基于保障黨的紀律實施之需要,是為了明確、細化和強化黨的紀律而必然做出的選擇,“其目的在于進一步突出和強調黨的紀律”【劉長秋.論黨內法規概念在《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中的文本表述[J].黨內法規理論研究,2021(1):91-107.】。在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擴大)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 個人服從組織;(二) 少數服從多數;(三) 下級服從上級;(四) 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為使黨內關系走上正軌,除了上述四項最重要的紀律外,還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這里傳達出了多方面的信息:首先,黨內法規是黨法黨紀層面的一種規范,該概念是在需要于全黨內部重申黨的紀律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的,目的在于彌補黨的紀律不夠詳細和明確而在實踐中經常難以真正落地的不足,以確保黨的紀律實施。其次,制定黨內法規以更好地實施黨的紀律,是為了體現并貫徹黨的統一意志,亦即“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以達成黨內團結一致、步調統一的目的。再次,黨內法規的調整對象是黨內關系,制定黨內法規的目的是使黨內關系行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因為只有黨內關系得到理順,全黨才能團結統一、更具有政治執行力和戰斗力。而時至今日,黨不斷強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任務盡管有所拓展,但其核心目的依舊在于“使紀律建設有所遵循”【郭玥.黨的紀律建設:淵源、要素和制度創新[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8(1):48-53.】,以便更好地依規治黨,令黨成為一個堅強團結的戰斗堡壘;亦即“黨的紀律需要用黨內規章制度進行維護”【梁振濤,高建.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邏輯理路[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30-37.】,以更好地管黨治黨,使黨始終堅強統一,擔好作為領導核心的使命,引領并實現好社會治理。這與當下黨中央一再突出的“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之要求實際上是一脈相承、完全契合的。以此為基點,在黨內法規概念界定中,如果必須要對黨規與黨紀的關系做出界定,則二者的關系顯然應當是黨內法規是用以確保黨的紀律實施的規章制度,而非黨內法規是依靠黨的紀律保障實施的規章制度。
不僅如此,從黨內法規效力的保障因素來看,黨內法規不同于國家法律,它不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而是以黨的組織強制力作為保障。對于違規黨員,只要其行為不構成對國家法律的違反,就不能對其施以國家強制力,而只能施以組織強制力,即通過黨的組織強制力確保黨內法規實施【有關黨的紀律與黨內法規之間關系的具體分析,可參見劉長秋、潘牧天的《全面從嚴治黨視野下的黨內規矩建設與紀檢監察研究》,法律出版社,2023年,第68-96頁。】。此外,從法治的維度來看,黨內法規作為一種相對特殊的法,需要特定的名稱與表現形式,它應當隸屬廣義上的黨內規范性文件的范疇,而且是黨內規范性文件中具有法的形式與內容規范要求的特定規范性文件。不僅如此,為了確保黨的政治決策的一體執行,這類黨內規范性文件通常對其制定主體有著特定要求,即制定此類法規的只限于黨內特定的黨組織而非所有黨組織。
從某個角度來說,“概念一旦被定義就容易故步自封,在保守傾向的概念定義與變動不居的實踐之間總會有張力”【宋功德.黨規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9.】。正因為如此,“黨內法規概念的內涵要保持空間的開放性,為黨內法規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成果的轉化創造條件”【陳家剛.“黨內法規”:概念、屬性與邊界[J].新視野,2020(4):81-88.】。畢竟,依規治黨不斷發展的現實需要決定了只有在界定黨內法規概念時保持一定的開放性,才能更好地適應依規治黨形勢的變化。就此而言,黨內法規概念的界定應當在力求細致以盡可能包納這一概念所應當包含的各要素的基礎上,盡量保留一定的延伸性,以便為今后黨內法規制度的發展以及依規治黨的需要留出足夠空間。以此為基點,筆者以為,黨內法規宜被作如下界定,即黨內法規是黨內有權機關制定或認可的,體現黨的統一意志,規范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活動,具有特定名稱、形式和內容要求,旨在確保黨的紀律實施,并由黨的組織強制力保障的具有一定法律性質的黨內專門規章制度的總稱【值得說明的是,黨內法規和黨內規范性文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如同行政法規和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區別。關于黨內法規與黨內規范性文件的關系,筆者曾發表過專文論述(見劉長秋、史聰《論黨內法規與黨內規范性文件的關系》,載《桂海論叢》2020年第6期,第111-116頁),后者有廣義與狹義兩種解讀。就廣義而言,黨內法規也是一種黨內規范性文件。】。
二、 黨內法規的特征分析
黨內法規的特征是黨內法規概念之外有關黨內法規本體論研究繞不開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人們準確把握黨內法規與其他制度規范之間聯系與區別的關鍵。但在當下學界有關黨內法規特征的有限研究中,人們對于黨內法規特征的歸納與表述并不統一,在黨內法規具有哪些特征這一問題上還遠沒有達成共識。
(一) 學界有關黨內法規特征的主要見解
在黨內法規特征的把握上,學者們立足于不同的研究視角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宋功德從黨內法規與黨的規范性文件、組織決定及領導講話的比較中歸納了黨內法規的特征,他認為,較之黨的規范性文件、黨的組織決定、領導講話等,黨內法規呈現出組織性、規范性、抽象性、泛適性等基本特征【宋功德.黨規之治:黨內法規一般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67.】。魏治勛則從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關系及其地位與功能上分析了黨內法規的特征,認為黨內法規具有正式社會規范的一般特征,同時又具有區別于一般特征的獨特特征,呈現出特征方面的多元向度,具體體現為突出的“黨性”、形式屬性的雙層次多向度、創制功能與效力范圍的特定性以及效力保障機制的多重性【魏治勛.黨內法規特征的多元向度[J].東方法學,2021(1):128-138.】。也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是黨的有權機關制定或認可的、調整黨內行為的社會規范,具有行為規范性;黨內法規是規定黨內權利和義務的社會規范,具有權利義務一致性;黨內法規是具有一定形式結構和內容結構的社會規范,具有剛性;黨內法規是由黨的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具有社會強制性【孫磊.黨內法規本體論研究的法理范式——論黨內法規的基本特征、構成要素與調整關系[J].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9(1):177-184.】。而宋功德、張文顯主編的《黨內法規學》則指出,黨內法規具有政治性、規范性與權威性【宋功德,張文顯.黨內法規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24-27.】。此外,還有學者探討了作為黨內法規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黨的領導法規的特征,認為黨的領導法規制度具有制度規范政治性、調適廣度全面性、內容層次“雙觀”性、展現形式多樣性等鮮明特征【王冰冰.黨的領導法規制度:概念、特征與功能[J].理論導刊,2021(11):31-39.】。這些研究對于我們科學認識黨內法規的特征,厘清黨內法規作為一種制度規范與國家法律以及其他社會規范的區別,無疑都能夠帶來很好的啟發。
但是,筆者以為,以上有關黨內法規特征的研究更多的是從黨內法規外在面向上來進行分析的,絕大多數成果似乎都還沒有關注到黨內法規從內在面向上所顯現出來的特征。就其概念內涵而言,所謂特征,其實是指研究對象與其他對象在比較過程中所顯現出來的差別或不同,亦即可以作為研究對象特點的標志和特殊的地方。從哲學上來說,事物的外在特征是其在內屬性的外化。“事物具有什么樣的特征通常是由其屬性所決定,有什么樣的屬性往往才會擁有什么樣的特征。”【劉長秋.論黨內法規的特征——兼論黨內法規調整作為一種制度調整的優勢[J].觀察與思考,2023(8):48-55.】以此為基點,要準確把握黨內法規的特征,必須立足黨內法規自身屬性的維度,首先明確黨內法規的屬性。
(二) 黨內法規特征的具體分析
黨內法規是中國共產黨運用依規治黨思維管黨治黨的實踐產物,是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核心,是黨全面從嚴治黨、強化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之寶貴經驗的制度成果,同時也是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與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政黨倫理尤其是執政倫理的制度化。這決定了黨內法規必然具有法律屬性、政治屬性以及道德屬性三種基本屬性,并因此而呈現出與這三種基本屬性相對應的法律性特征、政治性特征以及道德性特征。
其一,黨內法規是一種法治規范,具有法律屬性與法的基本特征。黨內法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法。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法,黨內法規具有明顯的法律性特征,即所有法都具有的規范性、統一性與權威性。具體而言:(1) 作為一種法,黨內法規具有規范性。“法的規范化是法之所以為法的邏輯結果。”【陳朝陽.論黨內法規的法學品格[J].海峽法學,2022(3):1-11.】黨內法規作為法,亦遵循此律,也具有法的規范性,無論是在制定方面,還是在實施方面,抑或在內容方面,都具有規范性要求,突出法言法語,強調嚴謹性,注重程序性。正因為如此,2019年《條例》對黨內法規的制定有著明確的規范性要求;而同時發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執行責任制(試行)》也明確規定了黨內法規執行需要遵循的程序。這些都是黨內法規作為一種法而具有的規范性體現。“黨內法規的規范化塑造著自身法的規范性屬性,其內容也就當然地內嵌著法的品質。”【同②.】(2) 作為一種法,黨內法規具有統一性。首先,黨內法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意志。任何法都是一定群體統一意志的反映。國家法律是國家意志的反映,而黨內法規則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意志的反映。其次,黨內法規具有淵源上的統一性。黨內法規以黨章為淵源,是黨章規定的細化、具體化或再細化、再具體化,任何一部黨內法規從根源上來說都是為了更好實施黨章相關規定的結果。再次,黨內法規具有適用上的統一性,即該規范統一適用于黨內,不會因為適用對象的不同(如職務上的差異、掌握資源的不同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等)而有所區別。在黨內法規的適用上,黨內各主體具有統一的平等性。此外,黨內法規還具有目的上的統一性,即所有黨內法規——無論是何種時期的黨內法規,也無論是哪一類黨內法規——其制定與實施都服務于黨的政治目標的實現,其目的都在于確保黨初心不改、使命必達。(3) 作為一種法,黨內法規具有權威性。權威性是法的重要屬性之一。黨內法規作為一種法也具有權威性,這是黨內法規法律性的外化。黨內法規之所以被稱為“法規”,就在于其在管黨治黨方面具有法的權威性和約束力,能夠作用于黨員及各級黨組織,發揮法的作用。對于廣大黨員及各級黨組織而言,黨內法規并不僅僅是一種制度,而是具有高度權威性的法。“黨內法規的權威意味著一種黨員自愿服從的自我約束。”【李大勇,郭理.論黨內法規合理性審查標準的展開[J].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2(2):149-160.】
其二,黨內法規又是一種政黨規范,具有政治屬性及政治規范的一般特征。黨內法規是中國共產黨用以管黨治黨的規范,是作為執政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規范與思想行為規范,也是一種主要適用于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內部規范。作為一種政黨規范,黨內法規首先是一種政治規范,即具有相應政治功能、以法規形式表現出來且具有法的效力的政黨規范。這種規范主要適用于黨的內部,用以調整黨內關系,確保黨內團結統一、步調一致、統一行動,以更好地實現黨的政治目標。當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政黨政治,政黨是政治的核心與主導。而政治性則是政黨的根本屬性。“政治屬性是政黨的第一屬性,體現著政黨的本質區別,決定著政黨的前途命運。”【李仰哲.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J].求是,2021(16):28-31.】政黨的政治屬性決定了黨內法規作為主要適用于黨的內部的一種規范,必然具有鮮明的政治目標與政策指向,服務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需要。黨內法規作為一種政黨規范,既具有一般政黨規范的共性,又與一般政黨規范有很大的不同,該種政黨規范是適應保持中國共產黨自身先進性與純潔性之需要、要求更高且規定更嚴、具有法律性質的政黨規范。而且,這種規范基于黨的自身的地位及其政治活動,往往能夠帶來一定外部效應,其對黨內關系的調整具有“由內及外”的鮮明特點【劉長秋.論黨內法規對黨內關系的調整[J].探索,2021(6):115-125.】,具有一般政黨規范所不具備的作用力。黨內法規的本質是政治立法,是用法律形式加以形塑的政治要求與政治規定,其存在的價值及其自身追求的目標應當是服務于黨的政治需要。這使得黨內法規既具有法律性,也具有政治性。作為一種政黨規范,黨內法規以政治性為根,以法的規范性為要,是一種較具特殊性的政黨規范。
其三,黨內法規還是一種道德規范,具有道德屬性以及道德規范的普遍性特征。斯科特·夏皮羅認為:“法律的道德性問題是一個即使不是至關重要,也是很有意義的研究領域。”【斯科特·夏皮羅.合法性[M].鄭玉雙,劉葉深,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4.】站在法哲學的角度上,法與道德關系密切。道德是法的基礎,法是道德的保障。“道德不只是法的條件,也是法的目標。”【伯恩·魏德士.法理學[M].丁曉春,吳越,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80.】黨內法規作為一種政治規范和法治規范,既內含了黨的政治要求,也內含了黨的道德追求,該規范寄寓了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倫理與執政道德,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新型政黨所特有的人民立場及高尚性。黨內法規是介于倫理道德與國家法律之間的一種法治規范,其要求高于國家法律而更趨近于倫理道德。正因為如此,黨內法規中含有很多高層次的倫理道德要求。例如,黨章要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要求“堅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這些要求不僅是適用于廣大黨員的法規要求,也是相比于一般公民而言層次更高的倫理道德要求。黨內法規是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政黨倫理與執政道德的制度化,具有極其鮮明且濃厚的道德底色。“與多數法律規范不同,道德規范最初并不注重外部行為,而是注重內心思想。”【伯恩·魏德士.法理學[M].丁曉春,吳越,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48.】黨內法規的道德性決定了作為一種法的黨內法規不同于國家法律。相比于國家法律在調整社會關系上更關注公民的行為而言,黨內法規在關注黨員行為的同時亦注重調整黨員的思想,其對黨內關系的調整是由內及外、從調整黨員思想開始最終落實到黨員行為的,會產生思想調整與行為調整的雙重調整功效。這顯然也是黨內法規作為一種法與國家法律相比所具有的鮮明特征。
三、 有關黨內法規研究困境的一點學術思考
對黨內法規概念與特征的研究乃至整個對黨內法規的研究需要充分了解黨內法規這一概念被提出并被反復強調的歷史背景,準確把握其功能定位。這是研究好黨內法規的基礎。黨內法規作為黨內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具有鮮明的法律性特征、強烈的政治性特征與厚重的道德性特征,是調整黨內關系、實現“黨規之治”的基礎和保障。黨內關系是社會關系的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這一政治事實同時也是法律事實下,黨內關系甚至已經成為我國當代社會關系中最需要關注和重視的一種關系。原因在于,黨內關系直接決定著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穩定、發展及其執政能力。從黨內治理的角度上來說,黨內關系的調整需要運用包括國家法律、政黨規范以及倫理道德與一般性社會規范等在內的各種規范。黨內法規只是眾多調整規范中的一種,但卻是其中最為重要且發揮核心作用的規范。黨內法規的重要性源于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重要地位及其勇于自我革命的品行定位。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及其勇于自我革命的品行定位決定了黨的領導及其自身建設在整個國家治理中的引領性與決定性,也決定了“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基本邏輯。而黨內法規則是具有自我革命基因的中國共產黨在講政治、行德政、堅持運用法治思維的基礎上,高標準、嚴要求管黨治黨的制度成果,是管好黨、治好黨的核心制度保障。黨內法規所具有的法律性、政治性以及道德性特征,使得其相較于單純的法律規范、政治規范以及道德規范,在調整黨內關系時往往具有更大的制度優勢,能夠吸收并集合法治規范、政治規范以及道德規范的部分功能,并盡可能彌補單純的法治規范、政治規范與道德規范在調整黨內關系時所顯現的不足。而黨內法規的上述制度優勢決定了依規治黨作為管黨治黨基本方式必然會產生單純的規則治黨所無法達到的效果,必然會帶來眾所期盼的“黨規之治”。
黨的二十大宣告了黨和國家事業邁上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新征程中,需要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一如既往地強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一以貫之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和依規治黨。正因為如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完善黨內法規,增強黨內法規權威性和執行力”【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45.】。而要“完善黨內法規,增強黨內法規權威性和執行力”以便更高效深入地推進依規治黨,就必須要重視黨內法規研究,推進黨內法規研究的學理化構建與學科化發展。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于2024年初發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將黨內法規學納入法學學科目錄,使得黨內法規學被明確列為法學一級學科門類下的一個獨立二級學科,為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然而另一方面,黨內法規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功能定位與國家法律存在差異的一種法治規范。這使得黨內法規學作為以黨內法規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必然具有不同于以國家法律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法學學科的一些特征,該學科實際上是以黨為根、以馬為魂、以法為要的一門學科。具體而言:黨內法規作為黨內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之基本定位,決定了黨內法規存在的價值在于通過將管黨治黨納入法治化軌道來加強黨的建設,進而強化黨的領導。這使得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必然是黨內法規學的根脈所在,黨內法規學研究必須以黨為根,服務于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的需要。同時,作為黨內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黨內法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與黨的領導及其建設實踐相結合的重要制度成果。這決定了黨內法規學必然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開展研究。此外,作為黨內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黨內法規也是一個新的重要法學概念。而法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術性,法的專業技術性決定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必然是“一項兼具政治性、規范性和技術性的系統工程”【陳光.論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化視角下的黨內立規協調[J].理論與改革,2018(3):101-112.】,而黨內法規研究也必然是一項要求具有法學專業知識背景與技術要求的研究。如果不了解、不熟悉法律,沒有法學的系統訓練,通常很難研究好黨內法規,很難為依規治黨提供真正有價值的對策建議。以此為基點,黨內法規學盡管根在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魂在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以法為要,必須重視法學研究方法在黨內法規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具備必要法學修養的基礎上對黨內法規開展更為專業的研究。
立足于以上分析,2024年初發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將黨內法規學作為法學二級學科的做法,正有助于黨內法規研究在法學學科內找到自身的歸屬以暫時解決其過去一直迫切需要解決而未能解決的學科歸宿問題,并能夠發揮法學專業性在研究黨內法規問題上的優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法學尚沒有將黨內法規現象納入自己的視野,這使得一些法學研究者容易忽略作為法的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之間的差別,以致在研究時照搬法學研究的套路與方法,使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朝向國家法律制度建設方向發展,逐漸弱化甚至消弭其在管黨治黨方面的制度優勢。而這已成為當下黨內法規研究亟須走出的一個困境。實際上,黨內法規自身的法律性特征、政治性特征以及道德性特征,決定了黨內法規研究必然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該領域需要發揮法學研究的主導作用,但同時更需要發揮中共黨史黨建學、政治學、紀檢監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其他學科研究的協同作用。黨內法規學作為以黨內法規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新學科,應當被作為一門獨立一級學科。黨內法規研究更需要在跨學科維度上多層面展開,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自身專有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盡管當下為了解決無學科歸屬的問題而暫時將黨內法規學作為法學的一門新的二級學科,但今后該學科依舊具有進一步發展成為一門獨立一級學科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責任編輯: 劉雨軒)
On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 Reflections on the Difficulty of the Study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Liu Changqiu
(School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definitions in both the Party’s documents and scholars’ works, none of these definitions is accurate enough. The Party regulations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general term for specializ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within the Party that are formulated or recognized by the authoritative organs within the Party to reflect the unified will of the Party to regulate the leadership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They have specific names, forms, and content requirements, aim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 discipline, and are equivalents to law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regulations have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attributes, therefore presenting corresponding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evitability of governing the Party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in the new journey calls fo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hese regulations, which may be upgraded to an independent first level discipline from a second level on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Party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arty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legal nature; political nature; moral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