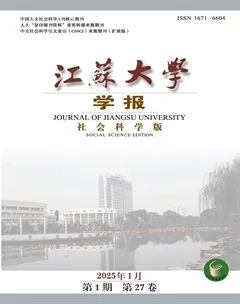論文學(xué)譯叢出版的“非文學(xué)”策略
摘 要:生活書店出版的《世界文庫》系20世紀(jì)30年代譯介匯編中外名著的大型文學(xué)叢書,由著名作家、權(quán)威譯者、知名學(xué)者供稿,打造了頗具特色的外國文學(xué)名著譯介出版模式。其在譯介推廣時(shí)采用了“非文學(xué)”作品傳播策略,將尼采的哲學(xué)篇什、比昂松的回憶錄、華茲華斯的作品序言、蘭姆的書信等“非文學(xué)”作品納入出版范疇。這些“非文學(xué)”作品譯介充實(shí)了《世界文庫》的內(nèi)涵,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把握譯作的結(jié)構(gòu)、主題和意圖,深入了解作家的思想脈絡(luò)和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以及把握所讀作品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在連接中國讀者與文學(xué)經(jīng)典的過程中,這些“非文學(xué)”作品發(fā)揮了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在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背景下,這種“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融合譯介模式也為中國文學(xué)“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guān)鍵詞:《世界文庫》;“非文學(xué)”譯介;文學(xué)傳播;中外文學(xué)交流
基金項(xiàng)目:國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一般項(xiàng)目(19BZW173)
作者簡介:曾潤,貴州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講師,文學(xué)博士,從事現(xiàn)代文學(xué)與傳媒研究;羅長青,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化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文學(xué)博士,從事當(dāng)代文學(xué)與文化傳播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I209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1-6604(2025)01-0098-11
在文學(xué)作品譯介中,傳播策略的有效性對(duì)作品推廣至關(guān)重要。有效的傳播策略不僅能增加作品的知名度,使作品在目標(biāo)受眾中得到廣泛傳播,而且能促進(jìn)文學(xué)的國際交流,推動(dòng)文學(xué)多元發(fā)展。在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探尋有效的譯介傳播策略對(duì)于促進(jìn)文化的國際傳播至關(guān)重要,譯介傳播策略研究也備受學(xué)界重視。此前竇衛(wèi)霖的《政治話語對(duì)外翻譯傳播策略研究——以“中國關(guān)鍵詞”英譯為例》【竇衛(wèi)霖.政治話語對(duì)外翻譯傳播策略研究——以“中國關(guān)鍵詞”英譯為例[J].中國翻譯,2016(3):106-112.】、張曉雪的《“翻譯說服論”視角下中華典籍外譯與傳播策略研究——以明清小品文英譯為例》【張曉雪.“翻譯說服論”視角下中華典籍外譯與傳播策略研究——以明清小品文英譯為例[J].湘潭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5):171-176.】、肖笛的《中國當(dāng)代小說海外譯介與傳播的特點(diǎn)、問題及策略》【肖笛.中國當(dāng)代小說海外譯介與傳播的特點(diǎn)、問題及策略[J].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22(7):35-44.】等研究已經(jīng)強(qiáng)調(diào)過譯介傳播策略的重要意義,并從政治話語、翻譯理論、文化傳播等層面分析中國文化如何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傳播與接受問題,就如何構(gòu)建有效的譯介傳播策略提出了諸多構(gòu)想。
隨著相關(guān)研究的推進(jìn),研究者對(duì)具體作品的譯介傳播策略研究也持續(xù)跟進(jìn),如萬瀅安的《謠知童趣:〈孺子歌圖〉海外譯介出版的文化圖景與傳播策略》【萬瀅安.謠知童趣:《孺子歌圖》海外譯介出版的文化圖景與傳播策略[J].中國出版,2022(17):66-70.】、王海和王樂的《〈京報(bào)〉英譯活動(dòng)中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與技巧——以〈中國叢報(bào)〉文本為例》【王海,王樂.《京報(bào)》英譯活動(dòng)中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與技巧——以《中國叢報(bào)》文本為例[J].國際新聞界,2014(10):62-81.】、許多和許鈞的《中華文化典籍的對(duì)外譯介與傳播——關(guān)于〈大中華文庫〉的評(píng)價(jià)與思考》【許多,許鈞.中華文化典籍的對(duì)外譯介與傳播——關(guān)于《大中華文庫》的評(píng)價(jià)與思考[J].外語教學(xué)理論與實(shí)踐,2015(3):13-17.】等文章就探討了中國文學(xué)的對(duì)外譯介傳播策略。翻譯文學(xué)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生成與建構(gòu)過程中發(fā)揮著關(guān)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dòng)了中國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和繁榮。在此進(jìn)程中,大型外國文學(xué)翻譯叢書起到的中介作用不容小覷,如商務(wù)印書館的《世界文學(xué)名著》(1928)、世界書局的《世界名著叢書》(1929)、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譯文叢書》(1935)等,這些大型譯叢的譯介與傳播策略理應(yīng)受到足夠重視,然而目前學(xué)界對(duì)此鮮有關(guān)注,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現(xiàn)象。
生活書店出版的《世界文庫》系20世紀(jì)30年代匯集中外名著的大型文學(xué)叢書,被視為與同時(shí)期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并駕齊驅(qū)的新文學(xué)出版“兩大工程”。得益于著名作家、權(quán)威譯者、知名學(xué)者供稿,《世界文庫》形成了有特色的外國文學(xué)名著出版經(jīng)驗(yàn),尤其是收錄了大量哲學(xué)理論、作家論、序言、作家書信等“非文學(xué)”作品,做到了翻譯文學(xué)經(jīng)典的“譯”“介”統(tǒng)一,為后世出版文學(xué)叢書、引進(jìn)翻譯外國文學(xué)作品提供了較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借鑒。本文從傳播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圍繞《世界文庫》譯介的“非文學(xué)”作品特征,探討《世界文庫》翻譯文學(xué)經(jīng)典的推廣與傳播策略,試圖在學(xué)理層面為中外文學(xué)交流實(shí)踐與研究提供相應(yīng)的支撐。
一、 依托“哲學(xué)理論”弘揚(yáng)反叛精神
從學(xué)科分類上看,哲學(xué)和文學(xué)屬于截然不同的學(xué)科領(lǐng)域。哲學(xué)主要思考關(guān)于存在、知識(shí)、價(jià)值等基本問題,通過邏輯分析和哲學(xué)思辨來追求普遍真理;文學(xué)則借助藝術(shù)形式表達(dá)人類的情感、經(jīng)驗(yàn)和思想,通過故事、詩歌等手段傳達(dá)多樣化的個(gè)體和社會(huì)體驗(yàn)。哲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作品的側(cè)重點(diǎn)也有所不同,前者多強(qiáng)調(diào)理性思辨,后者更側(cè)重于情感表達(dá)。雖然哲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會(huì)相互影響,有所溝通、聯(lián)系,但在哲學(xué)著作和文學(xué)名著的出版上,大多數(shù)出版機(jī)構(gòu)還是會(huì)將二者區(qū)分對(duì)待,因此“哲學(xué)理論”一般不會(huì)出現(xiàn)在以“文學(xué)名著”為主體的叢書中。《世界文庫》作為20世紀(jì)30年代出版的大型文學(xué)叢書,其出版定位是有計(jì)劃地“介紹和整理,將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獻(xiàn)世界的文學(xué)名著于一般讀者之前”【鄭振鐸.世界文庫發(fā)刊緣起[M]//世界文庫:第1冊(cè).上海:生活書店,1935:1-4.】。從這個(gè)定位來看,《世界文庫》應(yīng)該不會(huì)將“哲學(xué)理論”納入出版對(duì)象。然而,在實(shí)際出版的《世界文庫》中,有不少作品可被歸入哲學(xué)理論范疇。這種獨(dú)特的運(yùn)作方式顯然值得關(guān)注。
《世界文庫》收錄了大量哲學(xué)理論著作,其中“尼采學(xué)說”最具代表性。該叢書首年出版的十二冊(cè)中,后七冊(cè)均刊載了尼采的哲學(xué)理論,包括《啟示藝術(shù)家與文學(xué)者的靈魂》《宗教生活》和《蘇魯支如此說》等重要作品。在哲學(xué)領(lǐng)域,尼采的“上帝已死”“超人哲學(xué)”“權(quán)力與意志”“永恒循環(huán)”等核心思想和理論,顛覆了西方傳統(tǒng)道德標(biāo)準(zhǔn)與價(jià)值觀念,對(duì)后世哲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成為現(xiàn)代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尼采學(xué)說蘊(yùn)含著打破傳統(tǒng)束縛、推崇創(chuàng)新、倡導(dǎo)個(gè)體自由的精神,在中國知識(shí)界引起廣泛共鳴,成為20世紀(jì)以來中國學(xué)界持續(xù)關(guān)注的重要思想資源。郜元寶在考察尼采的中國接受史時(shí)指出:“中國新派知識(shí)分子幾乎無人不談尼采”【郜元寶.魯迅六講:二集[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0:93.】。王國維、魯迅、茅盾、鄭振鐸等人均撰文闡釋過尼采學(xué)說,如王國維認(rèn)為尼采學(xué)說“破壞舊文化而創(chuàng)造新文化”【王國維.叔本華與尼采[M]//方麟.王國維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115-135.】,魯迅多次援引尼采觀點(diǎn)稱其為“矯十九世紀(jì)文明”通弊的“大士哲人”【魯迅.文化偏至論[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45-64.】,茅盾盛贊“尼采實(shí)在有詩的天才,與其說他是大哲學(xué)家,不如說他是大文豪”【詳見雁冰(茅盾)《尼采的學(xué)說》,載《學(xué)生》,1920年第7卷第1號(hào)。】。這些評(píng)價(jià)充分說明了尼采及其哲學(xu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影響。
在文學(xué)家、思想家們對(duì)尼采進(jìn)行介紹的同時(shí),尼采的作品也陸續(xù)被翻譯至國內(nèi)。1920年,《民鐸雜志》專門推出“尼采號(hào)”特刊,集中發(fā)表了《尼采思想之批判》《尼采之著述及關(guān)于尼采研究之參考書》《超人和偉人》《查拉圖斯特拉的緒言(尼采原著)》《尼采傳》《尼采之一生及其思想》【詳見《民鐸雜志》1920年第2卷第1號(hào)。】等系列文章介紹尼采及其相關(guān)作品,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知識(shí)界對(duì)尼采的討論與接受。在尼采思想傳播至國內(nèi)的進(jìn)程中,魯迅對(duì)尼采的譯介與接受情況最具代表性。在魯迅的著作中,有數(shù)十篇雜文和書信提及尼采及其著作,如《文化偏至論》(1908年)、《〈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譯者附記》(1920年)、《“硬譯”與“文學(xué)的階級(jí)性”》(1930年)等,可以說尼采思想貫穿了魯迅的大半個(gè)文藝生涯。縱然魯迅前后期對(duì)尼采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但他始終將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jià)值”的思想視為反抗舊中國傳統(tǒng)、追求民主自由、實(shí)現(xiàn)富國強(qiáng)民的一種思想武器。魯迅在1925年盛贊尼采是掃除舊思想的“軌道破壞者”【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201-207.】;1929年承認(rèn)自己投稿《語絲》是因?yàn)槭艿侥岵勺髌返摹坝嗖ā敝绊憽爵斞?我和《語絲》的始終[M]//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168-180.】;他還在《〈致近代美術(shù)史潮論〉的讀者諸君》中,把尼采與歌德、馬克思一同并稱為偉人【魯迅.致《近代美術(shù)史潮論》的讀者諸君[M]//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309-315.】。1935年,魯迅推薦徐梵澄翻譯尼采的《啟示藝術(shù)家與文學(xué)者的靈魂》《宗教生活》《蘇魯支如此說》幾篇著述,并介紹給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出版。可見,魯迅對(duì)尼采學(xué)說的濃厚興趣從未間斷,而尼采及其相關(guān)學(xué)說當(dāng)時(shí)在國內(nèi)已形成傳播熱潮。
尼采學(xué)說蘊(yùn)含著批判傳統(tǒng)、追求自由、探索人性的思想,“以戰(zhàn)斗的姿態(tài)匯入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洪流”【樂黛云.尼采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0(3):20-33.】,與30年代左翼文學(xué)提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不僅不矛盾,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左翼文學(xué)的發(fā)展。尼采學(xué)說中的“超人哲學(xué)”“意志至上”“永恒回歸”等思想與中國左翼作家追求個(gè)性、倡導(dǎo)自我解放、表達(dá)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滿等理念具有相通之處,因此,尼采學(xué)說受到國內(nèi)知識(shí)分子歡迎,甚至成為時(shí)代精神。《世界文庫》將《啟示藝術(shù)家與文學(xué)者的靈魂》《宗教生活》《蘇魯支如此說》三部作品與其他文學(xué)經(jīng)典一并出版,原因也在于此。《世界文庫》第八到十二冊(cè)發(fā)表的徐梵澄翻譯的《蘇魯支如此說》就是尼采極為典型的否定舊價(jià)值體系、肯定個(gè)人生命意志的作品。《蘇魯支如此說》是尼采的主要著作之一,后通譯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在這部著作中,尼采借虛構(gòu)人物拜火教先知蘇魯支的口吻,以散文詩的形式,宣揚(yáng)自己的“超人哲學(xué)”及“權(quán)力意志”思想觀點(diǎn),探討人類存在、道德、宗教、權(quán)力等諸多問題,認(rèn)為傳統(tǒng)的哲學(xué)、宗教和道德已不能與時(shí)代同步,應(yīng)該由“超人”把人們從舊文化中拯救出來。這部作品表達(dá)了對(duì)舊價(jià)值體系的反叛與疏離,是尼采重新審視生命、主宰自我世界、超越已有自我的表現(xiàn)。五四時(shí)期魯迅、茅盾等人將尼采學(xué)說視為改造國民性的精神來源,從尼采學(xué)說中汲取有助于激勵(lì)中華民族戰(zhàn)斗精神的資源,這與20世紀(jì)30年代左翼作家們的文學(xué)追求具有很強(qiáng)的一致性。從這個(gè)層面看,《世界文庫》編者將尼采的哲學(xué)著作與其他作家的文學(xué)作品一起作為“世界文庫名著”出版發(fā)行,折射出20世紀(jì)30年代學(xué)人對(duì)于文學(xué)經(jīng)典價(jià)值認(rèn)知的進(jìn)步取向——關(guān)注自身命運(yùn)和弘揚(yáng)反叛精神,意義十分深遠(yuǎn)。
二、 借助“作家論”擴(kuò)寬讀者視野
“作家論”是對(duì)作家思想、文學(xué)修養(yǎng)、創(chuàng)作才華及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等重要問題的評(píng)述,有助于理解作家的生活經(jīng)歷、所處時(shí)代背景及文學(xué)風(fēng)格等,是文學(xué)研究的重要理論資源。在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論及“作家”的作品屢見不鮮。如南朝文學(xué)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以“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強(qiáng)調(diào)屈原的人格修養(yǎng)對(duì)《離騷》的影響。進(jìn)入20世紀(jì)30年代,更是出現(xiàn)了大量論及作家的“作家論”或“作家評(píng)傳”,如《郁達(dá)夫評(píng)傳》(1931)、《冰心論》(1932)、《周作人論》(1934)等。此外,上海生活書店還在1936年出版了“作家論”系列叢書,徐志摩、周作人、林語堂、沈從文等作家都有專論。溫儒敏曾分析這一“作家論”熱潮出現(xiàn)的原因,認(rèn)為主要是進(jìn)入20世紀(jì)30年代之后,“新文學(xué)發(fā)生已經(jīng)過去十多年,歷史的距離稍微拉開,新文學(xué)也基本上站住了腳跟,那些新文學(xué)的前驅(qū)者們,有了檢閱、總結(jié)新文學(xué)歷史的強(qiáng)烈的欲望”【溫儒敏.作為文學(xué)史寫作資源的“作家論”——“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學(xué)科史”研究隨筆之一[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5(2):83-90.】。在他看來,“作家論”不僅是對(duì)“五四”以來新文學(xué)作家作品的評(píng)述,更通過為這些作家“立論”“立傳”,強(qiáng)化了他們的文學(xué)經(jīng)典地位,為新文學(xué)樹立了權(quán)威形象。這種通過“作家論”強(qiáng)化新文學(xué)地位的努力,還體現(xiàn)在對(duì)外國“作家論”的翻譯和引介中。《世界文庫》對(duì)別倫·別爾生的《我的回憶》、泰納的《梅里美論》及蒲寧的《憶契訶夫》等作品的載用,不僅反映了學(xué)界打造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經(jīng)典的意圖,也為推廣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及其作品開辟了新的途徑。
《世界文庫》第一冊(cè)所載的挪威散文家別倫·別爾生撰寫的《我的回憶》是一篇介紹其父親、19世紀(jì)末挪威現(xiàn)實(shí)主義戲劇家別瑟尼·別爾生(以下稱比昂松)【即挪威現(xiàn)代戲劇家、詩人、小說家比昂斯滕·比昂松(Bjrnstjerne Martinus Bjrnson,1832—1910),在原文中也被稱為“老別爾生”。】的作品,由茅盾翻譯。《我的回憶》主要聚焦比昂松早年從事的政治活動(dòng),并涉及比昂松的生活及交友情況,寫作初衷是讓讀者清晰地看到“當(dāng)年自由主義的老別爾生”是如何被他的同胞們視為“洪水猛獸”的【別倫·別爾生.我的回憶[M]//鄭振鐸.世界文庫:第1冊(cè).上海:生活書店,1935:425-434.】。因此,這篇文章不僅僅記錄了比昂松個(gè)人的經(jīng)歷,更通過比昂松家人的視角,為讀者全面呈現(xiàn)了比昂松作為一位政治家的形象。這種政治家形象與20世紀(jì)30年代“左聯(lián)”重視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的譯介需求具有一致性,譯介該作恰好契合了“左聯(lián)”對(duì)于揭示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呼喚社會(huì)正義的文學(xué)作品的要求。而譯者茅盾作為左翼文壇巨匠,選擇譯介《我的回憶》則源于他長期對(duì)比昂松及挪威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的關(guān)注。從茅盾早年譯介的挪威文學(xué)來看,他關(guān)注的作家作品均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特征,與20世紀(jì)以來中國文學(xué)界人士皆大力提倡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的潮流相契合。因此,茅盾譯《我的回憶》不僅為國內(nèi)讀者介紹了比昂松這個(gè)挪威作家,更為讀者提供了深入了解挪威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的有效途徑。
《世界文庫》第五冊(cè)所載的《梅里美論》是19世紀(jì)法國著名文學(xué)批評(píng)家泰納之作,主要介紹法國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梅里美的生平、創(chuàng)作理念、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及所處時(shí)代環(huán)境,也是讓國內(nèi)讀者了解法國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的重要作品。泰納在文中不僅分析了梅里美作品的藝術(shù)特質(zhì),還探討了其創(chuàng)作與社會(huì)環(huán)境之間的深刻聯(lián)系,強(qiáng)調(diào)梅里美對(duì)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貢獻(xiàn),從而展現(xiàn)了梅里美在法國文學(xué)史上的獨(dú)特地位。梅里美在中國的影響同樣深遠(yuǎn),周立波專門撰寫《梅里美和他的〈卡爾曼〉》進(jìn)行介紹【周立波.梅里美和他的《卡爾曼》[M]//周立波魯藝講稿.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26-31.】;著名法語翻譯家柳鳴九評(píng)價(jià)梅里美是“法國19世紀(jì)最富有藝術(shù)魅力的作家之一”,指出其創(chuàng)作“在思想內(nèi)容上也經(jīng)歷了由批判過時(shí)的封建階級(jí)到否定資產(chǎn)階級(jí)文明的過程”,“反封建的激情與銳氣顯然大大超過了他對(d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揭露”【柳鳴九.柳鳴九文集:卷5 法國文學(xué)史(中)[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394.】。梅里美作品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圍內(nèi)產(chǎn)生廣泛影響,主要在于其深刻揭示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問題和階級(jí)矛盾,諷刺了虛偽的宗教道德,肯定了世俗情感的價(jià)值,展現(xiàn)了不同時(shí)代、國家的風(fēng)俗與道德。《世界文庫》刊載《梅里美論》,為讀者深入了解法國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開辟了新路徑,這與20世紀(jì)30年代學(xué)人打造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經(jīng)典的努力不謀而合。
《世界文庫》第六冊(cè)所載的《憶契訶夫》也是全面介紹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的作品,由俄國作家蒲寧所作。文章主要以蒲寧與契訶夫的交往為線索,涉及契訶夫的生平、愛好、寫作特點(diǎn)及文學(xué)活動(dòng)等,為讀者呈現(xiàn)了一位豐滿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家形象。契訶夫的作品多取材于普通百姓生活,揭示沙皇黑暗統(tǒng)治、地主剝削及資本主義弊端,表達(dá)了對(duì)勞動(dòng)人民的深切同情。契訶夫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及對(duì)社會(huì)問題的關(guān)注,與20世紀(jì)上半葉中國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需求高度契合,因此在中國文學(xué)界影響深遠(yuǎn)。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契訶夫的影響。例如,魯迅就曾表示“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yàn)樗拢臀覀兊氖澜绺咏薄爵斞?葉紫作《豐收》序[M]//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227-230.】。契訶夫作品所反映的俄國與20世紀(jì)初的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這使得其作品在國內(nèi)被廣泛譯介。自1907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吳梼譯的《黑衣教士》以來,契訶夫譯介熱潮逐漸興起,如1923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耿濟(jì)之、耿勉之譯《柴霍夫短篇小說集》,1930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趙景深譯《柴霍夫短篇杰作集》。巴金曾回憶,在19世紀(jì)“俄羅斯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中間,契訶夫是作品譯成中文最多的一個(gè)”【巴金.向安東·契訶夫?qū)W習(xí)——在莫斯科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紀(jì)念會(huì)上講話[M]//談契訶夫.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39-43.】。結(jié)合契訶夫作品在國內(nèi)的譯介情況來看,《世界文庫》選載《憶契訶夫》正是從“作家論”角度推動(dòng)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在國內(nèi)的接受與傳播,有其獨(dú)特的學(xué)術(shù)史意義。
三、 通過“序言”拓展文學(xué)經(jīng)典內(nèi)涵
為增進(jìn)讀者對(duì)世界文學(xué)名著的了解,《世界文庫》還選載了一些知名作品的“序言”。“序言”又稱“前言”或“引言”,一般指介紹或評(píng)述著作的文章,通常放在著作正文之前,用來說明著述的創(chuàng)作意圖、寫作經(jīng)過、編次體例、作家評(píng)述及作品特色等。根據(jù)法國敘事學(xué)家杰拉德·熱奈特的“副文本”理論,“序言”與“標(biāo)題”“插圖”“跋”等同屬副文本的重要類型【熱拉爾·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集[M].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71.】,是連通正文本與讀者的有效橋梁。序言作為獨(dú)立于著作之外的文本形式,對(duì)于幫助讀者了解著作成書背景和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均有重要參考價(jià)值。如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總括了《史記》一書,追溯了司馬遷的生平及家世;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序》闡述了中國文字的源流及演變,說明了漢代書體與古文的聯(lián)系;北宋歐陽修的《五代史伶官傳序》對(duì)五代時(shí)期后唐的盛衰進(jìn)行分析,闡述了國家興衰、事業(yè)成敗由“人事”所定而非“天命”的道理等。考察中外文學(xué)發(fā)展的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序言的文學(xué)史地位遠(yuǎn)比原著或正文更高,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李清照的《金石錄后序》、王勃的《滕王閣序》等,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都具有極重要的價(jià)值。《世界文庫》出版的“序言”有華茲華斯的《〈抒情詩歌集〉序言》、莫泊桑的《〈筆爾和哲安〉序》、雨果的《〈克林威爾〉序》、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總序》、泰納的《英國文學(xué)史序論》以及菲爾定的《散文的〈喜劇的史詩〉》(即《約瑟夫·安德魯斯》的序言),均為世界知名作家所著的知名作品序言,在幫助讀者認(rèn)識(shí)世界文學(xué)經(jīng)典方面具有重要價(jià)值。
《人間喜劇總序》是“現(xiàn)代法國小說之父”巴爾扎克畢生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也是理解其創(chuàng)作文學(xué)巨著《人間喜劇》的關(guān)鍵文本。巴爾扎克在序言中詳細(xì)闡述了《人間喜劇》的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作意圖及其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主張。他明確指出,小說應(yīng)該包括“社會(huì)的歷史和社會(huì)的批判,社會(huì)的罪惡的分析和社會(huì)的原理的檢討”【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總序[M]//鄭振鐸.世界文庫:第8冊(cè).上海:生活書店,1935:3683-3699.】,著力揭示社會(huì)現(xiàn)象和人性的復(fù)雜性,作家必須關(guān)注社會(huì)生活、描繪社會(huì)真相、展示時(shí)代風(fēng)貌。這篇序言與《人間喜劇》一樣體現(xiàn)出深刻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特征,既是巴爾扎克對(duì)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的闡述,也是他對(duì)法國社會(huì)的批判與剖析,為讀者理解其創(chuàng)作理念、藝術(shù)風(fēng)格及時(shí)代背景提供了重要參照。
《英國文學(xué)史序論》是法國文藝?yán)碚摷姨┘{1863年為《英國文學(xué)史》第一卷所作的序言,是理解其文學(xué)理論的關(guān)鍵文獻(xiàn)。泰納在序言中系統(tǒng)闡述了“文學(xué)三要素”理論,認(rèn)為“種族”“環(huán)境”“時(shí)代”是決定文學(xué)的三大根本要素,既涉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內(nèi)部根源,又體現(xiàn)文學(xué)作品生成的外部環(huán)境。三者的相互作用不僅影響精神文化的走向,也決定了文學(xué)藝術(shù)的發(fā)展趨勢(shì)和路徑。泰納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模仿,是對(duì)事物本質(zhì)的表現(xiàn),是記錄人類精神狀態(tài)的重要文獻(xiàn),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色彩。這一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xué)觀念有相通之處:左翼文學(xué)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注和對(duì)不公正現(xiàn)象的批判,力求揭示社會(huì)階級(jí)、性別、種族等不平等問題,并試圖通過文學(xué)作品呼吁社會(huì)變革和進(jìn)步;泰納用種族、環(huán)境和時(shí)代來關(guān)照文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與社會(huì)及時(shí)代的密切關(guān)系,致力于探討社會(huì)時(shí)代下的民族心理。《英國文學(xué)史序論》提出的文學(xué)理論在世界文學(xué)史上影響深遠(yuǎn)。譯者逸夫高度評(píng)價(jià)該序言,稱其“最簡賅地闡明他的實(shí)證主義的歷史哲學(xué)和藝術(shù)哲學(xué),同時(shí)也展開了自然主義理論的基礎(chǔ)”【泰納.《英國文學(xué)史》序論[M]//鄭振鐸.世界文庫:第10冊(cè).上海:生活書店,1935:4787-4808.】。這一評(píng)價(jià)表明,泰納的理論為理解文學(xué)作品的歷史、哲學(xué)和藝術(shù)內(nèi)涵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jù),也為自然主義文學(xué)研究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同時(shí),這一理論啟發(fā)了更多文學(xué)研究者和評(píng)論家深入探討文學(xué)與社會(huì)、時(shí)代、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極大地拓寬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研究視野,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而持久的影響。
《〈筆爾和哲安〉序》為法國小說家莫泊桑所作,是充分表達(dá)其美學(xué)思想、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及小說特色的一篇小說論。該作是莫泊桑小說創(chuàng)作理論的集中呈現(xiàn),因此學(xué)界又稱其為《論小說》。莫泊桑在序言中圍繞小說創(chuàng)作的相關(guān)問題進(jìn)行了闡釋。首先,他反對(duì)學(xué)院派批評(píng)家們按已有“規(guī)則”解讀新興小說的做法,以此號(hào)召批評(píng)家們摒棄成見,以謙虛的態(tài)度鑒賞當(dāng)代小說作品。其次,他指出小說所描繪的現(xiàn)實(shí)與生活中的現(xiàn)實(shí)有所不同,文學(xué)作品應(yīng)表現(xiàn)真實(shí)但又超越現(xiàn)實(shí)的真實(shí)。在此基礎(chǔ)上,他反對(duì)左拉等人認(rèn)為小說“單是真實(shí)并且是全部的真實(shí)”的論調(diào),認(rèn)為“真實(shí)是有時(shí)可以不像真的”【莫泊桑.《筆爾和哲安》序[M]//鄭振鐸.世界文庫:第10冊(cè).上海:生活書店,1935:4778-4779.】。再次,他還在序言中分析了古今小說家的差異,認(rèn)為過去的小說家傾向于選擇并描述人生的危機(jī)以及靈魂和內(nèi)心的劇烈變化,而現(xiàn)在的小說家則更關(guān)注日常狀態(tài)中內(nèi)心、靈魂和智慧的表現(xiàn),進(jìn)而指出古今小說家的這種差異絲毫不影響他們藝術(shù)成就的高低。分析序言不難發(fā)現(xiàn),莫泊桑的美學(xué)主張是在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主義觀念基礎(chǔ)上所作的補(bǔ)充,對(duì)世界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的發(fā)展有重要推動(dòng)作用,是了解近代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文獻(xiàn)資料。著名翻譯家柳鳴九在重譯《〈筆爾和哲安〉序》時(shí)就表示翻譯該序的原因在于其是“一篇在世界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論中膾炙人口的理論文字”【莫泊桑.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M].柳鳴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268.】的佳作,這也充分說明了《世界文庫》將其視為經(jīng)典的做法有獨(dú)特價(jià)值。此外,《世界文庫》收錄的《〈抒情詩歌集〉序言》和《〈克林維爾〉序》等也是極為重要的理論作品,對(duì)于讀者熟悉西方文學(xué)及文學(xué)思潮具有重要參考價(jià)值。
四、 憑借“作家書信”透析作家思想及生平
作為一種私人化寫作,書信是解讀一個(gè)人思想及行為的重要載體。而作家書信更是兼具歷史和文學(xué)的雙重價(jià)值,成為文學(xué)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與文獻(xiàn)。中國文學(xué)史上不乏知名的作家書信,如樂毅的《報(bào)燕王書》、司馬遷的《報(bào)任安書》、吳均的《與朱元思書》、李白的《與韓荊州書》等均是揭露作家思想及其文學(xué)活動(dòng)的重要文獻(xiàn)。西方文學(xué)也將作家書信視為探究作家情感交流的重要形式,在啟蒙運(yùn)動(dòng)、浪漫主義思潮興起時(shí)就產(chǎn)生了許多著名的作家書信。《世界文庫》選載的《游美雜記》《集外書簡》《蘭姆書簡選》就是此類作家書信的典型。20世紀(jì)30年代,國內(nèi)掀起了一股作家書信出版的熱潮,國內(nèi)外作家的書信集紛紛問世。國內(nèi)有陶行知的《知行書信》、周作人的《周作人書信》、郭沫若的《沫若書信集》、朱湘的《朱湘書信集》等,國外如柴霍夫的《柴霍夫書信集》、高爾基的《高爾基文藝書簡集》等也在這一時(shí)期被譯介至國內(nèi)。大量作家書信的出版,體現(xiàn)了20世紀(jì)30年代學(xué)界對(duì)作家個(gè)人生活及創(chuàng)作心路歷程的高度重視。《世界文庫》“外國之部”將古羅馬渥維德的《擬情書》、波蘭顯克威茲的《游美雜記》、挪威易卜生的《集外書簡》、英國蘭姆的《蘭姆書簡選》等作家書信納入譯介范疇,也順應(yīng)了20世紀(jì)30年代關(guān)注作家書信的出版潮流。
作為理解作家思想與創(chuàng)作的重要史料,《世界文庫》選譯的這些書信不僅展現(xiàn)了作家的思想脈絡(luò)、創(chuàng)作背景和生活軌跡,也豐富了讀者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認(rèn)識(shí)維度。如茅盾翻譯的《擬情書》就為讀者了解古羅馬文化提供了獨(dú)特視角。《擬情書》是古羅馬詩人渥維德【即古羅馬詩人普布留斯·奧維第烏斯·納索(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年—公元18年),通稱奧維德。】給傳說中的神話人物撰寫的情書,又譯為《女名人的哀詩》,共21篇。前15篇是女性寫給男性的書信,著重刻畫女性面對(duì)愛情時(shí)的心理變化;后6篇是三對(duì)男女的往來書信,以男性去信女性復(fù)信的形式,展現(xiàn)男女之間真摯的愛情。《擬情書》以豐富的想象力將西方古代神話故事融入其中,通過細(xì)致入微的描寫呈現(xiàn)豐富的內(nèi)容。鑒于《擬情書》涉及典故較多,為使讀者深入地了解其內(nèi)容,茅盾在翻譯時(shí)做了詳盡的題解及旁注。他不僅在開篇說明了作品的作者、內(nèi)容、風(fēng)格及譯本選擇,還在每一篇書信譯文前專門寫了“題解”,如在第一封《莎茀給法昂的信》【此處的“莎茀”應(yīng)指古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約公元前630年—約公元前560年),原文誤印為“茀莎”,引用時(shí)已修正,特注。】前,詳細(xì)介紹了莎茀的身份背景及其與法昂的愛情故事,并對(duì)渥維德作此信的意圖及風(fēng)格進(jìn)行說明:“渥維德此虛擬的情書,就作為在法昂逃避后,莎茀寫的;他把關(guān)于莎茀的種種傳說以及希臘神話的一些故事凝合而為此信之骨骼,再披以他的美麗的想象的衣,成了一封出色的失戀的哀詩”【渥維德.擬情書[M]//鄭振鐸.世界文庫:第7冊(cè).上海:生活書店,1935:3149-3161.】。這些題解、旁注與譯文相互照應(yīng),使古希臘古羅馬的神話更立體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有助于拓寬讀者的閱讀視野,更好地了解外國古代文學(xué)經(jīng)典。
同為茅盾翻譯的《游美雜記》和《集外書簡》也是幫助讀者了解作家思想及生平的重要作品。《游美雜記》是波蘭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顯克微支【即波蘭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亨利克·顯克維支(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根據(jù)他在1876年至1879年間的旅美經(jīng)歷寫成的通訊集,又譯作《旅美書簡》。顯克微支從《波蘭報(bào)》特派記者的身份視角,記錄了美國社會(huì)各階層的生活狀況,既展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工業(yè)經(jīng)濟(jì)的發(fā)達(dá),又揭露了種族歧視等社會(huì)問題,特別是印第安人和波蘭僑民的悲慘遭遇。這段旅美經(jīng)歷直接促成了顯克微支文學(xué)觀念的轉(zhuǎn)變,使他隨后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茅盾在譯介《游美雜記》時(shí)指出:“顯克微支游美以前是一位革命的民族主義的作家。但從美國歸來后,他就從‘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到‘過去’,專用波蘭歷史上的‘光榮’的史實(shí)來寫‘安慰’的小說,使他的同胞暫時(shí)忘記了眼前的痛苦。”【顯克微支.游美雜記[M]//鄭振鐸.世界文庫:第2冊(cè).上海:生活書店,1935:875-883.】顯克微支作品中體現(xiàn)的思想與當(dāng)時(shí)的中國社會(huì)需求十分契合,譯介《游美雜記》對(duì)中國讀者了解西方“弱小國家民族”文學(xué)具有重要意義。茅盾翻譯的挪威現(xiàn)實(shí)主義戲劇家易卜生的《集外書簡》同樣具有史料價(jià)值。《集外書簡》收錄了易卜生的十封書信,這些書信時(shí)間跨度從1863年至1899年,涵蓋了易卜生成名前到成為挪威文壇代表作家期間的重要階段,涉及他與挪威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克萊門·彼得森、劇作家別瑟尼·別爾生、柏林大學(xué)教授霍福來及德國藝術(shù)家海倫娜·拉孚的通信,展現(xiàn)了易卜生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dòng)和思想發(fā)展歷程。為方便讀者理解,譯文還對(duì)信中涉及的學(xué)人進(jìn)行了詳細(xì)介紹,進(jìn)一步拓寬了讀者的視野。
此外,《世界文庫》第十一冊(cè)選載的《蘭姆書簡選》同樣極具代表性。蘭姆是英國著名的散文家和書信家,其現(xiàn)存書信多達(dá)上千份。這些書信內(nèi)容極為豐富,是了解其生平經(jīng)歷及內(nèi)心世界的第一手資料。《世界文庫》發(fā)表的《蘭姆書簡選》選編了蘭姆在不同時(shí)期寫給友人的書信,如給撒繆爾·推勒·科爾列治(柯勒律治)、威廉·溫茲華斯(華茲華斯)、妥麥斯·曼寧以及溫茲華斯夫人等人的信件。給科爾列治的信寫于1796年,主要是蘭姆對(duì)其所遭遇家庭變故及處理情況的描繪;給溫茲華斯的信寫于1801年,主要談及蘭姆對(duì)倫敦生活的向往及對(duì)親友之死的感傷;給曼寧的信寫于1802—1803年,主要分享他的旅行計(jì)劃及出行趣事;給溫茲華斯夫人的信寫于1818年,主要述說他在東印度公司的生活感受。從蘭姆書信涉及的內(nèi)容來看,他的書信呈現(xiàn)出面對(duì)生活挫折和不幸仍選擇頑強(qiáng)奮斗的小人物形象,這種從日常瑣事入手展現(xiàn)復(fù)雜社會(huì)環(huán)境的書信寫作手法,使蘭姆書信成為英國書信文學(xué)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我國著名散文家梁遇春的散文風(fēng)格就受到蘭姆書信的影響,甚至有研究者表示梁遇春“以英國隨筆作家蘭姆談話體隨筆為結(jié)構(gòu)基礎(chǔ),建造了一種類似的文體”【黃偉.中國的伊利亞——梁遇春散文兼與蘭姆隨筆比較[J].北京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2(2):13-20.】。《世界文庫》中的《蘭姆書簡選》立體地向中國讀者呈現(xiàn)了作家蘭姆的文學(xué)活動(dòng)及當(dāng)時(shí)英國社會(huì)文化的多個(gè)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價(jià)值。
生活書店出版的《世界文庫》通過大量“非文學(xué)”作品來推廣文學(xué)經(jīng)典,譯介了哲學(xué)篇什、回憶錄、作家論以及各類作家序言和書信等作品,多層面地拓寬了中國讀者的閱讀視野。這種“非文學(xué)”作品譯介不僅為讀者提供了關(guān)于作品文學(xué)背景和文化語境的解釋,有助于接受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結(jié)構(gòu)、主題和目的;同時(shí),它向讀者呈現(xiàn)了作者對(duì)作品的闡釋和創(chuàng)作理念,使得讀者更為深入地理解作者的思考和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此外,這類譯介還提供了文學(xué)傳統(tǒng)的參照,幫助讀者了解所讀作品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以及這些作品在不同歷史階段所獲得的評(píng)價(jià)。在連接中國讀者與文學(xué)經(jīng)典的過程中,這些“非文學(xué)”作品發(fā)揮了橋梁和紐帶作用,為讀者理解和欣賞世界文學(xué)經(jīng)典提供了線索和支撐。在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背景下,這種“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融合譯介模式為中國文學(xué)“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融合譯介不僅能夠豐富作品的文化內(nèi)涵,增強(qiáng)其在市場(chǎng)上的競(jìng)爭力,而且能夠拓寬讀者的文化視野,幫助海外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學(xué)的精髓與內(nèi)涵。
(責(zé)任編輯: 劉雨軒)
The “Non-literary”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 A Case Study of Life Bookstore’s Promotion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Zeng Run1, Luo Changqing2
(1. School of Language and Art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2.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Life Bookstore’s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series, published in the 1930s, i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contributed by renowned writers,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creating a unique model for introducing and translating foreign literary masterpieces. In its promoting the literary series, the bookstore employed a “non-literary” strategy by including such works as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essays, Bjrnson’s memoirs, Wordsworth’s preface, and Lamb’s letters for publication. These non-literary translations enriched the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series by providing readers with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structures, them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translated works, so the readers could hav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s’ thoughts and creative motivations,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works in literary history. These works served as a vital link in bridg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literary classics.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internationally, Life’s integrated translation approach of combining “l(fā)iterary” and “non-literary” works sheds a new light on the “going abroad” for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literary dissemination; Sino-foreign literary exchan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