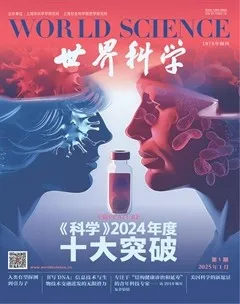支持高層次人才創業,重塑企業生態體系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上海市重點智庫、人才理論研究基地)有一項研究顯示,美國集成電路領域尖端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比例為1.6:1:1,而中國的這一比例為6:3:1。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我國尖端人才分布與美國存在巨大差異:我國尖端人才主要分布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分布在企業的相對較少。這一極其不均衡的結構筆者認為是制約企業成為科技創新主體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著力改變整體的尖端人才或高層次人才的分布情況,才有可能使企業成為這類人才的承載主體,進而使企業成為科技創新成果輸出的主體。
企業還未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科技進步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科研投入、組織科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我國企業是否已經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科研投入、組織科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呢?應該還沒有。
企業若要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必須首先成為科技人才的承載主體,特別是高層次人才的承載主體。無論是技術創新決策、科研投入,還是組織科研和成果轉化,都需要科技人員,特別是高層次人才來實施或執行。如果高層次人才不在企業,企業怎么做出引領行業技術進步的技術創新決策?怎么組織高水平的科研?怎么實施高水平的成果轉化?再說科研投入,其最主要是對科研人才的投入,特別是對高層次人才的投入,進而推動企業形成高水平的技術創新能力,促使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然而事實是,這一科研投入邏輯尚無法順利實施。
企業缺乏高層次人才
正如本文開始所提及的調研,我國高層次科技人才,無論在數量、質量還是結構及其分布上,都與美國有較大的差距,特別是高層次科技人才的分布及結構極其不均衡。
我國的高層次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機構,特別是在隸屬中央的高校、科研院所,地方的高校、科研院所相對少些,分布在企業的就更是鳳毛麟角。而美國高層次人才分布相對均衡多了,不僅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分布在企業的比例也非常高。這一局面的形成,跟我國不同類型機構發展到現階段承擔的科研角色有關,即高校、科研機構主要開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因而高層次人才集中,企業主要開展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而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的人才還比較缺乏,這又進一步降低企業成為高層次人才承載主體的可能性。
從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分布推導企業科技創新能力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化,主要通過技術開發、咨詢、服務的方式實施,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相對較少。而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又以10萬元之內的小項目為主。從《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2023(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上的數據看,2022年度380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和“技術開發、咨詢、服務”六種方式(通常作價投資參照技術轉讓,統稱“五技”服務)轉化科技成果的總合同項目數為562 882項,合同金額為1776.6億元,平均合同金額為31.56萬元。其中,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項目數為29 289項(占項目總數的5.2%),合同金額為242億元(占合同總額的13.6%),平均合同金額82.6萬元;以簽訂技術開發、咨詢、服務合同(統稱“三技”合同)的項目數為533 593項(占項目總數的94.8%),合同金額為1534.5億元(占合同總額的86.4%),平均合同金額為28.8萬元。與科技成果轉讓、許可、作價投資相比,“三技”合同是利用專門知識為企業解決技術難題,原創性不強,主要解決企業中短期發展中存在的技術難題,但對企業長遠發展的影響及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作用都很有限。
從科技成果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額看,1000萬元及以上的項目436項,占項目總數的比例為1.5%,而合同金額10萬元及以下的項目占比高達60%以上,大量低價值科技成果的轉化,對企業長遠發展的影響及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也許只有那些合同金額超億元,至少是超千萬元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才有可能對企業的中長期發展及科技創新能力提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上述數據表明,高校、科研院所的原創性研發不足,企業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能力也很有限。同樣,企業難以通過實施科技成果轉化比較快地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也就難以承載高層次人才,進而難以實施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轉化。這是由企業生態體系仍不健全決定的。要根本解決企業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不強、承載高層次人才不力的問題,必須重塑企業生態體系。
支持高層次人才創業,重塑企業生態體系
改變高層次人才分布,必須重塑企業生態。要通過科技成果轉化提升現有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使之成為科技創新主體,這是不現實的。必須大力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高層次科研人員以在職創辦企業、離崗創辦企業的方式實施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轉化,進而引導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的高層次科研人員創辦企業或進入企業,以改變我國當下高層次人才的分布。不過當下全國陸續有高校、科研院所正在先行探索,或許能為我們構建更好的企業生態提供借鑒。例如,上海交通大學推行的“完成人實施模式”,西北工業大學通過“三項改革”支持科研人員創辦企業,上海科技大學通過支持師生創辦衍生企業等,都是讓高層次科研人員主導實施高水平科技成果的轉化。此外,清華系、北大系、上海交大系等高校系上市企業群體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都比較強,推動一批高層次人才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企業。
隨著這些先行探索的做法成為一定模式在我國逐步推廣,或許有助于改進我國的高層次人才的分布結構。
本文作者吳壽仁是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級高工,曾任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原體制改革與法規處處長,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