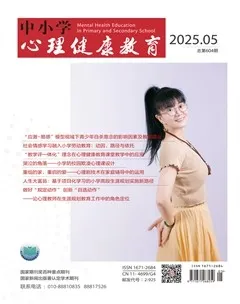“應激 - 易感”模型視域下青少年自殺意念的影響因素及教育建議
摘要:“應激-易感”模型將生理、心理、社會等多種因素相結合,探尋導致學生產生自殺意念的多重風險因素。基于“應激-易感”模型,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產生受多種因素影響:應激因素是外在風險因素,包括學習壓力、父母嚴苛型教養方式等;個體易感性因素是內在風險因素,包括自殺行為合理化認知、感覺尋求與沖動性、低自尊等;保護性因素是風險緩沖因素,包括內部和外部因素。由此提出了預防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應激-易感”模型;自殺意念;應激因素;個體易感性因素;保護性因素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25)05-0004-06
近些年,青少年群體受學業、家庭、人際關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困擾,出現自殺行為的比例呈現逐年遞增趨勢[1-2]。調查顯示,我國青少年群體自殺行為頻發,每年約有10萬中學生死于自殺,平均5位中學生中就有1位考慮過自殺。自殺意念是在實施自殺行為前,個體產生的結束生命的想法,我國青少年自殺意念檢出率為13.6%~17.1%[3-4]。自殺意念的出現能夠正向預測青少年的自殺行為,可以通過干預減弱自殺意念,降低青少年產生自殺行為的風險。明晰哪些因素會導致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或者哪些因素能保護青少年不產生自殺意念,顯得尤為重要。
“應激-易感”模型于1999年由Mann、Waternaux和Haas等[5]提出,結合生理、心理、社會等多重因素探討自殺意念的多重風險。該模型認為,應激因素、個體易感性因素和保護性因素相互作用,影響自殺行為的發生。應激因素是個體面對壓力源時身體適應和反應的應激過程,已有研究表明,應激因素與自殺意念顯著相關[6-7]。易感因素是個體的內在特質,包括沖動性、低自尊、負面認知模式等。保護性因素在該模型中發揮調節作用,積極的保護性因素可以降低個體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
基于“應激-易感”模型,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產生受應激因素與個體因素的相互影響。在應激因素方面,學業壓力、不良家庭環境等都可能導致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在個體因素方面,自殺意念的產生受到自殺行為合理化認知、沖動性等易感因素的影響。此外,同伴與教師的社會支持、心理韌性等能夠起保護性作用,減少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產生。在何種應激因素下青少年更容易產生自殺意念?有哪些因素能夠預防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青少年自身需要具備哪些積極心理品質,能更好地降低自殺意念易感性?本文將聚焦以上問題,對應激因素、個體易感性因素、保護性因素進行詳細闡述。
一、應激因素
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應激因素包括學業壓力、父母嚴苛型教養方式、人際關系困擾等。
(一)學業壓力
學業壓力是指未達到預期學習目標而引起的負面情緒、消極認知等心理感受,伴隨著青少年的學習生活問題[8]。熊茗伶、王泉泉和熊昱可等[9]認為,學業壓力產生時,學生挫敗感增強,由此引發適應不良等問題。不同的生長環境、心理狀態等導致個體對于壓力的感受性不同,高壓力易感性的青少年會表現出更多的負面情緒,出現更多心理健康問題,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性也隨之增加[10]。
(二)嚴苛的教養方式
父母嚴苛的教養方式是指在教育過程中,父母采用暴力懲罰的方式解決孩子成長中的問題。有研究表明,父母體罰能夠正向預測青少年自殺風險[11]。如果青少年經常處于父母嚴苛型教養方式下,其心理健康水平會更差,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增高,自殺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增加[12-13]。
(三)同伴關系困擾
隨著身心迅速發展,青少年對自己的人際關系狀況較為敏感,較為關注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高質量的同伴交往會增強青少年的幸福感,增強其社會適應能力。由于人際情景的多變、人際經驗的不足等因素,青少年容易產生人際壓力與心理沖突,進而出現人際關系困擾。人際關系困擾(如同伴沖突、社交回避等)是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重要風險因素,出現人際關系困擾的青少年更可能遭遇同伴欺凌,由此增加了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14-15]。
二、個體易感性因素
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個體易感性因素包括自殺行為合理化認知、感覺尋求與沖動性、低自尊、負面認知模式、童年期創傷、性別認同等。
(一)自殺行為合理化認知
自殺行為合理化認知屬于個體自殺態度的一部分,指個體對自殺行為持合理、認可態度的心理認知[16]。例如,青少年如果長期得不到認可,可能會導致價值感減弱;如果遇到困難時缺少社會支持,就會對生活持消極態度,久而久之,對自殺行為的認可度增強,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更高。
(二)感覺尋求與沖動性
感覺尋求與沖動性均可預測青少年自殺意念,進而導致青少年出現自傷、自殺等危險行為。危險行為雙系統模型指出,青少年社會情緒系統的發展速度快于認知控制系統,隨著青少年的成長,社會情緒系統將增強大腦對外部刺激體驗的敏感性。感覺尋求是反映青少年對新異刺激體驗的追求以及采取行為獲得新奇體驗的人格特質,具有較高感覺尋求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現自殺意念[17]。與此同時,青少年的認知控制系統發展相對滯后,自我控制能力尚未完全成熟。沖動性反映了個體自控力和意志力的不足,是青少年自殺、自傷行為的核心因素。沖動性常導致青少年在面對壓力和挫折時采取激進行為,而此時認知控制系統的發展不足以有效抑制這些沖動行為,從而增加了危險行為的發生風險[18]。總之,感覺尋求和沖動性是青少年自殺意念及危險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通過加強認知控制系統的培養,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產生自殺、自傷行為的風險。
(三)自尊
自尊作為自我概念的核心組成成分,代表個體對自身能力和價值所持有的肯定或否定評價,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能夠負向預測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19]。高自尊青少年思維模式更加積極,對學業生活中的困難持樂觀態度,對未來持有強烈的希望感;低自尊青少年思維模式較為消極,認為自己一事無成,無法形成積極自我認同,認為未來毫無希望,從而增加了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20]。此外,較低的核心自我評價會增加青少年產生抑郁的風險,而抑郁能夠正向預測自殺意念的產生,長期處于抑郁狀態的青少年通常認為未來無希望、人生無價值,感到無助和痛苦,由此產生用自殺結束生命的想法[21]。
(四)負面認知模式
青少年正處于探索自我同一性的發展階段,由于身心發展尚未成熟,對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理解較為有限。因此,當他們面對挫折時,往往更容易產生負面認知(對自我、未來和世界的消極看法),或者對發展中的挑戰容易持負面觀點。負面認知模式導致的生命意義感的缺失、對未來感到悲觀消極等,均有可能促使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22]。
(五)童年創傷經歷
童年創傷經歷對青少年自殺意念的影響是深遠和復雜的,其中,童年期虐待(指照顧者對兒童產生的傷害與潛在威脅)作為兒童成長過程中常見的成長類創傷,將導致個體的人格類型朝神經質方向發展,產生負性情緒注意偏向,對負性信息(如自殺相關的信息)更加敏感,從而產生自殺意念[23-24]。臨床與非臨床的研究均表明,童年期虐待與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產生存在較強的關聯,任何類型的童年期虐待都會加劇青少年出現自殺行為的風險[25]。
(六)性別認同
性別認同代表個體對自己性別的主觀體驗,它可能與出生時被指派的生理性別一致,也可能不一致[26]。性別認同不一致的青少年可能經歷更多的來自社會、家人與自我認知的挑戰,從而產生更多的焦慮、抑郁情緒,增加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研究表明,在性別認同不一致的青少年中,有14.8%的青少年持有自殺企圖,自殺意念終生流行率為28%[27-28]。
三、保護性因素
青少年自殺意念的保護性因素包括內部保護性因素和外部保護性因素。內部保護性因素包括心理韌性、領悟社會支持、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希望感和樂觀態度等;外部保護性因素包括友誼、支持性的學校氛圍、家庭支持(親密的家庭關系、健全的家庭功能)、學校活動及可獲得的心理健康服務等。
(一)內部保護性因素
1.心理韌性
心理韌性作為一種重要的保護性因素,能夠顯著影響青少年在面對學習和生活中的困難與挫折時的適應能力。心理韌性是指青少年面對學習、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時,利用自身保護性心理認知資源而達到適應良好的狀態。心理韌性高的青少年能夠靈活地運用自身資源,調整自身行為以適應客觀環境,從而戰勝困難、渡過難關[29]。已有研究證實,心理韌性水平高的青少年在面對消極生活事件時能夠保持較好的情緒調節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從而降低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相反,心理韌性較低的青少年因缺乏應對壓力的有效手段,壓力易感性更高,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也隨之增加[30-31]。
2.領悟社會支持
領悟社會支持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指個體對來自家人、同伴、教師等各類社會支持的感知和理解,并與主觀幸福感密切相關[32]。當青少年能夠充分感受到來自外界的關愛和支持,他們更容易保持心理上的安全感與穩定感,面對壓力時也能更有效地調節情緒。然而,當外部環境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時,若其領悟社會支持水平較低,青少年往往缺乏應對壓力的資源和信心,從而更容易產生自殺意念。外部支持與青少年的內在心理系統相互作用,社會支持的缺失會削弱其對負面情緒和挫折的抵抗能力,增加自殺風險。
3.情緒調節能力
情緒調節代表個體對情緒表達的管理和監控過程,主要涉及認知重評與表達抑制兩種策略,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能夠起保護作用,減少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產生[33]。認知重評作為一種適應性策略,能夠幫助青少年重新思考對情緒事件的認知,以積極觀點處理負面情緒和壓力(如將考試失利看作一次成長的機會)。表達抑制指有意識地控制并抑制自身情緒的外在表達(如隱藏自身痛苦情緒),這可能導致青少年的痛苦難以被發現,無法得到周圍人的支持和幫助,進而增加了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
4.希望感與樂觀態度
希望感和樂觀態度是青少年自殺意念的重要保護性因素,在維護心理健康和應對壓力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具有希望感的青少年通常對未來充滿期待,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實現目標。這種信念不僅增強了他們面對困境時的毅力,也提升了應對困難的信心。樂觀態度則幫助青少年更傾向于從積極角度看待挫折,減少消極情緒的累積。在面對壓力事件時,擁有希望感和樂觀態度的青少年更容易采用積極的歸因方式,將壓力事件視為暫時的、可控的挑戰,并善于挖掘內部積極資源,以積極心態應對挑戰和困難,降低了自殺意念的發生概率[34]。
(二)外部保護性因素
1.社會支持
在校園環境中,來自同伴與教師的支持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青少年處于身心迅速發展的階段,渴望獨立,但認識問題、評價結果的能力還相對較弱。面對壓力與挫折時,更傾向于采用逃避沖突的方式,周圍人(如同伴、教師等)的支持能夠幫助青少年表達情緒、應對挫折、克服困難。已有研究證實,大部分青少年并非希望通過自殺傷害自己,而是希望通過自殺讓周圍人了解到自己處于困境中,需要周圍人的支持與幫助。在校園中,同伴與教師支持、與周圍同學形成的友誼關系等對預防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產生起重要保護作用。
2.家庭關系
家庭是每一位青少年成長發展的第一個社會文化環境,家庭成員的靠近和親密程度能夠促進并培育青少年的心理素質,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35]。良好的家庭整體運作狀況是防止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重要外部保護因素,親密的家庭關系和健全的家庭功能能夠為青少年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幫助青少年以積極樂觀的心態應對學習生活與人際環境的挑戰,降低青少年出現自殺意念的風險[36]。
3.學校活動
學校活動對于預防青少年自殺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和多種多樣的課外活動能夠為青少年提供發展自我、發展興趣、拓寬友誼的機會,有助于緩解學業壓力,降低自殺風險。
4.心理健康服務
此外,學校的心理健康服務也尤為關鍵。心理健康服務的可及性是自殺意念的重要保護性因素,對預防自殺行為和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顯著作用。當青少年能夠方便、及時地獲得心理健康服務,他們在面對心理困擾時就能很快獲得專業支持和幫助,從而有效緩解負面情緒,減少自殺意念的產生。目前心理健康服務主要集中在學校和社區的心理健康中心(或心理咨詢室),主要的方式包括心理評估、心理咨詢、心理治療、危機熱線、心理健康教育等。特別是學校“每年一測”的心理健康篩查和評估機制,能夠早期識別有自殺風險的青少年并及時提供干預和支持。
四、教育建議
(一)注重家庭教育
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夠為青少年成長發展筑牢堅實根基,不良的家庭氛圍可能是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根源,家長要注重營造信任、平等的家庭氛圍,尊重孩子的獨立性,看到孩子行為背后隱藏的期待與渴望,以接納、包容、理解、尊重的態度感受孩子的需求,激發孩子成長的內在動力。
1.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
全體家庭成員要共同營造一個充滿愛、支持和理解的家庭環境,促進青少年情感發展,增強青少年的社會適應能力。當家庭內部出現矛盾和分歧時,家長要注意管理好自己的情緒,避免在憤怒或沮喪時做出沖動行為,避免使用暴力和侮辱性的語言。家長要時常向孩子表達愛和關心,讓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溫暖,還可以定期組織家庭活動,增進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系。
2.運用科學的溝通技巧
高質量親子溝通是促進形成積極健康家庭關系的催化劑,家長與孩子溝通時,要放下主觀想法,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聆聽孩子內心的聲音。當與孩子的想法出現分歧時,建議家長采用“非暴力溝通”的語言技術。
非暴力溝通包括觀察、感受、需要和請求四個步驟。觀察是指家長將自己觀察到的事實不帶任何主觀想法地講述給孩子,比如“你今天一直在玩游戲”;感受是家長對孩子表達自己對于事件的感受,表達感受時要盡可能避免使用攻擊性語言,比如“你今天的行為令我很憤怒”;在此基礎上,家長可以清晰具體地向孩子表達需要,比如“請你把游戲機關上,開始做作業”;最后,家長向孩子提出實操性強的請求,比如“之后你的游戲機放在媽媽這里,做完作業后,允許你玩20分鐘,可以嗎?”
(二)加強學校教育
學校要注重營造溫馨、和諧的校園氛圍,創設多元育人環境,將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滲透在學校教育全過程中,營造真誠溝通的氛圍,引導每一名教師與學生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
1.關愛學生,密切關注學生日常表現
教師要用真心、真情對待每一名學生,密切關注學生在學校的日常表現,尤其要留意學生在校的異常表現。若學生一段時間內頻繁出現緊張、焦慮的情緒狀態,生理上也出現心慌、心煩的感覺,這可能是自殺意念產生的前兆。教師要定期與學生進行深入交流,了解學生的情緒狀態及學習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并圍繞孩子近況積極地與家長溝通,降低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
2.開展心理健康篩查
學校要定期開展心理健康篩查工作,明晰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識別有自殺風險的學生,確定預警名單,及時對學生的心理危機進行干預。學校心理教師要向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對學生的問題給予直接指導,助力學生健康成長。此外,學校可以組織多樣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如心理訓練、角色扮演、游戲輔導、心理知識講座等。學校要引導每一名學生學習心理健康知識,并在實際學習生活中學會運用心理健康知識,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3.引導學生發展同伴關系
青少年接觸的環境不僅局限于家庭,同伴間良好的人際關系也能夠為青少年身心發展提供強大的情感支持。教師應及時在人際關系方面給予學生積極的引導,引導學生以開放的態度積極交友。學校可以通過運動會、班會課、素質拓展活動、社團活動等多種形式,引導青少年掌握人際交往的技巧,發展同伴關系,降低產生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的風險,降低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
4.幫助學生學會合理表達情緒
教師要引導青少年認識到,情緒是正常的人類體驗,無論是開心、緊張、焦慮或憤怒,都是自然的情感反應,需要正視自身情緒變化,學會合理表達情緒。心理教師可以通過心理課、心理社團等多種形式,帶領青少年學習冥想、正念、漸進式肌肉放松等技術,幫助青少年在面臨負面情緒時保持冷靜,避免在情緒高漲時做出危險行為。教師還可以引導青少年通過寫情緒日志的方式記錄自己的情緒變化,明確情緒的觸發因素。或者鼓勵學生定期進行自我反思,記錄情緒變化及有效的應對策略,逐步提高自己的情緒調節能力。如果情緒問題影響了個人生活,要勇于向心理教師尋求幫助。
參考文獻
[1]余思,劉勤學. 青少年身體不滿意與自殺意念的關系: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19,35(4):486-494.
[2]袁婷,范雪菲,陳網妮,等. 青少年抑郁情緒與自殺意念的關系:失眠的中介作用[J]. 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24,51(4):1100-1103,1115.
[3]Pokorny A D. A scheme for classifying suicidal behaviors[M]. In the prediction of suicide,1974.
[4]俞國良. 我國學校心理健康狀況與教育效能的基本估計:調研證據[J]. 基礎教育參考,2023(9):3-14.
[5]Mann J J,Waternaux C,Haas G L,et al. Toward a clinic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psychiatric pati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99,156(2):181.
[6]Ciarrochi J,Deane F P,Anderson 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2,32(2):197-209.
[7]Gossop M. Alcohol in suicide attempts and completions[J]. Psychiatric Annals,2005,35(6):513-521.
[8]曾晉逸,郭成,劉鑫,等. 親子關系與小學生抑郁的關系:學業壓力的中介作用與心理素質的調節作用[J]. 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3,45(12):12-19.
[9]熊茗伶,王泉泉,熊昱可,等. 感知到父母施加的學業壓力對不同性別青少年心理適應的影響:自我韌性的保護作用[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24,40(4):542-550.
[10]Zubin J,Spring B. Vulnerability:A new view of schizophrenia[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77,86(2):103-126.
[11]Liu X C,Tein J Y,Zhao Z T,et al. Suicidality and correlates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of China[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2005,37(6):443-451.
[12]Liu X H. Parenting styles and health risk behavior of left-behind children: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2020(29):676-685.
[13]劉思含,伍新春,王歆逸. 父母教養方式的潛在類別及其與青少年學習投入和焦慮癥狀的關系[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23,39(5):673-682.
[14]Benatov J,Brunstein K A,Chen-Gal S.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ssociations to suicide behavior:A longitudinal study[J]. European Child Adolescent Psychiatry,2022,31(9):1353-1360.
[15]劉峻君,何曉燕,李松,等. 社交回避與青少年自殺意念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 心理與行為研究,2023,21(5):675-681.
[16]肖水源,楊洪,董群惠,等. 自殺態度問卷的編制及信度與效度研究[J].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9(4):250-251.
[17]張緯武,胡春梅,李方珍. 家庭因素對我國中職生非自殺性自我傷害行為的影響研究——基于感覺尋求和沖動性的中介效應分析[J]. 教育科學研究,2024(3):51-59.
[18]胡春梅,何玲玲,潘其蘭. 基于雙系統模型理論的青少年攻擊行為積極教育策略探析[J].教育科學研究,2023(8):11-17.
[19]蔣舒陽,劉儒德,馮毛,等. 自尊與中學生問題性手機使用:社交焦慮和逃避動機的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學,2024,47(4):940-946.
[20]李佳憶,郭成,陳帥,等. 親子關系與中小學生自殺意念的關系:自尊的中介和心理素質的調節[J]. 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3,45(12):36-43.
[21]Segal Z V,Teasdale J D,Williams J M,et al. The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adherence scale:Inter-rater reliability,adherence to protocol and treatment distinctiveness[J].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2002,9(2):131-138.
[22]Flotskaya N,Bulanova S,Ponomareva M,et al. Self-identity development among indigenous adolescents from the Far North of Russia[J]. Behavioral Sciences,2019,9(10):106.
[23]崔愛琳,張珊珊. 累積生態風險對留守高中生自殺意念的影響:生命意義感和心理痛楚的鏈式中介作用[J]. 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2024(4):14-20.
[24]Zhang Y,Xu W,McDonnell D,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subtypes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s:The mediating role of maladap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J]. Child Abuse amp; Neglect,2024(152):106796.
[25]黃雅梅,馬健生,張宏娜. 童年創傷對自殺風險的影響:神經質人格和抑郁的鏈式中介作用[J]. 中國特殊教育,2021,5(4):58-64.
[26]宋雨亭,于萍,栗克清,等. 童年期創傷對青少年抑郁癥患者非自殺性自傷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 心理月刊,2024,19(1):17-20.
[27]Goldhammer H,Crall C,Keuroghlian A S. Distinguishing and addressing gender minority stres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symptoms[J].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2019,27(5):317-325.
[28] Surace T,Fusar-Poli L,Vozza L,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al behaviors in gender non-conforming youths:A meta-analysis[J]. European Child Adolescent Psychiatry,2021(30):1147-1161.
[29]張耀華,徐敏,黃云云,等. 心理韌性緩沖壓力生活事件與青少年學業倦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J]. 心理與行為研究,2024,22(1):123-129.
[30]肖松齡,王怡,彭春迪,等. 大學生心理韌性與自殺意念的關系[J]. 心理月刊,2021,16(14):38-40.
[31]Kim S M,Kim H R,Min K J,et al. Resilience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Korean workers[J]. Psychiatry Investigation,2020,17(2):147-156.
[32]田雨,丁洪君,郭宗新. 大學新生負性生活事件與手機成癮的雙向關系:領悟社會支持的作用[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25(4):579-588.
[33]顧紅磊,黃佳,李家成. 同一性混亂與青少年自傷的關系:疏離感的中介作用和情緒調節困難的調節作用[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25(1):126-134.
[34]林琳,劉俊岐,楊洋,等. 負性生活事件對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影響——反芻思維的中介作用和氣質性樂觀的調節作用[J]. 心理與行為研究,2019,17(4):569-576.
[35]Zhu Z G,Tang W C,Liu G Z,et al.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uzhi on suicide idea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upport and friend support[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1(11):632274.
[36]楊克飛,袁秋雨,張文俊,等. 非自殺性自傷行為青少年的應付方式和父母養育方式[J]. 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24,51(4):1110-1115.
編輯/張國憲 終校/黃瀟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