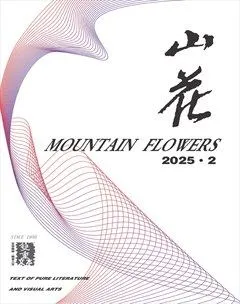亡蟲
1
蛇蟲百腳,在自己的角落,正是這些怪異的細節讓村莊充滿秘密。平原太坦蕩了,除了草木和屋舍沒有起伏可言。像南角墩這樣的高地,也被這坦蕩鋪陳得一馬平川,所以細節就變得珍貴,瑣碎的事物里藏著驚天動地的情緒——這是一個平原地區住民所有想象力的介質。
但有些蟲亡了,要到城市動物園才能看見畏縮的活體或者僵硬的標本——它們以一種沒有情緒的方式茍延殘喘。
土虺蛇大概曾是村莊里最惡毒的動物。一個良善坦蕩的地方,就是毒辣都不抵別處的。大概草木萬物也因為泥土不同而生出了各異的秉性。就像一個好人,連個像樣的惡作劇都做不來——這當然也是一種頑固的自認。沒有秘境的坦蕩是大地的一種恩情。如今的村里好像很少再有被蛇咬的消息了。過去據說人們有一個很古怪的方法治療蛇毒,用糞便去泡,但沒有人真正見過。不遠的村子里有人家有一種祖傳的治蛇毒的手段,但也少有本地人問津,后來他們還在城里開了診所——有些辦法的靈驗,是茅山上的菩薩,照遠不照近。那些密制的草藥對于村莊來說是無效的。
無數的蛇還在過往的角落里潛伏著。有一次深夜醒來,我猛然發現屋頂有瑩綠的目光。我萬分地無助和恐懼,好像它已經盤算好了要一躍而起。我害怕屋子里的黑夜,那是由來已久的事情。那些深夜是空洞的,虛無得讓疲憊都無以抵消。很多時候一覺醒來,聽見廣播還在響著,本來以為天明已經消弭了長夜,卻偏偏還有無助的時間要去對抗。那時候總是在夜間播一個廣播劇,總有一個女孩在不停地呼喊。我后來才知道那是沈從文的《邊城》。在那些荒蕪的深夜里,這聲音讓人覺得虛空。身體還是迷糊的,在黑暗中摸索著那細瘦的燈線,卻一下拉斷了,讓人滿心懊惱。找不到鞋子的我,又跌跌撞撞去拉廣播線。廣播終于閉口了,沉寂間我抬頭看見了屋頂的蛇。
父親后來堅決否認了我的說法。我說得太堅定了,他就輕描淡寫地說:“有也是家里的蛇,是捕老鼠的,并不傷人。”他不知道我的恐懼,我連放聲大哭都不敢。他是見過大蛇的,還講過很多關于蛇的故事。他的祖父是個好賭的人,據說成日帶夜地打一種紙牌,牌上有很多古怪的圖案和表情,實在令人恐懼。那種牌叫做“看麻雀子”,比這名字更怪異的事情,是他有一次夜里打牌總是覺得脖子癢,便在伸手沾唾沫摸牌的時候,順便用手指摸摸后腦勺。村里人認為吐沫是能消毒的——等待牌局結束了,轉身看見一條蛇死在了身后。我覺得這個故事很不可信,但父親認為這是確鑿無疑的事情。后來他講到自己的祖父過世了,多年后又遷移墳墓,朽壞的棺材板下也有通紅的蛇。我以為這一點可信——我見過冬天里在墳墓邊挖蛇的外地人。可他又說那墳塋里還有一對金泥鰍,一見陽光就飛了。他的這些故事詭譎得像蛇的魅影。他堅信這些都是家蛇,它們是家庭的一部分。
某次他出了后門,一條菜花蛇從屋檐掉在了他的脖子上。那時候的屋子都是空洞的斗子墻,蛇蟲就在里面出沒。他也沒有大叫,而是把那蛇捉住了用口袋裝上。這是一條大蛇,他覺得能賣一個好價錢,就趕緊騎著車去了鄉里。鄉里有飯店是收這些野貨的,這時他好像又忘記了自己關于家蛇的說法。他在去的路上遇見了一個熟人,停車說了幾句話的 工夫,那蛇竟然跑了。他也不感到沮喪,又騎著車子回來了,就像河里偶然游過的水蛇一樣淡然。他后來說又看到那蛇出沒在屋后的菜花地里,這大概也不大可信。不過蛇捕食老鼠是常見的,那些惱人的家伙被蛇吞下去時,在蛇肚子里隆起很高,就像是對世界的怨言一樣。
老鼠在空墻中埋伏著,夜色降臨后就猖獗起來。饑餓能激發萬物的惡行。人們畏懼這些邪惡的物種,連名字都不敢叫,只說是“老啃”,好像是怕他們聽懂了村莊的埋怨,尤其在年節的時候,這些名字更是一種禁忌。人們造屋的時候知道蛇鼠必然會到來,便會在墻上留一些寬容的空洞,這樣它們就不必去破壞屋舍了。更有一些地方把這些邪惡的家伙供奉起來,是為號神。城里的當鋪里就有這種神位,火神、號神和財神一樣都成為供奉。對號神的供奉有些助紂為虐的意思,雖然事出無奈但畢竟顯得畏縮。
村里人好像要多些主見和決斷。人們也知道貓的能力不足以對付這些龐大的族群,就想出了別的方法來對付它們。三叔見串鄉賣老鼠藥的生意很可喜,也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了一些藥物。他蹲在離屋子很遠的地方把蘿卜刨成細絲,將那些無色無味的藥物攪拌其中,然后去很遠的地方兜售——好像是覺得本村的老鼠得到了消息不會上當似的。秋收后,每家都要滅鼠,很多老鼠死在角落里,留下惡臭的味道。除了老鼠藥,人們還用鼠籠或者粘鼠板。捕獲老鼠之后,它們那種凄慘鳴叫令人不安。古人當然也是要對付老鼠的,人們立秋之后便要“穹窒熏鼠,塞向墐戶”。我一度覺得這種方法很有些詩意——殺戮總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相安無事的寬容會更有意境。但是我天真了,鼠類何嘗有過什么善行?它們餓極了會瘋狂起來。
父親本是有個姐姐的,饑荒的時候發熱在家,夜里迷糊中被老鼠活活地咬死了。這件事情我是相信的,因為多少個夜里,老鼠都在床頂上肆意折騰,有時失足掉下來還會砸在臉上。它們倉皇地從人臉上奔過,那種滋味是無盡的恐慌,比黢黑的夜更令人戰栗。這些無有善意的東西,蛇鼠一窩地折磨著夜色,讓村莊曾有無數的戰戰兢兢。
2
父親一直養著鴨子,他對自己的這點祖傳的“事業”很有些深情。他把雛鴨圈在家中的堂屋里,它們散發出令人掩鼻的氣味。他很有些不以為然地說:“沒有這些鴨屁股哪有人的一張嘴?”這種說法很粗糙,但好像也有點道理。他滿是酒味的嘴里總是能吐出一些別樣的話語來。奶奶會翻著眼睛說他:“你是三斤重的鴨子二斤半的嘴。”他便不說話了,獨自出門挖蚯蚓去。村里叫蚯蚓作寒蛇,它們在潮濕的泥土里隱居著。寒蛇在泥土里,但看得出頂上松軟的碎土,人們便由此知道它們的所在。那些細碎的泥土是微型的堡壘,細致得熨帖,但又正是符號一樣的細節,暴露了它們想要隱瞞的行蹤。寒蛇是一種有些哲學意味的存在,潛伏在黑暗的地方,又以最簡潔的形式表現著自己的強大。這種強大能夠不斷地延伸,又不依賴于繁復的形式。這是人們難以懂得的道理。因為形式正是村莊或者世界所追求的。它甚至沒有表情,但似乎又有太多無需要言明的內在,這樣的隱居才真正是極簡而至真的。這也許是這種動物存在的深刻的意義,而它又從來不在乎這些意義——煩惱的是心存雜念的人們。
寒蛇平素只被用來釣魚,也有用以做湯給婦女催奶的。父親挖寒蛇給他的鴨子吃,吃了活食的雛鴨長得歡快。對于養鴨子,他有一套自己的辦法,這大概是他唯一從上輩得來的遺產。鴨子長成之后也會自己去找寒蛇吃。雨后的土地顯得活躍而不安,水喚起了村莊的心思。寒蛇被蠕動的泥土暴露了行蹤,它們成為了那些聒噪口舌中的活食。它們掙扎著,安于黑暗的品格無以拯救一切。母親還有一種很有意思的方法來對付這些暗黑者。本來韭菜是不用施肥的,這是一種很自律的菜蔬。寒蛇的潛入會成為生長的障礙,農人們在播種前便會在泥土中摻雜毒辣的藥物。母親卻有自己的經驗,她用糞水對付這些隱蔽的生靈,眼看著它們默默地離開。
鴨子夏秋之際就羽翅豐滿了。公鴨的翎毛透出油綠時,中秋節就到了。中秋前后的村莊,有一種重要的風俗——“送節”,實際多是“催節”,訂婚的男方家去女方家催促,會送去鴨子。鴨就意味著“押”。一件事要押著做就是著急了。父親會照例殺一只雄鴨子過節。這些吃活食的鴨子鮮嫩可口。這可能只是一種幻覺,但被父親描述得有些出神入化。他多次講過一件事情:過去有個人吃了公鴨,飯后沒有洗臉,午睡的時候口舌間的鮮味引來蜈蚣鉆進鼻孔,最后殞了命。這種怪異的故事在村里很多。這是一種很殘忍的修辭,比那些巧言令色的話語更加迷人。用殞命這樣極致的結果來證明一件事情的可靠性,是無比決絕的態度。蜈蚣這種邪魅的蟲子,在村莊的角落穿行,至于它的毒性,其實并沒有多少實證,偶爾有些意外的傷害,人們也并不十分重視,有些人皺皺眉頭用唾沫擦一下便忘記了。有些講究的人,摘些蒲公英的葉片嚼碎了外敷,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道理。
人們畏懼這種蟲子,大多是因為被渲染的傳說。那一陣子大家都聚集在老正松家看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這部電視機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那些信號很不穩定的夜晚,他的院子里總是聚集了一幫人,等著那些奇異故事的開始。關于蜈蚣精的議論,讓蜈蚣似乎變得更加邪惡了。每每夜里回家,總感覺腳邊會有蟲子盤旋著。其實,它不經常出現在生活里。聽說它還是名貴的藥物,但人們逮著了都是默默地將其斬成幾段,好像是斬殺了蜈蚣精一樣解恨。村里有些“藥罐子”把中藥的殘渣倒在路口,有時藥渣里也會看見蜈蚣的影子——讓人一時也想著上去揮劍斬幾段才能放心。
膽大的孩子們也去找這些蟲子,但它們敏捷地在暗黑處走過,不會留下太多痕跡。孩子們翻起潮濕處的磚頭,會有一種與蜈蚣形似的蟲子懶散地扭動。那種蟲子被叫作百腳,但并不是蜈蚣。它們數不清數量的細足更加怪異,但并沒有什么危險。往往正在端詳著的時候,一邊的雞會奔上來果斷地把它啄食下去,把難得一點的興致都吞沒了。據說這些蟲子能從雞嗓子里穿過肉身鉆出來,但誰也沒有見過這種場景,最終雞和人一樣都淡定地走開了。潮濕的磚塊下還有那種黏膩的鼻涕蟲。它們害怕光亮,只在夜里鉆出來在潮濕的地方蠕動。這些蟲子與村莊相安無事,偶然在水缸邊沿留下一點游走的痕跡,比起生活的嘈雜,只是輕描淡寫而已。
人們有時候也會尋求一些蟲子的幫助。它們都是可以藥用的,但這是醫生們神秘的認知,對于村莊里的大多數人而言,它們多數時候是沒有實用價值的。像蜘蛛這種動物,只有到春節前打掃的時候才會被細心的人除去,也有人會刻意留下它們。這是一種被認為有些神性的蟲子,人們叫它喜蛛。它們把張揚的網架在夜色里。那些現實而又虛無的網張在生活里,有些還沾滿了露珠,是一種很唯美的存在。它們的詩意大多數時候是無人過問的,覺得礙事了,人們只揮手拂去,并不怎么在意。蟲子驚恐地從半空中掉下來也不至于殞命,它們匆忙地逃回自己的角落。那些在網上喪命的蟲子已經失去了對冷暖的感知,風吹過的時候卻還在瑟瑟發抖。
受了驚嚇的孩子,老人要給他們“叫”一下。這種事情被老人們弄得很莊重,要把蜘蛛包在紅紙里放在孩子身上。這讓蟲子變得有些詭異,其中究竟什么道理,也無人去追究。
3
我們今天念叨這些蟲子,并不是站在鄉野深處。我們蜷縮在城市的角落,像失去故鄉的蟲子。城市里難得見到自在的蟲子,我們也不再愿意回鄉去尋。我記下的那些細節就像是悼詞,而悼詞是為了離別而作。
還有一些聒噪的蟲子,讓村莊變得歡樂,其實也是過去的一段段悼詞。春末的時候,河水就情緒飽滿地鬧騰起來。對于大地的鬧騰,有一個很古典的詞語,叫作“作伐”。這個詞本來是說幫人做媒,后來延伸出很多不安的意思。生長本就是不安的事情,躁動的舉止就被人們稱為“作伐”。比如黑魚散籽了,就像是河流作伐一樣,一時間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活躍的情緒。正是這種躁動讓土地生機勃勃。蝌蚪比黑魚更加活躍,它們的隊伍聚集得有些壯觀,大軍壓境般逼近河岸,等待著時節給它們的號令。它們是迫不及待的,一夜之間就登陸到土地上,在滿是塵土的世界里奔波起來。這種密集的活躍令人感到不安,甚至充滿了恐懼的情緒。孩子們撈幾頭回來養在水里,過幾日便又倒回到河水中去。它們是帶著未知的——孩子們不敢確定它們最終會變成青蛙還是蛤蟆。它們的腿慢慢地長出來,拼命地尋找屬于自己的世界——那種熱烈讓土地顯得心神不寧。
聽說蝌蚪也是可以藥用的。有些孩子燙傷了,老人們便用這些蟲子外敷,這種滋味比疼痛更令人煎熬。有一陣子孩子們總是得一種被稱為“害大腮”的病,人們也是用蝌蚪去外敷,病愈的時候還會用墨汁涂出一個圓來,那種黑色和蝌蚪的顏色一樣怪異。沒有蝌蚪的季節,人們還有一種更古怪的方法——用新鮮的蛤蟆皮敷貼,那也是很奇異的體驗。
青蛙長成后那些古怪就退去了,它們在四野里歡快地叫起來。蛙聲一片就像對稻田的催促,土地在努力地拔節向上。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叫聲也會成為一種險情——人們會在夜晚去尋找這些聲音。人們說找青蛙而不是說抓青蛙,這是一種很有些意思的說法,把那種緊張感轉化出歡快的情緒,就像是找人。有人來收購這些活躍的青蛙,甚至就連蛤蟆或者螞蟥都是能換來一些生計的。螞蟥的價格會高出一般的蟲子許多,但大概因為它有在人腿上吸血的劣跡,所以人們并不十分待見。在村莊里,有時候價格或者價值并不完全是人們判斷的依據,就比如蛇也總被認為是怪異的,一般人并不去捉。缺少食物的時候,人們也會去吃這些鮮活的肉身,那是一種無奈。及至后來生活好起來,在城里見到一些被認為是美味的食物,農人們只會不屑地說——這些東西過去都是雞鴨鵝吃的。他們其實也吃過,不過心里是一種不同的念頭,就像是母親經常說的:它們也是一條命。
這些命也是村莊的命,沒有它們,土地無法延續生機。它們在流水里、泥土上、縫隙間、天空中,無所不在地存活著,讓村莊的動靜更加立體。比如蟬從泥土抵達天空,就像是一趟修行,在村莊垂直的世界里留下自己的苦行。它的每一種痕跡都被人們關注著,依次熬過季節的一道道的關口。聽說北方的人是吃蟬蛹的,但在平原上這是少數。這也許是因為平原的物產太豐富了,但更是因為人們的樸素,對于入口的食物總保持著某種警惕,這也是為自律和美感所左右的。
蟬糾纏著樹木,連影子一樣的蛻都是如此。蟬的叫聲也糾纏著村莊,成為夏天的一種標識。孩子們也學會一種糾纏的方法——用蜘蛛網去綁架它們活躍的翅膀。還有身手敏捷的孩子,能夠舉手按住那些歡快的聲音。這種背后下毒手的方式,很有螳螂捕蟬的意味。捕獲的蟬被掐去了翅膀,從此它們失去了天空,孤獨地附在帳子上不再愿意出聲。據說沒有了露水它們就不再鳴叫了,這種說法很是值得懷疑。因為同樣是蟲子,那種青色的大蟈蟈被控制在股掌之間的時候,依舊會沒心沒肺地嘶鳴。也許蟬有自己的脾性,它們失去了天空就寧愿失聲不語。有一種體形壯碩的蟬——據說只有這種褐色的家伙才真正叫做“蟬”,其他聒噪的本是普通的“黃娘”。這種真正的蟬遠離人間,它們在樹木的最高處,發出一種響亮而冷靜的叫聲。我以為這種叫聲是朝著云天的,所以也沒有人愿意去把它們捉拿到人間。孩子們寧愿去抓那種外形古怪的甲蟲,那種頂著犀牛角一樣的蟲子鉆在被破壞的樹干里,身上有樹木腐朽的味道。還有那種披著盔甲一樣的“昂猴子”,它們有一對驕傲的觸角,讓人想到孫行者的裝束——或許人們就是按照它的樣子,想象出了那個頑劣的神仙形象。它的叫聲無以模仿,就像河里釣上來的昂刺魚,滿腹牢騷地咕噥著。這蟲子很愛干凈,它們趴在苦楝樹或者桃樹上。這兩種樹有很自我的味道,一般蟲子也不愿意靠近。
有蟲子的地方才有人間的樣子。它們也像是人群,其間也有不安或者惱怒。蟲子隨處可見,它們讓村莊的情緒變得完整,而沒有蛇蟲百腳的日子是不周全的。當大風吹得土地一片寂靜,蛇蟲們都酣睡了,它們等待著一個又一個重新而來的開始——城市里沒有這些,水泥掩蓋了泥土,蟲子亡去的地方無有人間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