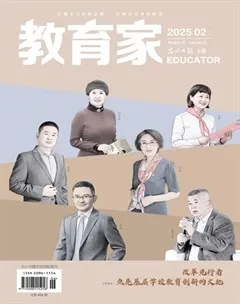魏瑞江:讓課堂緊緊貼著孩子的心



魏瑞江,天津市河西區教師發展中心美術教研員,正高級教師、特級教師。義務教育藝術課程標準修訂測試組成員,教育部“國培計劃”專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天津美協水彩畫專業委員會副會長。
人民教育家于漪認為,好的課堂應該是將知識傳授到學生的心中,而非僅僅停留在黑板上?。她曾說:“我不斷地反思,我一輩子上的課,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上到學生心中的。”
天津市河西區教師發展中心美術教研員、正高級教師、特級教師魏瑞江一直將于漪老師當作教書育人的榜樣力量。他努力讓課堂緊緊貼著孩子的心,把“將自己和學生同視為藝術家而進行平等的藝術對話”作為課堂追求,引領學生以美術特有的方式表達情感;通過藝術教育教會學生以自己的方式實現心靈與世界對話。
有“狀況”才是真實的課堂
有美術老師聽完魏瑞江的公開課后寫下這樣一段話:“魏老師的課堂是真實的,他會根據學生在課堂中的變化隨時作出調整。這種隨機應變的能力,離不開他扎實的專業技能和平時課堂中的留心觀察與細心記錄。魏老師的課堂難嗎?不難。難得的是,他真正從學生實際出發,把學生真正當作兒童,而不是陪老師表演的演員!”
一直以來,多數公開課都設計得非常完美,準備得非常精細,有評課專家說“甚至連針都插不進去”。公開課多是借班上課,但魏瑞江從不擔心在陌生的課堂上發生“狀況”。在他看來,有“狀況”才是真實的課堂,才能與學生建立真實的聯結。“當課堂偏離某種‘設計’的時候,往往更能收獲預設不到的東西,引領課堂不斷走向深處。”
作為教育部“國培計劃”專家,魏瑞江會受邀到全國多所學校上公開課。有一年,他到“國培計劃”培訓基地浙江師范大學,給一所小學的二年級學生上了一堂公開課,真實、真誠、真情的課堂互動,使師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之后又連續兩年受邀給這個班上課。但由于種種原因,第四年、第五年沒有成行,這個班的孩子竟集體向學校提出申請:“馬上就要小學畢業了,我們很想念魏老師,能不能再請魏老師給我們上一堂課?”
“他們班主任把這件事轉述給我時,我的心頭一陣溫熱。沒想到只有幾面之緣的孩子們,竟對我有著這般的惦記和想念。”于是,就有了魏瑞江給這個班上的“最后一課”。
備課期間,魏瑞江跟他們的美術老師說起自己正著手研究多肉植物,希望借這次課讓孩子們幫他“輔導”一下這方面的知識。走進課堂那天,他看到孩子們的課桌上擺著各種各樣的多肉植物,有一名學生還專門做了PPT,等他分享完,魏瑞江就開始進入正課。
“孩子們準備的紙張特別大,我讓他們裁成豎條,并提示他們可以疊成格子,想畫多大就畫多大,他們很快‘上鉤’,大多疊成了很小的格子,不一會兒就畫完了。我說:‘其實你們還沒有畫完,多肉是會長大的。’孩子們開始‘反攻’我:‘魏老師,你是真不懂多肉,它們是長不大的。’我接著說:‘在藝術的世界,完全有可能。’接著引導孩子們攤開紙張繼續畫開來,隨后我們還找來顏料用水稀釋后噴上去,在顏料的暈染下,孩子們筆下的多肉植物瞬間‘長大了’,課堂也跟著興奮起來。”
最后,魏瑞江向孩子們提議把當天畫的這幅畫送給學校留作紀念,在一片贊同聲中卻聽見有個孩子嘟囔了一句“不想給”。魏瑞江將目光投向他,看到他將那幅畫抱得特別緊。“聽說你不愿意把畫送給學校?為什么呢?”孩子略帶哭腔答道:“我想拿回家自己保留。”魏瑞江說:“你感動了我。是不是因為這是你畫得最好的一幅畫?”他使勁點了點頭。“老師要給你鞠一躬,向你真誠道歉。因為老師們習慣了收作業,學生們也習慣了交作業,但是在收和交的過程中,我們忘記了藝術。”魏瑞江的這一行為感動了所有在場的老師和學生。后來,基于這堂課的視頻《老魏的課為何讓我們流淚》還被傳至網絡,一度感動了全國眾多美術老師們。
一課20年,從“教的技術”到“教的藝術”
在我國課程改革的20年間,課程目標經歷了從“雙基”到“三維目標”,再到“核心素養”的演變,這是從“教書”走向“育人”的三個不同階段。
魏瑞江以執教《寫生——手》這一課,“見證”了課改歷程。
在“雙基”時期,他更多是讓學生關注手的結構特點,學習用線條寫生的方法,重視美術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與訓練,并隨時監控學生掌握的程度。
到了“三維目標”時期,他的教學理念發生了改變,不僅僅把手的寫生技能技巧看作教學目標,還關注到學生內心的感受和情感的表達,更強調學生行為習慣的養成和價值觀的形成。教學中,從畫握拳的手到畫執筆的手,讓學生在繪畫中逐步發現在錯誤的執筆姿勢下自己的手變丑了,甚至出現了手指畸形……他由此指出錯誤的執筆姿勢可能帶來的諸多危害,并引導他們改正。這充分體現了美術教學中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進入“核心素養”時期,魏瑞江的教學理念再次發生改變。在一次“核心素養時期下的美術教學研討會”上再次執教這一課時,當他面對學生畫出的因執筆錯誤而扭曲的手,努力使教學達到預先設定的育人環節(也就是他馬上要進行“教育”的環節)時,卻欲言又止,最終選擇了放棄。“因為那一刻我從心底里更加理解學生、包容學生了。學生的習慣已經養成,他們十分明白,錯誤的執筆姿勢絕不是好習慣,只是此時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學生去思考,我相信他們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學生們紛紛在畫作旁寫下一段段真情的“告白”——“錯誤有時候是另樣的風景,畫畫是讓心靜下來”“這堂課,我從一開始的興高采烈、認真專注,再到最后的沉默、反思”“手陪伴我一生,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們在生活中逐漸遺忘了本來的習慣,這個社會的浮躁,讓很多人遺忘了最初的美好,愿通過這堂課你我可以不忘初心”,魏瑞江的教學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核心素養階段。
一課上“百遍”,更要“百變”
在多年的美術教學中,魏瑞江觀察到兩種現象。一是當學前兒童進入小學美術課堂后,就很難看到兒童繪畫的本來面目,幾乎所有作業都成了簡筆畫,或者是半成品。二是美術老師給予學生的知識與技能不僅沒有幫助學生自由表現,反而成為束縛他們想象、創造的枷鎖。于是,他努力探索既順應兒童天性發展又能發掘其潛能的美術創意教學法,將學生置于課堂教學中心,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挑戰自我、自主表達,將技能、藝術和教育進行完美融合。
在一堂最平常的《畫大樹》的美術課上,魏瑞江提出“我們是先畫樹干,還是先畫樹冠和果實”這一問題,引領孩子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針對大家的各種表述,他在大屏上呈現了“簡筆畫”的大樹圖式,激發他們繼續發表自己的意見。在認真聽取了孩子們的回答后,他繼續追問:“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避免畫成簡筆畫呢?”他希望通過改變學生思維,引導他們轉換視覺觀看和美術表現,把培養核心素養的目標落實到教學活動中。“我們可以嘗試先畫果實,再畫樹冠,后畫樹干”,這一學習任務的提出,為孩子們自主探究學習打開了新的思路。
《寫生書包》是小學階段一節平淡無奇的美術課,如何把它上得波瀾壯闊?魏瑞江以“挑戰不可能”為情境,以5分鐘畫完一個書包為任務,以25分鐘寫生5個不同角度的書包為挑戰內容,重新設計了這堂課。課堂伊始,魏瑞江提議,在畫之前可以先將紙疊出格,6格或8格都行,當然也可以不疊格直接畫。在孩子們動手開工后,他開始從中觀察,有多少學生不疊格,有多少學生疊6格,有多少學生疊8格。“這背后是孩子們學習習慣和性格的一種映射。隨遇而安的不疊格,做事認真的疊8格,追求卓越的疊6格。但這還不算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確切統計之后,引導孩子們挑戰改變,讓不疊的疊8格,讓疊8格的疊6格,讓疊6格的不疊,以此發展他們的創造性思維。”
這節課的最后,魏瑞江對孩子們說:“現在很多家長抱怨孩子們的書包太沉重了,甚至有不少家長替孩子背書包。的確,你們的書包是沉重的,但你們可知書包里藏著父母無私的愛、老師溫暖的關懷和祖國殷切的期待。所以,希望你們勇敢地背起書包,面對挑戰。”
走百校、上百課
為了回饋社會,魏瑞江自2011年啟動了“走百校、上百課”活動,一是推廣、驗證“美術創意式教學”的思想和方法,二是以感恩的情懷回報教育,三是希望上100節不重復的美術課以展現當代名師的風采。
他強調,“課堂在變、學生在變、知識在變、時代在變、自己也在變,教研員要經常到課堂中去獲取有價值的教育信息,置換自己陳舊的經驗。給教師方法,不如升級教師的思想,因為方法再好也有用盡的時候,而升級思想才有可能徹底改變教師。一位教師的思想升級了,即使沒有方法也會創造出來方法。”
“每個學生都希望走進他們教室的老師是一位名師。那么,為了學生的期望,就努力做學生心目中的名師吧!”在魏瑞江一本著作的扉頁上印著這樣一段話。為了提高工作室成員的教學水平、激發名師感恩教育的情懷,他將“雙百計劃”納入工作室項目,針對成員提出了“一課上百遍、百課不重樣”的構想,要求成員三年一課上百遍,領銜人三年上百課、百課不重樣。恰恰是這一近乎苛刻的要求,讓每一位成員在教育教學研究方面嘗到了甜頭,找到了研究的樂趣,教學研究水平有了顯著的提升。工作室成員胡渤海在體會中寫道:“一課上百遍,是一錘百煉,上百次磨礪,也就意味著有百種千種上法。一課上百遍,是一生的真情不變,一輩子追求的人生大課。”
回望自己30余年的教育人生,魏瑞江用“三心二意”來概括。“三心”指的是——
一顆感恩教育的心。每個人的成長都凝結了老師和父母的關心、幫助、指導、支持,所以要心懷感恩。同樣還應感恩學生,因為他們向我們學習知識,學習做人。唯有把這種無以為報的感恩銘記心中,并化作前進的力量投入摯愛的教育,才能更好地與老師們一同探索藝術教育規律,為學生創造出高質量的美術課堂。
一顆畫家的心。作為美術教師,不見得都要追求成為一名畫家,但要有畫家的情懷,要像畫家那樣從觀察人、事、物的角度獲得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
一顆教師的心。具有教師職業的特質,這是超越父母的愛,是不帶任何偏見的教師特有的愛,其中包含著愛與責任。
強調“二意”則是因為,唯有在教育教學工作、學習生活、藝術創作中有創意,教育人生才有意義。
“我從教的目標不是培養畫家,而是培養喜愛藝術的各行各業普通人。我在很多地方遇見過自己曾經的學生,美術課課時不多,這些學生竟還記得我、記得我的課,這就足夠了。”在魏瑞江心中,好的教育就是你曾和學生說過一句話,當若干年后學生長大了,跟你見面時,還會再次提起它。這時,老師是幸福的,學生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