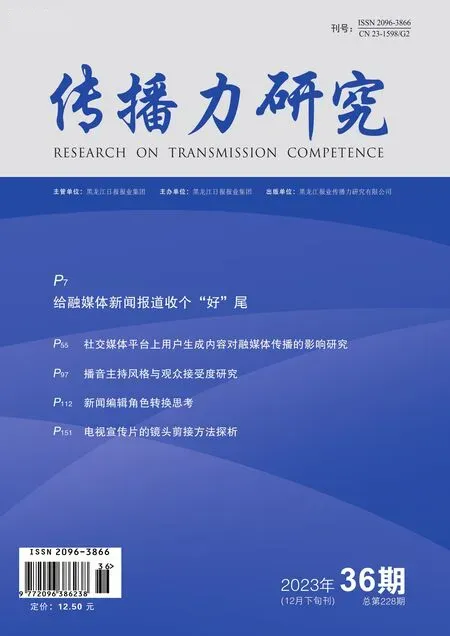探究媒體融合時(shí)代地方新聞短視頻的內(nèi)容生產(chǎn)與運(yùn)營(yíng)策略
◎倪曉爽
(太原廣播電視臺(tái),山西 太原 030001)
互聯(lián)網(wǎng)市場(chǎng)動(dòng)態(tài)發(fā)展中,數(shù)字原生態(tài)受眾成為消費(fèi)群,短視頻消費(fèi)規(guī)模隨之?dāng)U大,并呈現(xiàn)出移動(dòng)化和社交化的特征。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和社交媒體端口在飛速發(fā)展的現(xiàn)在,為現(xiàn)代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其中視頻也作為宣傳的有效形式受到關(guān)注與重視。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短視頻具有短小、快節(jié)奏、趣味性強(qiáng)等特點(diǎn),是互聯(lián)網(wǎng)內(nèi)容行業(yè)的全新增長(zhǎng)極。為了適應(yīng)市場(chǎng)發(fā)展趨勢(shì),地方新聞也開(kāi)始朝著短視頻的方向演進(jìn),結(jié)合媒體融合時(shí)代環(huán)境特征,大力探索地方新聞短視頻模式,但這也隨之面臨新的問(wèn)題,尤其是內(nèi)容生產(chǎn)和運(yùn)營(yíng)。本文分析新聞短視頻及優(yōu)勢(shì),總結(jié)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的發(fā)展困境,提出內(nèi)容生產(chǎn)和運(yùn)營(yíng)策略,緊跟時(shí)代發(fā)展特征,加快地方新聞模式的升級(jí)與轉(zhuǎn)型。
一、新聞短視頻概述
短視頻從2016年開(kāi)始逐漸興起,在后續(xù)的不斷發(fā)展中,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也總結(jié)了關(guān)于短視頻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以快手為例,人工智能系統(tǒng)對(duì)用戶行為做出自動(dòng)判斷之后,總結(jié)了“57秒”定義[1]。但其實(shí)不管定義的主體是平臺(tái)還是用戶,短視頻概念界定的維度均體現(xiàn)出單一性,即視頻時(shí)長(zhǎng),其中并不涉及內(nèi)容方面的標(biāo)準(zhǔn),也因此引發(fā)了一些行業(yè)內(nèi)的問(wèn)題。
第一,信息技術(shù)使視頻消費(fèi)的標(biāo)準(zhǔn)降低,人們對(duì)于視頻時(shí)長(zhǎng)也有更高接受度。所以,如果單純的將時(shí)長(zhǎng)作為“短視頻”概念界定標(biāo)準(zhǔn),并不能彰顯實(shí)質(zhì)性意義。第二,短視頻缺少內(nèi)容方面的標(biāo)準(zhǔn),導(dǎo)致出現(xiàn)很多動(dòng)圖與PPT形式的偽視頻,此類視頻補(bǔ)充了網(wǎng)絡(luò)流量缺口,降低了優(yōu)質(zhì)短視頻在平臺(tái)中的曝光度。第三,對(duì)于市面上的主流媒體,短視頻成本低,成為獲取流量的工具,各個(gè)短視頻平臺(tái)也開(kāi)始主打以流量為主的內(nèi)容戰(zhàn)。
綜上,界定“新聞短視頻”,建議不應(yīng)以時(shí)長(zhǎng)為唯一依據(jù),還需增加內(nèi)容標(biāo)準(zhǔn),以此展現(xiàn)出新聞短視頻在行業(yè)內(nèi)的應(yīng)用價(jià)值。
二、新聞短視頻價(jià)值與優(yōu)勢(shì)
(一)地方新聞生產(chǎn)模式得以升級(jí)
媒體固有工作模式主要為內(nèi)容生產(chǎn)模式,該模式以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專業(yè)生產(chǎn)內(nèi)容)生產(chǎn)模式為主,傳播內(nèi)容彰顯專業(yè)性,但是生產(chǎn)者時(shí)間、精力、視野范圍等均會(huì)對(duì)其帶來(lái)限制。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為大眾提供了豐富的話語(yǔ)權(quán),網(wǎng)民也轉(zhuǎn)變了身份定位,成為制作、傳播新聞?wù)遊2]。這離不開(kāi)融媒體的影響,調(diào)整了短視頻制作標(biāo)準(zhǔn),但也大量生產(chǎn)出失真的信息。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網(wǎng)民雖然可以制作、傳播新聞,但其不具備專業(yè)的篩選、處理能力,面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中海量資訊,很容易混淆,從而將未經(jīng)證實(shí)的新聞上傳到互聯(lián)網(wǎng)中,降低地方新聞媒體權(quán)威性。
相比之下,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的地方新聞短視頻,同時(shí)融合了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成內(nèi)容)和PGC,加強(qiáng)了媒體和受眾關(guān)系的協(xié)調(diào)性。換言之,由大眾負(fù)責(zé)生產(chǎn)原始新聞,專業(yè)媒體負(fù)責(zé)新聞內(nèi)容的篩選與加工,深入挖掘新聞內(nèi)容,并對(duì)其進(jìn)行過(guò)濾。如此一來(lái),便可以實(shí)現(xiàn)新聞生產(chǎn)模式的創(chuàng)新,更有利于體現(xiàn)出新聞短視頻的價(jià)值。
(二)完善融媒體產(chǎn)品鏈
媒體融合時(shí)期所采用的傳播技術(shù)、社交工具,使新聞供給、大眾需求更加緊密,這也引發(fā)了媒體新聞新舊傳播模式的對(duì)比。視聽(tīng)媒體的核心是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新聞信息傳播載體為視頻內(nèi)容賦予了生動(dòng)性和網(wǎng)絡(luò)傳播便捷性,而且這兩點(diǎn)特征也得到融合,對(duì)于廣大信息接收者而言,可以更好地滿足其閱讀中呈現(xiàn)的碎片化需求[3]。地方新聞短視頻在此基礎(chǔ)上更顯娛樂(lè)性、社交性,使傳統(tǒng)媒體進(jìn)入媒體融合時(shí)代之后,能夠進(jìn)一步提升其發(fā)展速度。在此背景下的地方新聞短視頻,使新聞產(chǎn)品鏈更加完善。
(三)新聞信息傳播呈現(xiàn)多元化
融媒體在信息化時(shí)代下飛速發(fā)展,為新聞行業(yè)環(huán)境帶來(lái)了新的轉(zhuǎn)機(jī),地方新聞報(bào)道信息傳播逐漸展現(xiàn)出多元化態(tài)勢(shì)。一方面,與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與普及有關(guān),即通過(guò)智能手機(jī)、電腦等設(shè)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負(fù)責(zé)信息傳輸;另一方面,則與當(dāng)下逐漸成熟的視頻網(wǎng)址運(yùn)營(yíng)有關(guān),為人們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信息。除此之外,傳統(tǒng)媒體在融媒體時(shí)代下,新聞事業(yè)隨之進(jìn)入到改革創(chuàng)新的關(guān)鍵階段,通過(guò)傳統(tǒng)媒體和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的整合,為地方新聞賦予了多元化特點(diǎn),這種多元化特征也體現(xiàn)在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的生產(chǎn)與運(yùn)營(yíng)中,滿足群眾對(duì)新聞信息的需求。
(四)地方新聞內(nèi)容傳播方式具有社會(huì)性
地方新聞報(bào)道短視頻在融媒體時(shí)代下,開(kāi)始與社交媒體合作,社交媒體在新聞行業(yè)內(nèi)得到廣泛關(guān)注,這也使得短視頻新聞受到廣大群眾的青睞。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生產(chǎn)與運(yùn)營(yíng)中,在新媒體的支持下,移動(dòng)互聯(lián)用戶數(shù)量呈飛速增長(zhǎng)趨勢(shì),其間也離不開(kāi)智能手機(jī)的幫助。傳統(tǒng)媒體的受眾群體往往在信息方面具有被動(dòng)性,但隨著新媒體與地方新聞的結(jié)合,視頻直播間平臺(tái)作為全新的溝通渠道,為新聞受眾提供了效率更高的新聞資訊,從而利用地方新聞的新媒體平臺(tái)進(jìn)行在線交流,這為地方新聞內(nèi)容傳播賦予了社會(huì)性。
三、地方新聞短視頻的內(nèi)容生產(chǎn)與運(yùn)營(yíng)面臨的問(wèn)題
第一,內(nèi)容來(lái)源不局限于單一的渠道,增加了內(nèi)容審核難度。以往的媒體新聞素材采集主要由專業(yè)新聞媒體工作者負(fù)責(zé),但是地方新聞短視頻素材與之不同,更多是由網(wǎng)民提供,很難完全保證真實(shí)性與專業(yè)性,而且也很難保證素材篩選與審核的質(zhì)量。
第二,內(nèi)容制作經(jīng)驗(yàn)少。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在前期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如果是主流媒體,在進(jìn)入媒體融合時(shí)代之后,為了能夠更加契合時(shí)代發(fā)展需求,必須關(guān)注到新聞內(nèi)容制作技術(shù)、制作方法的改變。例如技術(shù)應(yīng)用層面,短視頻在傳統(tǒng)媒體領(lǐng)域?qū)儆谛率挛铮苋菀自诠ぷ髦杏龅街谱鞣矫娴募夹g(shù)難題,如視頻編輯軟件操作不夠熟練,或者是對(duì)短視頻存在認(rèn)知偏差,只是在長(zhǎng)視頻基礎(chǔ)上進(jìn)行剪輯,形成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制作的專業(yè)性問(wèn)題[4]。另外,內(nèi)容生產(chǎn)中,主流媒體各自獨(dú)立,盡管也會(huì)有合作,但是只是局限于業(yè)務(wù)層面。互聯(lián)網(wǎng)與媒體行業(yè)結(jié)合之后,并未將傳統(tǒng)媒體制作新聞內(nèi)容存在的單一性問(wèn)題徹底解決,而是采用轉(zhuǎn)移的方式,使電視節(jié)目?jī)?nèi)容進(jìn)軍互聯(lián)網(wǎng)。群眾也作為地方新聞生產(chǎn)與傳播的一環(huán),主流媒體更加關(guān)注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的同質(zhì)化現(xiàn)象,這是主流媒體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需要重點(diǎn)攻克的問(wèn)題。
第三,短視頻內(nèi)容有明顯不足。以往生產(chǎn)新聞內(nèi)容,主流媒體比較關(guān)注內(nèi)容是否完整,這一點(diǎn)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有非常顯著的變化,特別是在信息碎片化的現(xiàn)象下,媒體新聞內(nèi)容篇幅較短,更滿足受眾的碎片化需求。由此,媒體為了解決該問(wèn)題,開(kāi)始專注于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表達(dá)方法[5]。地方新聞短視頻時(shí)長(zhǎng)以一分鐘為主,而且要在有限的時(shí)間內(nèi)吸引受眾。實(shí)際上主流媒體新聞短視頻中的亮點(diǎn)內(nèi)容比較少,仍需在內(nèi)容完整性和強(qiáng)調(diào)亮點(diǎn)之間做出平衡。另外,新聞內(nèi)容真實(shí)與客觀,對(duì)于主流媒體而言,始終是其得以生存的關(guān)鍵,這也決定了主流媒體嚴(yán)肅形象的形成。基于此情況,也需要在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生產(chǎn)與傳播中,加強(qiáng)客觀性、情感性之間的均衡性。
四、媒體融合時(shí)代地方新聞短視頻的內(nèi)容生產(chǎn)及運(yùn)營(yíng)的建議
(一)加強(qiáng)技術(shù)賦能
新媒體的內(nèi)容、技術(shù)對(duì)于地方新聞短視頻而言,是實(shí)現(xiàn)其發(fā)展的重要?jiǎng)恿ΑK约夹g(shù)創(chuàng)新在新媒體發(fā)展中尤為重要,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生產(chǎn)也離不開(kāi)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支持。尤其是面臨復(fù)雜的內(nèi)容來(lái)源渠道,地方新聞媒體更加需要以技術(shù)賦能,助力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選擇。建議在產(chǎn)品策劃初期組建技術(shù)團(tuán)隊(duì),采取技術(shù)賦能形式,助力地方新聞短視頻,其間通過(guò)等部門同時(shí)參與,促使地方新聞短視頻真正實(shí)現(xiàn)“去信息化”,也為新聞賦予生動(dòng)性。
為了真正發(fā)揮技術(shù)賦能的優(yōu)勢(shì),建議應(yīng)用人工智能,將其與新聞內(nèi)容視頻化結(jié)合。地方新聞短視頻的生產(chǎn),選擇新的生產(chǎn)軟件、智能化工具,實(shí)現(xiàn)新聞內(nèi)容生產(chǎn)的人機(jī)合作。工作人員根據(jù)專題,將其提煉出多個(gè)話題,采取大數(shù)據(jù)算法實(shí)現(xiàn)多個(gè)渠道、終端以及平臺(tái)的傳播,并且觀看實(shí)時(shí)彈幕以及評(píng)論,了解受眾對(duì)于新聞短視頻的建議,以此為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的優(yōu)化提供參考
(二)構(gòu)建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生態(tài)圈
媒體融合環(huán)境下,信息量顯著增長(zhǎng),容易造成信息過(guò)載、信息割裂的問(wèn)題,而且該問(wèn)題在短視頻中仍然存在,為了提高短視頻質(zhì)量,需要針對(duì)此類問(wèn)題,提出解決與優(yōu)化對(duì)策。
在內(nèi)容生產(chǎn)方面,建議聚焦地方新聞受眾的日常生活,從中提煉出優(yōu)質(zhì)內(nèi)容,搭建新聞短視頻生態(tài)圈,其中還需融合專業(yè)新聞內(nèi)容,以矩陣的形式優(yōu)化新聞傳播效果。與此同時(shí),地方新聞短視頻的內(nèi)容覆蓋范圍也需不斷擴(kuò)大,在PGC內(nèi)容方面,應(yīng)同時(shí)涉及民生、金融、旅游、賽事等多個(gè)領(lǐng)域,并不斷拓寬內(nèi)容模塊。充分發(fā)揮出主流媒體內(nèi)容生產(chǎn)的專業(yè)性優(yōu)勢(shì),同時(shí)滿足各個(gè)階層群眾對(duì)新聞內(nèi)容的需求,以此來(lái)增強(qiáng)新聞短視頻用戶黏性。
現(xiàn)階段地方新聞短視頻更多是垂直內(nèi)容生產(chǎn),內(nèi)容空間也呈現(xiàn)出多元化趨勢(shì)。這便需要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與其他行業(yè)深度融合,實(shí)現(xiàn)各個(gè)行業(yè)領(lǐng)域的資源共享,為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注入新的元素。
(三)加強(qiáng)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的體驗(yàn)感與認(rèn)同感
短視頻在當(dāng)前互聯(lián)網(wǎng)中興起,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短視頻敘事的多元化,使受眾更容易產(chǎn)生情感共鳴,繼而增強(qiáng)文化認(rèn)同感。為此,地方新聞短視頻的內(nèi)容生產(chǎn),也可以借助這一優(yōu)勢(shì),采取短視頻的敘事范式,不僅與新聞價(jià)值訴求相契合,又能夠獲取廣大群眾的傳播語(yǔ)態(tài),加強(qiáng)短視頻內(nèi)容文本的真實(shí)性,并且與受眾實(shí)現(xiàn)情感的同頻共振,產(chǎn)生沉浸式的體驗(yàn)。
固有新聞內(nèi)容敘事模式主要由記者負(fù)責(zé)編輯,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的地方新聞短視頻,所有內(nèi)容敘事是以社會(huì)受眾為來(lái)源,通過(guò)跨界合作加強(qiáng)短視頻受眾在原創(chuàng)短視頻方面的積極性,使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更具傳播力。
很多媒體在地方新聞短視頻轉(zhuǎn)型期間,與當(dāng)?shù)馗咝:椭髁髅襟w合作,不定期組織創(chuàng)意短視頻比賽。比賽中為全民互動(dòng)提供了平臺(tái),并且也為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生產(chǎn)提供了大量?jī)?yōu)質(zhì)原創(chuàng)內(nèi)容,加強(qiáng)地方新聞短視頻內(nèi)容的多元性、差異性,生產(chǎn)、制作新聞內(nèi)容,受眾更容易產(chǎn)生共情,借此可以加強(qiáng)新聞短視頻的傳播效力。
(四)地方新聞短視頻運(yùn)營(yíng)強(qiáng)調(diào)地域特征
現(xiàn)行國(guó)家新聞短視頻運(yùn)營(yíng)模式在應(yīng)用中,主要是以“中央廚房”和“臺(tái)網(wǎng)融合”為要點(diǎn),在此類運(yùn)營(yíng)模式的作用下,地方主流媒體新聞短視頻運(yùn)營(yíng)也逐漸體現(xiàn)出一體化聯(lián)動(dòng)特征,即采用“獨(dú)立+嵌入”立體化運(yùn)營(yíng)的形式彰顯其地域性。在運(yùn)營(yíng)方面,主要是根據(jù)新聞短視頻產(chǎn)品形態(tài)的不同,以分眾化運(yùn)營(yíng)模式為首選。其一,需要研發(fā)獨(dú)立運(yùn)行的短視頻客戶端,實(shí)現(xiàn)新聞的終極表達(dá)。新聞的中心定位是短視頻內(nèi)容,并產(chǎn)出碎片化內(nèi)容,這更與用戶的閱讀需求相符合。例如很多媒體推出的獨(dú)立客戶端,使用圖片、文字、視頻結(jié)合的方式,闡述新聞事件脈絡(luò)。與此同時(shí),客戶端和當(dāng)?shù)貜V電APP合作,在全域內(nèi)實(shí)現(xiàn)媒體網(wǎng)絡(luò)聯(lián)合運(yùn)營(yíng),為用戶快速獲取地方新聞資訊提供便利。其二,新聞短視頻欄目新增媒體移動(dòng)新聞客戶端,工作者會(huì)在欄目中補(bǔ)充更加豐富的新聞內(nèi)容,為運(yùn)營(yíng)賦予全面性與綜合性。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用戶對(duì)于新聞資訊的需求也呈現(xiàn)出多元化特征。很多廣播電視臺(tái)踐行臺(tái)網(wǎng)融合進(jìn)程中,也開(kāi)始研發(fā)官方客戶端,使新聞產(chǎn)品豐富。通過(guò)這種嵌入式運(yùn)營(yíng)模式,更有利于提高新聞資訊的傳播效率,并以地方廣電媒體資源為依托,達(dá)到區(qū)域范圍內(nèi)高效傳播的目標(biāo)。
(五)構(gòu)建多路徑的新聞傳播運(yùn)營(yíng)矩陣
短視頻在媒體融合的市場(chǎng)環(huán)境中,面臨更加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趨勢(shì),應(yīng)用區(qū)域性傳播運(yùn)營(yíng),實(shí)際上并不能滿足所有地方新聞短視頻在當(dāng)前行業(yè)內(nèi)的發(fā)展需求。建議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加強(qiáng)跨界合作,構(gòu)建多路徑新聞傳播運(yùn)營(yíng)矩陣,探索不同的渠道,應(yīng)用一體化推廣運(yùn)營(yíng)模式,從而真正發(fā)揮地方新聞短視頻的品牌效應(yīng)。
媒體融合時(shí)代的新聞傳播中,選擇與傳統(tǒng)媒體建立合作關(guān)系,這對(duì)于地方新聞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是比較常見(jiàn)的形式。建議結(jié)合媒體融合時(shí)代特征,推出融媒體產(chǎn)品,充分發(fā)揮新聞制作、新聞內(nèi)容資源所具有的優(yōu)勢(shì),并利用先進(jìn)技術(shù)手段,選擇合適的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創(chuàng)新平臺(tái)技術(shù),開(kāi)辟新聞傳播路徑,豐富新聞媒體資源。
再如新聞媒體可以于抖音、快手等平臺(tái)中注冊(cè)賬號(hào),在這一類短視頻平臺(tái)的幫助下可以快速積累流量。另外,新聞媒體還可以通過(guò)“兩微一端”社交平臺(tái),向互聯(lián)網(wǎng)受眾分享新聞短視頻,使地方新聞短視頻和用戶能夠在更多元化的渠道對(duì)接。這樣不僅可以優(yōu)化新聞內(nèi)容的傳播效果,還可以拓寬互聯(lián)網(wǎng)互動(dòng)空間。受眾在平臺(tái)中點(diǎn)贊、評(píng)論,與新聞短視頻進(jìn)行在線互動(dòng),使地方新聞媒體獲取其需求,針對(duì)性地調(diào)整內(nèi)容生產(chǎn)、運(yùn)營(yíng)機(jī)制。
五、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地方新聞短視頻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無(wú)論是內(nèi)容生產(chǎn)還是運(yùn)營(yíng),均要在固有形式基礎(chǔ)上做出創(chuàng)新,才能夠契合新行業(yè)環(huán)境發(fā)展需求。這就需要新聞媒體積極探索短視頻內(nèi)容生產(chǎn)與運(yùn)營(yíng)模式,應(yīng)用短視頻優(yōu)勢(shì),滿足廣大新聞受眾的碎片化、快節(jié)奏的閱讀需求。如此一來(lái),不僅可以加快實(shí)現(xiàn)新聞媒體在媒體融合時(shí)代下的創(chuàng)新,還能夠提高地方新聞短視頻在新時(shí)代環(huán)境下的效益與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