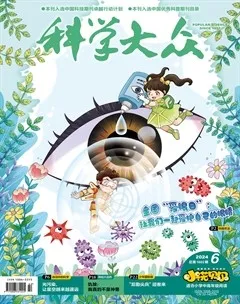犰狳:我真的不是神獸
馬睿棋


外形相似,但犰狳不是穿山甲
在戰(zhàn)國(guó)至漢代初期成書的古代三大奇書之一《山海經(jīng)》中記載了一種名為犰狳的上古神獸,書中是這樣描述的:它們生活在380 多千米遠(yuǎn)的南方,長(zhǎng)得像兔子,卻有一張鳥嘴、一雙像鷂鷹的眼睛和一條像蛇的尾巴,會(huì)躺下裝死。
而犰狳一直生活在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qū)。直到1492 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后,這些地方才第一次進(jìn)入歐亞大陸人的視野。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中國(guó)就和南美洲有了實(shí)際的交流,乃至有犰狳運(yùn)送過來,這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是否《山海經(jīng)》里描述的是穿山甲之類的動(dòng)物,而對(duì)南美洲犰狳的中文命名,只是對(duì)古代神獸的冒名頂替?
在動(dòng)物分類學(xué)上,犰狳和穿山甲的親緣關(guān)系比較遠(yuǎn)。犰狳隸屬貧齒目犰狳科,穿山甲則是鱗甲目穿山甲科的動(dòng)物。它們?cè)谕獠啃螒B(tài)上的相似,更多的是趨同進(jìn)化的結(jié)果。即當(dāng)不同物種的動(dòng)物處于近似的環(huán)境下,往往會(huì)演化出相似的生存策略及外部形態(tài)。在親緣關(guān)系上,犰狳和食蟻獸、樹懶反而更親近些。
甲胄笨重,卻絲毫不影響活動(dòng)
犰狳最明顯的外貌特征就是有著厚厚的甲胄。這身“鎧甲”雖然看起來厚重,但是設(shè)計(jì)得非常體貼。頭部、身體腹側(cè)和身體背側(cè)的鎧甲都是分體式的,彼此密切配合,不會(huì)互相約束。另外,只有肩膀和屁股的骨質(zhì)鱗片是一個(gè)整體,無法伸縮。胸背部的骨片則像一條長(zhǎng)長(zhǎng)的帶子一樣,一片片地和身體內(nèi)的肌肉相連,伸縮自如,完全不影響犰狳靈活地進(jìn)行日常活動(dòng)及快速奔跑。據(jù)說,犰狳遇到危險(xiǎn)時(shí),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shì)奔跑到合適的地點(diǎn),飛快地挖土掘洞,一眨眼的工夫,它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犰狳逃到洞里后,會(huì)用尾部的“鎧甲”死死抵住洞口。當(dāng)然,有鎧甲、有刺的動(dòng)物,在沒法逃之夭夭的時(shí)候,都會(huì)把身體縮成球形裝死,讓敵人無處下嘴。
同卵四胞胎,哪哪都相似
有些種類的小犰狳出生的時(shí)候,都是同卵四胞胎。犰狳長(zhǎng)大后,獨(dú)自生活。成年的雄性犰狳和雌性犰狳各有自己的領(lǐng)地。
夏末,雄性犰狳背井離鄉(xiāng),去尋找雌性犰狳。求愛成功后,雄性犰狳就會(huì)返回自己的領(lǐng)地。
而在雌性犰狳的體內(nèi),就有了小犰狳的雛形——受精卵。這個(gè)受精卵很快進(jìn)行細(xì)胞分裂,變成2 個(gè)細(xì)胞,接下來又進(jìn)行一次細(xì)胞分裂,變成4 個(gè)細(xì)胞。然后,每個(gè)細(xì)胞遷移到犰狳媽媽的子宮里,發(fā)育成4 只小犰狳。
由于是同卵四胞胎,每個(gè)小犰狳的性別都是一樣,要么都是雄性,要么都是雌性。由于4 只小犰狳的染色體都來自同一個(gè)受精卵,它們的相貌、氣質(zhì)、秉性也都極為相似。當(dāng)小犰狳呱呱墜地、睜眼看世界時(shí),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3 個(gè)“克隆體”,心里到底是驚喜,還是無比驚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