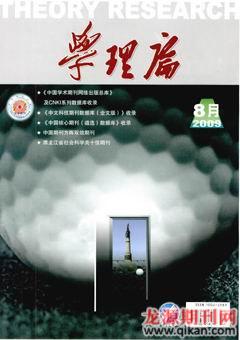淺談網絡人肉搜索中的多重博弈
楊先起
摘 要:在人肉搜索過程中,本文對各方權利在其中的多重博弈也進行探討:人肉搜索究竟是輿論監督的工具,還是網絡暴力的形式;是個人隱私權的侵害,還是保障公民知情權的途徑?
關鍵詞:人肉搜索;博弈;網絡
中圖分類號:G35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20-0098-02
時至今日,誕生于網絡中的“人肉搜索”早已經不是什么新事物了,然而它帶來的影響和產生的問題卻一直在不斷產生著,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筆者認為,在人肉搜索中,數量龐大的網民作為人肉搜索的行為實施者,與被搜索者在你來我往的過程中,使各種法律權利在無形的層面上交織,并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和問題。一場多重博弈在網絡媒體上上演:個人隱私、言論自由、公共道德、輿論監督、網絡暴力,眾說紛紜。
輿論監督VS網絡暴力
可以看到,人肉搜索的確在眾多的輿論監督案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監督的實施過程中,甚至不需要傳統媒體的介入就可以將案件推入到司法程序上去。人肉搜索的監督對象大多是由網民自身發現并予以公布的,眾多網民隨后積極參與到監督的行動中去,形成群體優勢,最終在網民的推動下是事件得到解決或處理。人肉搜索是一種網民主導的監督方式。
2008年年末,南京江寧區房管局原局長周久耕落馬。周久耕因為聲稱“低于成本價賣房將被查”激怒網民,被搜索出抽千元一條的天價煙,戴十萬元一只的名表,結果被上級免職。盡管這僅是眾多落馬官員中的一個,但由于從頭到尾網民的參與,使這次的反腐案件吸引了眾多的關注。網民們備受鼓舞,深感網絡反腐時代的來臨。
《憲法》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就保證了公民利用網絡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那么,以人肉搜索為手段進行網絡輿論監督又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在網絡媒介傳播過程中,輿論主體大多數是普通網民,他們可以自由地在網上表明自己的立場觀點、交流思想等,這種交流具有較強的開放性、及時性和更強的針對性。網絡媒介的特性使它與傳統媒介的輿論監督相比,有著特殊的優勢。從“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再到后來的“溫州考察團”,人肉搜索從早先的傾向暴力變成了輿論監督權利的行使工具。人肉搜索以輿論監督的方式進入公共事務,也以其自己的方式彌補著現有法律對政府監督的缺陷。當人肉搜索用于公共事務,毫無疑問,它進一步拓展了民主與言論自由的領域。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黨鮮明地指出了公民“四權”即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表達權。權利只有在充分使用的情況下,才能體現其自身的真正意義。而在現今的社會,可供人人參與發表意見,除了網絡,還沒有其它的媒介載體可以勝任。我們看到,網絡的輿論監督職能以引起各方重視。徐州在頒布《徐州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禁止網絡人肉搜索行為后明確指出,對于舉報官員腐敗問題不在此保護條例的規定范圍之內;云南晉寧看守所在押人員離奇死亡后,云南政府主動邀請網民組成調查團,也體現了對于網絡輿論監督的重視。
然而在人肉搜索事件中,存在著大量的以語言暴力形式對他人進行惡毒攻擊的行為。這是一種借助網絡輿論的力量,對他人進行肆意人身攻擊的狂熱的偏執行為。這種行為具有的特點是,第一,明顯的暴力和攻擊傾向。參與網絡暴力的網民,往往以一種高昂的斗志,飽滿的情緒及熱情對一件事或人進行駁斥,怒罵。第二,以一種“道德判官”的形象出現。他們一般并不試圖利用法律手段來解決他們關注的問題,而以自己的道德標準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評判,進而把個人的處罰意愿強加在當事人身上。第三,對當事人造成非法不良傷害。非執法機構在對當事人進行處罰時,就構成了違法行為。
在人肉搜索中,道德權利往往掌握在大多數的網民手中,這樣他們就形成了一個強勢群體,而被搜索者則處在十分弱勢的地位,因此,在網民對被搜索者進行人身攻擊和謾罵時,一般會得到群體中其他網民的響應,這就為其繼續實施這種攻擊的暴力行為提供了動力,而暴力的范圍和程度也進一步加深。當然,在利用社會道德對當事人進行譴責時,難以避免的會摻雜自己的道德觀和個人的價值觀。而同時,網絡上的暴力行為往往會延伸到現實社會中,在當事人不道德的行為受到社會輿論譴責時,他的隱私、名譽以及人身自由都未能幸免。當事人在現實社會中的社會評價降低,受到周圍群體的排擠、被工作單位開除等等各種附加懲罰。
這種暴力行為對整個社會和個人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人肉搜索由最初的道德審判轉變成對公民人權的踐踏。而網絡暴力也表現出了網絡在輿論監督時的缺陷:首先,信息的準確性無法核實。網絡的開放性也就帶來了它的一個負面結果,即虛假信息的泛濫。網絡信息傳播是一種交互式傳播方式,即由用戶控制信息的交換而不是中介人,因此用戶有可能對自己接受的信息進行選擇,它使信息的準確性、權威性被打破,妨礙人們獲得真實信息,導致人們形成與現實不相符合的意見,網絡也為謠言的產生提供了技術條件,部分網民出于不良目的,在網上對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員加以誹謗和詆毀,混淆人們的視聽,影響政府的正常運轉和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開展輿論監督的前提,就是要保證信息的暢通和真實無誤的傳播,而虛假信息的存在,嚴重影響輿論監督的效力。其次,網絡輿論中的情緒性、攻擊性言論較為突出。如果在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偏激或者極端的情緒化觀點占了上風,無主見的群體成員的情緒就會受到影響,被偏激的觀點所感染,造成人多勢眾的局面,原本的輿論監督就會變成非正常的輿論暴力。
如何使人肉搜索更好的行使輿論監督職能,而不會轉變為網絡暴力呢?我們要遵循一定的規則。首先,不能超越法律許可的范圍,不能損害當事人法律賦予的權利。其次,要遵循個人的道德準則,不能為了獲取網民的支持,虛構故事、或者對事件本身添油加醋,喪失自身的道德底線。我們對人肉搜索要有全面而客觀的看法,既要看到它的缺陷,用法律形式加以約束,也要看到與傳統媒體相同的輿論監督作用。只有政府給予合理的疏導、管理和加強法制建設,廣大網民自身社會責任感的加強,才能使人肉搜索更好地進行輿論監督。
個人隱私VS公共道德
2008年12月18日,因“姜巖自殺事件”引發的“人肉搜索第一案”在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宣判。大旗網和“北飛的候鳥”兩家網站的經營者,侵犯原告王菲名譽權及隱私權,判網站停止侵權、公開道歉,并分別賠償王菲精神撫慰金3000元和5000元。隱私權頓時又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焦點。
隱私權的概念最早是1890年美國學者布蘭代斯和沃倫在《哈弗法律評論》上發表的《論隱私權》一文中提出的。后來逐漸被美國有關法律確認,以后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的采用。隱私,是指個人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而不愿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擾的私人事項。隱私權,就是個人有依照法律規定保護自己的隱私不受侵害的權利。①而在網絡時代的大環境下,人們又有了網絡隱私權這一衍生權利。網絡隱私權主要指,公民在網上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和私人信息依法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犯、搜集、復制、公開和利用的一種人格權;也指禁止在網上泄漏某些與個人有關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實、圖像以及毀損的意見等。
我國法律還沒有對公民隱私權進行規定,根據司法解釋,我國在法律實踐中,通常以保護名譽權的形式來保護個人隱私權。
公民隱私權的內容隨著社會發展呈現多樣化和擴大的趨勢,而隱私的具體分類也有不同的說法。但當前世界各國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主要有:
1.公民的私人信息
私人信息是個人的重要隱私,它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包括公民的姓名、肖像、住址、私人電話,財產狀況等等,這些私人信息非經本人同意,他人不得非法公布。
2.公民的通訊自由
公民的通訊自由不受侵犯,信件、傳真、電子郵件、短信、聊天記錄、電話錄音等都屬于個人隱私。未經本人同意,擅自拆閱、翻看或者刪除的,都會構成對公民通訊自由的侵害。隨著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公民通訊自由的保護范圍也會隨之擴大。
3.公民的空間隱私
公民的空間隱私指當事人的特定私密空間不受他人窺伺、侵入、干擾的隱私權。傳統的空間隱私主要是指物理空間的隱私,如個人居所或是包裹口袋等。在網絡時代,虛擬空間的廣泛使用使空間隱私擴大了其保護范圍,個人的電腦系統、郵箱、博客等都屬于個人的空間隱私范圍。
4.公民的生活安寧
公民對自己的生活安定和寧靜擁有一定的權利,可以排除他人對他正常生活的騷擾。在人肉搜索中,網民除了在網絡上公布、傳播被搜索人的信息外,常常還依據該信息對被搜索人進行騷擾,嚴重影響了被搜索人的正常生活。這種侵害行為從廣義上來說也是對隱私權的侵害。這些行為都侵犯了個人的私生活安寧,其危害不能低估,相應行為人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人肉搜索活動中,其目的就是為了找出被搜索人的個人信息,以使其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之下,因此,怎樣獲得其隱私信息就成了人肉搜索能否完成的關鍵。網民為了達到目的,會利用網絡的開放性和技術破解,侵入個人的網上空間,而個人空間中的各種私密信息也就落入了他人之手。而后,個人隱私被公開,隨之而來的是個人生活秩序的被擾亂。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私人信息、通信信息、空間隱私和生活空間等隱私都被侵害。“姜巖事件”中的當事人王菲就是在被人肉搜索后,出現眾多網民到其家上門騷擾的嚴重后果,使王菲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受到嚴重影響。
誠然,隱私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受法律的保護。但是我們不能以隱私權為借口和保護傘,做出違背社會道德與法律的事情。
“虐貓事件”中的女主角被人肉搜索后,是否侵犯了她的隱私權呢?如果說虐殺小動物這種與社會公共道德相違背的行為也受到隱私權的保護的話,那么所有的違法犯罪行為都可以被實施者冠冕堂皇地說成是自己的隱私權,這實際上是相當荒謬的。在個人行為觸犯了其他社會成員的共同準則時,這種行為即構成了社會學上的越軌行為。社會是一個群體組織,而任何社會都要運用社會控制體系來維系現存的社會秩序。所謂的越軌行為,“指的是那些違反重要的社會規范和要求并因此受到許多人否定評價的行為”②,其中就有不道德行為和犯罪行為。因此,對于違背道德和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加以公布,不是侵犯其隱私權的行為。
觸犯公眾的道德底線,會被網民人肉搜索加以公布,更不必說網民在行使監督權利時發現的違法違紀官員加以曝光的行為。“周久耕事件”和“溫州考察團事件”中,可以說周久耕的個人收入和日常生活以及溫州考察團的開銷等都是隱私,但是這種隱私如果一直被保護下去的話,不知道還會有多少個“周久耕”,多少個“溫州考察團”。在許多國家,官員隱私權的界定,其標準內涵都有別于普通民眾。財產情況、婚姻情況、消費情況、親屬財產情況等,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屬于隱私權保護的范疇,但對于官員而言,卻是公民權利的合理讓渡,應當置于民眾的監督范圍之內。因此人肉搜索在進行監督行為時對于政府工作人員的信息公開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我國在官員隱私權利的規定上還很不完善。早在2005年的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王有杰稱:有97%的官員對其提出《建立官員個人資產申報制度》持反對意見,直到2009年,官員財產公開仍然難以實現。
個人的隱私權需要保護,而公共道德和法律法規也需要遵守,這就要求公民自身要加強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責任感,而政府也要完善法律法規,避免違法行為的出現。
注釋:
①王澤鑒:《侵權行為法》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頁。
②韓廣年主編:《社會學基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87頁。
參考文獻:
[1]澤勒尼.傳播法:自由·禁制與現代傳媒[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2]張曉輝.論大眾媒介上的隱私公開現象[J].國際新聞界,2005.
[3]陳俐羽.從人肉搜索談我國公民隱私權保護[J].法治與社會,2008,(09).
[4]侯茜.隱私權的權利沖突與立法選擇——以網絡時代的“人肉搜索”為視角[J].科學·經濟·社會,2008,(04).
[5]王利明.人格權與新聞侵權[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王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