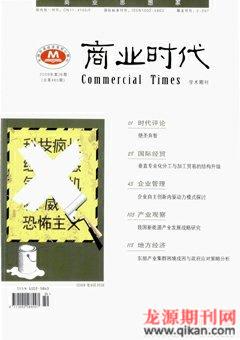伽達默爾的闡釋觀念與漢詩英譯
史 薇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20世紀末以來,譯者的主體性在各種框架下得到研究。隨著哲學闡釋學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其主要觀點對譯者角色定位的進一步認識有著獨到的啟示。本文擬在分析古詩《送別》的七種譯文的基礎上,以伽達默爾哲學闡釋學思想為指導,來探討漢詩英譯過程中所折射出的譯者文化雙重身份性(即作為闡釋者的譯者身份),以及譯者的這種雙重身份性對不同譯本的生成所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闡釋學 翻譯 主體
闡釋學一詞乃西文譯名,其發展經歷了古代希臘“闡釋學”,中世紀的“闡釋學”和“文獻學”,施萊爾馬赫(F. 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W. Dilthey)的哲學闡釋學以及海德格爾(M. Heidegger)和伽達默爾(H. G. Gadamer)為代表的西方現代闡釋學等幾個階段(祝朝偉,張柏然,2002)。而在近代西方哲學中,闡釋學運動的最高峰當是“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哲學闡釋學”。伽達默爾從海德格爾的闡釋學思想出發,將闡釋學作為哲學本性論對待,“把理解和闡釋同存在扯上了關系,理解表現為一種‘關系的總和(a relational totality),拋棄了舊闡釋學把‘客觀證實性(objective verifiability)作為一心想要實現的目標”。他認為文本不僅擁有自身的意義,而且對于理解主體“我”也有意義(劉華文,2005)。
伽達默爾的闡釋觀念與翻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伽達默爾對翻譯問題的討論是以整個哲學闡釋學為背景的,他對翻譯現象的探討,僅是把它作為闡釋學研究的一個特例來進行的。雖然他討論翻譯問題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討論翻譯本身,而是為了以翻譯為例來論證他的哲學闡釋學思想,但他對翻譯問題的精彩討論值得關注。
伽達默爾最重要的翻譯思想是“翻譯即解釋”。在哲學闡釋學框架內,翻譯即解釋,具體是指“翻譯的過程就是,在跨文化的歷史語境中,具有歷史性的譯者使自己的視域與源語文本視域互相發生融合而形成新視域,并用浸潤著目的語文化的語言符號將新視域重新固定下來形成新文本的過程”(朱健平,2007)。在新文本的生成過程中,譯者的闡釋者角色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為整個翻譯過程涉及到兩次解釋,“第一次解釋是譯者視域與源語文本視域的融合,第二次解釋則是目的語語言文化的視域與譯者新視域的融合”(朱健平,2007)。
王維《送別》詩七種譯文比照
在我國文化史上,盛唐是一個輝煌燦爛的巔峰時期,有“詩佛”之稱的王維可以說是盛唐文化非常光潤的結晶。王維(701-761),字摩詰,尤以清新明秀的山水田園詩最為人稱道。由于受到禪宗思想很深的影響,王維的詩歌常常透出幾分深遠玄妙的禪意。本文中所要分析的這首《送別》詩為五言古詩,詩曰: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云無盡時。
這是一首送友人歸隱的詩。表面看來語言明白如話,語句平淡無奇,然而細細品味,卻是詞淺情深,感慨良多。詩的開頭兩句敘事、寫飲酒餞別,以問話引起下文。三、四句是交待友人歸隱原因—“不得意”。五、六句很有韻味,寫出朋友間彼此的深刻理解,既含有作者對友人的同情、安慰,也有自己對現實的憤懣與鄙夷,有對追逐名利的世俗生活的否定,也有自己對人生窮達升沉的慨嘆,還有對隱居山林的欣羨,似乎是曠乎超脫,又帶著點無可奈何的情緒。
我們先來看一下七位譯者對《送別》詩三、四句“君言不得意,臥歸南山陲”所做的闡譯,具體見圖1。
詩歌作為特殊的文學形式,其語言是高度凝練的,這就導致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言意關系,繼而造成詩歌文本里存在著有待讀者去尋找和填補的未定點(spots of indeterminacy)和更多的空白(blanks),也就給譯者留下了更多的闡釋空間。在對這首詩中的“不得意”進行闡譯時,七位譯者對這同一個意向性對象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理解:Giles把它理解為“sick of life's ills”(對生活弊端的厭倦),Fletcher和Yu的理解相似,分別為“your hopes unprospered”和“You did not achieve your wishes”(意愿未能得以實現),Bynner認為是“I am discontent”(不滿意,對什么不滿意呢?),Watson則理解為“nothing goes right”(事與愿違),Wai-lim Yip將其理解為“at odds with the world”(與世俗難以相融),Owen把“不得意”闡譯為“something troubling you”(某事困擾你)。Giles,Watson以及Wai-lim Yip的譯文更接近原文意欲傳達的信息。我們知道這首詩是王維送友人孟浩然歸隱山林的,故“不得意”的內容主要是指政治上、功業上的坎坷困頓,懷才不遇,所以譯者是絕不能完全忽略掉這種基調(即仕途不得志而生失望之情,進而萌生歸隱之意)的。從這里可以看出,盡管翻譯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解釋,但作為闡釋者的譯者在進行闡譯時不是“天馬行空”,任意而為的,“因為任何翻譯都是針對某一源語文本而翻譯,都是在某一文本的觸發下而進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該源語文本的制約”(朱健平,2007)。
據劉華文(2005)在詩歌的翻譯過程中,翻譯主體往往會采納三個層次的闡釋意向:第一種是釋意性闡釋意向,即讓自己的存在游離在闡釋之外,只保留自己的邏輯、理性的一面,運用傳統意義上的闡釋方法,求得對文本內容的考證,力求做到轉譯時時有據,著筆處處可查。第二種是意識性闡釋意向,即原文中的構成元素能夠通過意向性的建構構造本身,同樣地在翻譯中它們也能構造自身,只不過構造之后獲得的意向性內容卻會不盡一致,這主要是由兩種主體的意識內容的差異性造成的。第三種是存在性闡釋意向,即把翻譯主體的理解視域從文本和意識擴展到人的整個存在境域,翻譯是主體的存在樣式,通過它,主體不僅揭示原文而且其自我也獲得了存在性的敞開與揭蔽。這三個意向結構層次會在譯文中有著相應的文本表征。

借助這一分類,本文具體分析諸位譯者對原詩第四句“歸臥南山陲”的闡譯,此句的不同譯文很好地反映了翻譯主體的意識性闡釋意向問題。在原詩的第四句中,詩人的友人因在世俗官場中郁郁不得志而希望退隱于山林,“歸臥”一詞表明他隱居山中后悠閑自在的生活狀態。Giles利用友人和“南山”之間的鄰近關系而把“臥(slumbering)”的這一狀態轉移到“南山”身上,使譯文自身和原文之間悄悄發生了認知轉變,從而抬升了譯詩的詩性價值,更好地體現了中國傳統詩學思想中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審美境界。
最后,本文來看七位譯者對“白云無盡時”這一富含禪意的詩句的闡譯。在這首詩中,詩人把自己內心世界的復雜豐富感受凝縮在“白云無盡時”這一幅自然畫面之中,從而達到:“拈花一笑,不言而喻”,令人回味無窮的藝術效果。首先對這一詩句的譯文進行一個比照,詳見圖2。
通過比照,可以發現后六種譯文僅僅是對“白云無盡”進行了客觀的轉譯,卻忽視了原作者賦予“白云無盡”這樣一幅圖景的意向性內容,即陶醉白云,自尋其樂之情。后六位譯者只是耽于對原始意象進行闡釋還原,而忘記了原作者對“白云無盡”的意向性賦意,譯者似乎在翻譯中過于“置身詩外”了,“白云無盡時”的妙遠意境難以被呈現出來。盡管Giles的譯詩加入了“me”(指友人)這一主體因素,也僅是傳達了友人歸隱后的悠然自得,對于詩人因友人歸隱而意欲抒發的各種感慨卻被遮蔽掉了。由此可見,對原詩進行準確而全面的闡釋實非易事,漢詩中寬闊的解讀空間常常會在譯詩中或多或少地喪失掉(劉華文,2000)。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遺憾的產生并非是由于譯者的闡釋方式或闡釋能力造成的,“這是由語言特別是(漢語)詩歌語言的本體特征(即辭不逮意卻又不懈于以辭達意)引起的”(劉華文,2000)。
結論
本文旨在以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思想為指導對漢詩英譯過程中的闡釋環節進行探討,并通過對古詩《送別》的七種譯文加以比照,來發現身兼闡釋者身份的譯者其闡釋活動對譯文生成的影響。英漢兩種語言的本質差異以及審美方式的不同對譯者的闡釋行為及闡釋結果都會施加影響。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僅是為我們研究漢詩英譯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框架,需要進一步去發掘的東西還有很多,特別是在漢詩英譯欣賞與評價中如何具體操作“翻譯即闡釋”這一概念值得細化。此外,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與我國傳統闡釋觀的異同所帶來的研究漢詩英譯的啟示是研究漢詩英譯應當關注的另一焦點。
參考文獻:
1.劉華文.“道”與“邏各斯”在漢詩英譯中的對話.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
2.陶文鵬選析.王維詩歌賞析.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
3.王維/楊義,郭曉鴻選注、譯評.插圖本中國詩詞經典—王維.岳麓書社,2005
4.祝朝偉,張柏然.翻譯與闡釋的多元—從《錦瑟》的英譯談起.外國語,2002
5.朱健平.翻譯:跨文化解釋-哲學詮釋學與接受美學模式[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
史薇(1977—),女,安徽蚌埠人,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