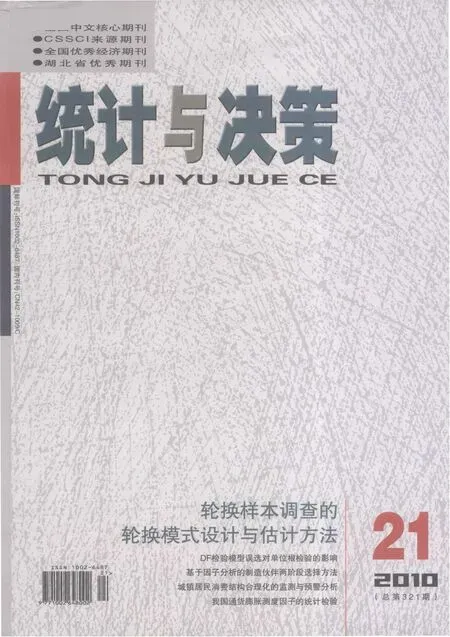廣東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地區差異研究
王克林
(廣東商學院 經濟貿易與統計學院,廣州 510320)
廣東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地區差異研究
王克林
(廣東商學院 經濟貿易與統計學院,廣州 510320)
文章運用多階模型方法研究了2007年廣東省11市7縣的1600戶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數據。結果表明,不同城市之間居民消費水平存在顯著差異。為了解釋這些差異,文章納入地區平均收入水平(GMI)和住房價格(HP)兩個場景變量。實證研究表明,這兩個場景變量對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跨地區變異的解釋程度可達95%以上。
消費水平差異;多階模型;場景變量
1 研究背景與方法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廣東省經濟的迅速崛起,廣東省各地區之間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也日漸凸顯。經濟增長的不平衡引起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消費水平的地區差異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被不斷拉大的。對消費水平地區差異性的研究不僅涉及到如何制定消費政策以擴大消費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而且直接關系到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關系到收入分配制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選擇。因此,對消費水平地區差異問題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研究方法與所研究的實際問題的切合程度直接關系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目前我國政府統計部門常規的統計調查大多都采用多階段統計調查方式。例如城鎮住戶調查按照省抽市、市抽縣(區)、縣(區)抽街道(居委會)等方式進行,由此產生的調查數據就具有多階特征。但是,傳統的統計分析技術(如ANOVA)將各階段數據“壓縮”到以個體為單位的總體進行分析,難以正確反映和充分利用多階數據各階段的信息,并且對估計結果會造成嚴重影響[1]。因而,具有多階特征的統計數據應該用多階模型來分析。多階模型方法是21世紀才被引入我國的。近幾年來,國內已有學者開始嘗試運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如楊菊華(2006)介紹了多階模型的基本原理,并用2000年“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數據展示了多階模型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2];郭志剛等(2006)應用多階模型分析了2001年全國計劃生育/生殖健康調查數據,考察了宏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計劃生育氛圍與微觀的婦女個人特征如何共同影響二孩生育間隔[3]。已有的研究都表明,多階模型非常適合于多階數據的分析,尤其是由多階段調查方式獲得的數據的分析。對多階模型的恰當應用往往能獲得傳統的統計分析方法難以獲得結論。下面首先介紹多階線性模型的基本形式,然后將其應用于廣東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差異性研究。
2 多階模型的基本形式
2.1 空模型(empty model)
多階模型分析通常是從空模型,又稱截距模型 (intercept-only model), 或無條件均值模型 (unconditional means model)開始的。空模型的基本格式如下:

該模型的微觀層(水平1)和宏觀層(水平2)公式中均沒有解釋變量。式(1)即表示微觀層面的變量關系,β0j和eij分別代表第j組因變量均值和圍繞該均值的個體隨機差異。式(2)表示宏觀層面的變量關系,總截距γ00代表的是yij的總(平)均值;u0j代表組均值之間的差異,即第j組的因變量均值與總均值的差異。 式(3)是式(1)和式(2)的組合,包括了固定效應(γ00)和隨機效應(u0j和 eij)兩部分。
2.2 兩階模型的公式表述
式(4)~(5)是一個兩階模型,包括兩個水平 1解釋變量(level 1 explanatory variable)和一個水平2解釋變量(level 2 explanatory variable)。

其中,yij是第j個水平2單位中的第i個個體的水平1觀測值,是因變量;其中 i=1,2,……,N(N 是樣本總量),j=1,2,……,J(J是水平 2 的單位數)。式(4)是分析 yij差異的水平1方程。水平1截距β0j下標j表示水平1截距跨水平2單位變化。水平1固定斜率α1說明水平1變量x1ij對yij的效應不跨水平2單位變化,隨機斜率β1j則說明水平1變量z1ij對yij的效應隨水平2單位變化。式(5)是水平1隨機截距β0j對應的水平2方程。Goldstein(1988)介紹了多階模型的一般形式。[4]
3 消費水平地區差異的實證研究
3.1 數據來源及指標選擇
本文采用2007年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組織實施的廣東城鎮住戶調查的部分結果進行分析。調查在廣州、深圳、珠海、汕頭、佛山、韶關、梅州、惠州、東莞、湛江、肇慶等11個市和順德、鶴山、廉江、電白、興寧、普寧、連州等7個縣進行,共調查了1600個家庭,樣本分布如表1所示。本文研究調查結果中的消費及相關數據。
從經濟學理論角度來看,影響一個家庭消費行為的因素有很多,如收入水平、物價水平、利率水平、風險因素、消費習慣、居住地點、宗教信仰等等,因而家庭消費行為是一個綜合的表象。如果我們把單個家庭看作是微觀個體,那么家庭屬于某個街道(居委會),而后者又屬于某一市(縣),這就具有了多階特征。一個家庭的消費行為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其所在地區,如市(縣)相應因素的影響,而后者又受到更大環境如省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研究家庭消費行為就不應該僅單純研究家庭這個微觀層面,還應該考慮家庭所處環境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就廣東來說,同一個市(縣)以下更小的行政單位如社區之間差異一般很小,對家庭的影響也可以忽略,而市(縣)之間的差異則比較明顯,對家庭會造成一定的影響。為簡化分析,本文只研究市(縣)相關因素對家庭消費行為的影響,即把市(縣)看作宏觀層進行兩階模型分析。本文采用指標包括微觀層面的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pce)、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和宏觀層面的組平均收入水平(GMI)和住房價格(HP)。這里,GMI和HP即為場景變量或協變量。
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pce)。在城鎮住戶調查中,每年住戶支出調查指標有100多個,本文不分析消費結構,僅關注住戶支出中的消費性支出。用家庭消費性支出除以家庭人口數得到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pce),用以衡量家庭消費水平。影響pce的因素包括微觀層面的PDI和宏觀層面的GMI和HP。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從凱恩斯的收入決定消費理論到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假說,再到莫迪利安尼等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再到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說的都是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異只在于收入的度量方式和對消費的影響形式,這一點無需再做解釋。本文采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即家庭年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數)來衡量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

表1 2007年廣東城鎮住戶調查各調查點樣本量分布
組平均收入水平(GMI)。應該看到,用絕對收入水平衡量消費行為是不充分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杜森貝利(J.Dusenberry)提出的相對收入假說,就是為了說明消費水平并不僅僅由絕對收入決定,而應該從相對收入角度考慮。一個人、一個家庭所處的環境會直接影響到個人和家庭的消費行為。例如,要解釋處于不同城市的居民消費水平差異,除了考慮個體的絕對收入差異外,還要與當地的平均收入水平、物價水平等因素結合起來。這里的組平均收入水平(GMI)指的就是不同市(縣)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它是影響地區居民消費的場景變量。
住房價格(HP)。隨著二元結構背景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和戶籍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主要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急劇膨脹:城市規模迅速擴大,人口也越來越多。再加上其它非市場因素的影響,近幾年,我國多數城市的商品房市場都呈現出需求大于供給,價格快速上漲的態勢。高漲的房價增加了城市中購房群體(處于還貸中的已購房群體和有購房意向的群體)的生活壓力,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消費行為。一般來講,房價高的城市,買房壓力大,這就會擠占家庭在其它方面的消費支出;反之,房價低的城市,居民可以分配更多的資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費。因而不同城市的住房價格成了影響本地區居民消費的“公共因子”。本文研究中用到的住房價格數據是筆者用《廣東統計年鑒2008》中“商品房屋銷售額?”除以“商品房屋銷售面積?”得到的[5]。
3.2 消費水平地區差異估計結果
本文運用SAS9.1中的SAS PROC MIXED模塊對2007年廣東省11市7縣的1600戶城鎮居民消費數據進行處理。我們從空模型(模型1)開始分析。模型1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模型1的固定效應估計部分,即總截距估計值γ贊00(13609)是各市(縣)消費水平總均值。模型1的隨機效應估計是式(2)中u0j的估計,u0j的正負表示第j個調查市(縣)的平均消費水平大于或小于全省消費水平總均值。例如,2007年廣州市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為 19107.6元(γ贊00+u贊01=13609+5498.6=19107.6元),余可類推。這里,除了汕頭、鶴山和連州之外,其余15個市(縣)的隨機效應估計都統計顯著,這說明這些地區的平均消費水平都與總平均消費水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表2 消費水平地區差異估計結果

表3 模型2的固定效應參數估計結果
3.3 消費水平地區差異原因探析
前文實證表明,所研究18個市(縣)城鎮居民消費水平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這些差異呢?本文通過引入GMI和HP兩個場景變量對此進行解釋。根據式(4)和式(5)可將場景變量GMI和HP引入多階模型,記為模型2。模型2的具體形式如式(6)所示。

模型2的SAS9.1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模型2的估計結果表明,地區平均收入水平與家庭消費水平正相關,而地區住房價格與消費水平負相關。模型2經過2次迭代就收斂了,說明模型擬合良好。截距項估計值14508表明,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DI達到所調查樣本的總平均收入水平18136.34元,且其所在市(縣)的GMI也達到該水平,HP達到總平均水平4433.93元時,該家庭的人均消費為14508元。由估計結果還可以看到:平均來說,家庭個人可支配收入PDI高于平均收入18136.34元后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6310;在個人可支配收入PDI和住房價格HP都不變時,地區平均收入水平GMI的(平均)每增加1塊錢,能引起該地區人均消費支出增加0.3002元;在個人可支配收入PDI和地區平均收入GMI都不變時,住房價格HP每上升1元,能引起該地區人均消費支出減少0.3540元;這說明GMI和HP確實能顯著影響不同地區家庭的消費行為。
那么場景變量GMI和HP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廣東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跨地區的變異呢?在多階模型分析中,通常用一個類似于判定系數的指標,即方差縮減比例指數,來測量估計中方差被解釋的程度,這需要將模型2與不含任何解釋變量的模型1作比較。模型2中截距項方差由模型1的38880089下降為804667,殘差項方差由1.45E+08下降為95854916,說明模型2中引入家庭層解釋變量PDI和市(縣)層場景變量GMI和HP后,模型更好地解釋了家庭消費的組間差異和組內差異。模型2能夠解釋的消費水平組間差異可用 Raudenbush&Bryk(簡稱 RB)方法或者 Snijders&Bosker(簡稱SB)方法進行估計[7][8]。兩種方法估計的模型水平2可解釋方差分別為:
其中,90是組平均樣本量。RB和SB水平2可解釋性差異比重近似,說明消費水平跨地區變異的95%以上可以由模型2解釋。
4 結束語
多階模型方法靈活,使用面廣。在本文的應用中,它很好地展示了廣東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水平跨地區的差異,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出現這些差異的原因,結論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場景變量GMI和HP能夠解釋家庭消費行為跨地區變異的95%以上。這是因為多階模型將家庭消費水平變異分解為“組內差異”和“組間差異”,然后就可以單獨應用宏觀層面的場景變量解釋家庭消費行為跨地區的差異。
對解釋變量的中心化處理使估計結果的涵義更加豐富。本文在模型2中,對人均可支配收入PDI進行了總均值中心化處理。中心化處理后的解釋變量有了有意義的零值,因而截距項的估計結果就可以得到有意義的解釋。同時,估計結果還顯示了非常有意思的結論:地區GMI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小于PDI的影響,因為模型2的估計結果中后者所對應的邊際消費傾向更大;當一個城市的住房價格高于總平均價格后仍繼續上漲的話,消費將會被擠占。因此,如果將家庭PDI高于和低于總平均收入(本文為18136.34元)作為區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標準,那么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將會比增加低收入地區的平均收入對消費產生更大的拉動作用。適當控制住房價格已經高于總平均價格的城市的住房價格將有助于拉動當地家庭的消費及其他支出。當然,要提高政策的執行效果,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綜合考慮。
[1]Muthen,B.0.Multilevel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J].Sociological Methods&Research,1994,22.
[2]楊菊華.多層模型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J].中國人口科學,2006,(6).
[3]郭志剛,李劍釗.農村二孩生育間隔的分層模型研究[J].人口研究,2006,7(4).
[4]Goldstein,H.A Gener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Multilevel Data[J].Psychometrika,53,1988,(4).
[5]廣東統計年鑒2008[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6]王濟川等.多層統計分析模型——方法與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Raudenbush,S.W.,Bryk,A.S.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2ndEdition)[M].Newbury Park,CA:Sage.2002.
[8]Snijders,T.A.B.,Bosker,R.J.Modeled Variance in Two-level Models[J].Sociological Methods&Research,1994,(22).
F222
A
1002-6487(2010)21-0095-03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09BJL005)
王克林(1980-),男,河南登封人,博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社會經濟調查與分析。
(責任編輯/易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