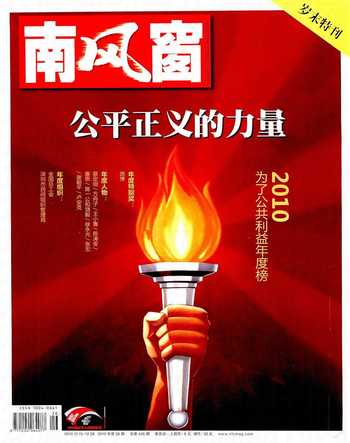微博時代:公眾“啟蒙”精英
王曉漁

公眾通過網絡進行自我教育,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經歷了從順民到公民的轉型,雖然這個轉型過程遠未完成,但是卓有成效。
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
當代中國的社會格局,從2007年底、2008年初開始轉型,標志是廈門Px事件和“周老虎”事件,市民或網民分別在街頭和網上開始社會運動。當代中國的文化格局,則是從2008年底、2009年初開始轉型,標志是“草泥馬”的橫空出世。隨著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由下而上的啟動,公眾逐漸理性地表達反對立場和戲謔性地使用反諷話語,公民意識呼之欲出。
2010年,各種社會事件目不暇接,加速度出現。“俯臥撐”、“躲貓貓”在2008年、2009年分別是年度關鍵詞,但是在201O年,此類事件曇花一現,就立即被層出不窮的其他事件覆蓋。在社會事件的重重壓力之下,文化領域暗流涌動,不時激蕩成風波,摩羅、汪暉、唐駿、李一、周立波等紛紛成為風波中的主角。唐駿、李一、周立波并非文化界人士,分屬商業、養生、娛樂領域,但是他們都事發于文化層面,唐駿的學歷、李一的信仰、周立波的網絡觀均遭到摧毀性的質疑。除了李一的“天價養生班”被暫停,唐駿的“打工皇帝”身份沒有動搖,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依然票房不錯,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無需付出代價。
與80年代精英“啟蒙”公眾不同,當下,公眾“啟蒙”精英成為常見現象。90年代以降,知識分子的專業化取代了公共性。許多精英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各有所長,在專業以外幾乎一無所知,對于公共問題的看法缺乏“常識”,卻憑借對話語權的壟斷成為權威。在網絡時代尤其是微博時代,話語權失去了決定性作用,價值觀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公民意識在中國匱乏,不僅表現于公眾缺乏公民意識,更表現在精英缺乏公民意識。不同的是,公眾通過網絡進行自我教育,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經歷了從順民到公民的轉型,雖然這個轉型過程遠未完成,但是卓有成效。公眾的“反智”傾向值得反思,但是部分精英對于公民意識的拒絕,更加值得檢討。
公眾對于部分精英的批判,“反智”的成分越來越少,“啟蒙”的成分越來越多。由于社會問題日益凸顯,難以回避,精英們紛紛走出專業領域,揚短避長,對公共問題發表意見,這增加了他們失言的幾率,進而增加了他們“被啟蒙”的機會。有些公眾更像精英,有些精英則泯然眾人。或許,根據身份劃分公眾和精英的做法,本身就值得檢討。不管公眾還是精英,都需要有公民意識,專業化不能成為排斥公民意識的理由。
“成功人士”的形象危機
從文化領域內部延伸到各個領域的文化層面,“成功人士”紛紛遭遇形象危機。
年初,摩羅的《中國站起來》讓熟悉他的讀者感到意外。僅就觀點而言,《中國站起來》并無特別之處,是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2009年《中國不高興》的山寨版,核心理念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種冷戰思維,一度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今天,排他型的民族主義不僅是意識形態,還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持這種立場者不僅“政治正確”,還可以獲得市場回報。此前,摩羅以獨立知識分子的形象出現,等到他高調推出《中國站起來》,讀者驚訝地發現他竟然“轉型”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擁躉。摩羅的“轉型”,比《中國站起來》里的老調重彈更加觸目驚心。不過,這種“轉型”有一脈相承之處,比如摩羅擅于悲情敘事,只是當年悲情敘事的主體是個人,表現為對體制的批判,現在的主體是國家,表現為對帝國主義的控訴。
隨后,汪暉涉嫌抄襲事件,引發爭議。這一事件本來不具爭議性,因為是否抄襲,可以做出一個客觀的鑒定結論,不屬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范疇。但是,汪暉的“新左派”同仁,試圖把抄襲之爭指認為派別之爭,進而認定,否認對汪暉的抄襲指控意味著超越了派別之爭,否則就是陷于派別之爭。遺憾的是,這個奇怪的邏輯未能得到普遍承認。“新左派”在事實層面上的躲閃,反而增加了旁觀者對于“新左派”價值立場的懷疑。“新左派”對民主制度的批判,在歐美是知識界的主旋律,在歐美語境里,民主制度是重點批判對象。“新左派”把這種批判“照搬”進中國,不僅可以和國際學術界接軌,還可以獲得默認和鼓勵。
新浪微博出現于2009年,直至2010年春夏之交才具有公眾影響力。“周老虎”事件中網友的協作調查模式,更適合微博,唐駿和李一“不幸”遭遇微博時代。2002年,楊瀾的先生吳征曾經遭遇學歷風波,當時網絡在中國尚未普及,吳征很快化險為夷。唐駿沒有那么幸運,在微博網友的協作調查下,唐駿和他的“母校”西太平洋大學迅速現出原形。與之類似的是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李一,2010年第2期《中國企業家》作了李一的封面報道,微博尚不普及,這個報道沒有獲得太多批評。7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再次作了李一的封面報道,在微博的人肉搜索之下,“神仙”李一迅速被祛魅,他的各種“神跡”一一被證明純屬虛構。
周立波在“海派清口”中模仿領導人,被視為具有獨立精神的娛樂明星。這種解讀純屬誤會,做出這種判斷的觀眾,可能只是看了周立波的表演片段。如果看過周立波完整的表演,就會發現他對領導人的贊美大于嘲諷,對國際時事的看法更是沒有超出《中國可以說不》的水準。在舞臺上或者在電視屏幕里,周立波可以依靠團隊和表演技術進行修飾,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意見領袖”。當團隊出現變動,在微博上脫口而出的“海派粗口”使他迅速崩盤。靜水流深的價值重建
文化轉型比社會轉型更為緩慢、溫和,沒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影響更加深遠。2010年,文化領域的“清理門戶”,是價值重建的過程,靜水流深:
第一,是非大于成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評判標準,不僅在政治領域根深蒂固,在文化領域也是通行無阻。一個人只要成為“成功人士”,是否抄襲,是否偽造學歷不再重要——這種邏輯逐漸無法獲得認同。在汪暉涉嫌抄襲事件中。除了汪暉的“新左派”同仁,學者大都對汪暉持批評態度,并不限于持自由主義立場者。唐駿、李一、周立波在商業、養生、娛樂領域的成功,無法阻止他們在文化領域的失敗。當然,是非并未徹底代替成敗,唐駿和周立波在各自領域沒有受到直接沖擊。這與社會轉型尚未完成有關,在一個成熟的社會里,唐駿和周立波所要付出的代價將遠甚于現在。如果他們無法意識到這一點,依然認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終有一天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第二,差異和共識共存。當文化逐漸多樣化,相對主義成為新的旋律,怎么樣都行,甚至連抄襲和造假都被視為寬容的對象。“成功人士”在2010年的形象危機,說明這種相對主義面臨挑戰。網絡產生之后,公眾可以分為兩種,網民和非網民。微博產生之后。網民也可以分為兩種:上微博的網民和不上微博的網民。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在微博時代,公民意識將成為基本共識,這種文化轉型將推動社會轉型,兩者形成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