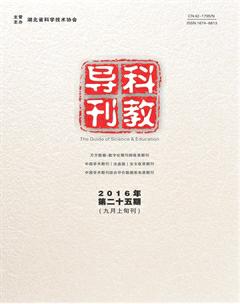再論中國近代史上的啟蒙與救亡
曹明臣 謝梅
摘 要 在近代中國,救亡和啟蒙一直是兩個突出的課題。救亡與啟蒙并非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救亡喚起了啟蒙,救亡深化了啟蒙;啟蒙的目的是救亡,啟蒙也會促進救亡。
關鍵詞 啟蒙 革命 救亡
1 問題提出
在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救亡和啟蒙一直是兩個突出的課題。二者是何關系?1986年, 李澤厚在《走向未來》創刊號上發表題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論文。他在文中指出,五四時期,“啟蒙性的新文化運動”與“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的關系是“相互促進”、“一拍即合”、“彼此支援”、“相碰撞而又同步”。遺憾的是,這種局面并沒有延續多久,嚴峻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再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
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遭到了學術界的普遍批判。王元化認為,“把啟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對的”。金沖及指出,“從根本上說,是救亡喚起啟蒙,還是救亡壓倒啟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丁守和也談到:“救亡喚起啟蒙,啟蒙是為了救亡。戊戌時期是這樣,五四時期也是這樣”。杜文君進一步強調,“救亡壓倒啟蒙”說歪曲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主題,改寫了中國近代的全部歷史”。彭明認為:“把馬克思主義排斥在科學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啟蒙運動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李良玉更是直接指出, “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救亡是啟蒙的邏輯發展,是它的必然趨勢。”
以上這些批評無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有的批評也不無偏差。那么,近代中國的救亡與啟蒙究竟是什么關系?如何深入理解近代中國的救亡與啟蒙之間的關系?首先就要明確界定救亡與啟蒙本身的內涵。
2 概念解讀
什么是救亡?李澤厚并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定義。但從概念的使用情況看,李澤厚的“救亡”至少有兩種定義:一是指“愛國反帝運動”或“反帝政治運動”;一是指“革命”,或“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嚴峻、艱苦、長期的政治、軍事斗爭”。可見,李澤厚對救亡一詞的使用極為隨意,他把救亡與革命混為一談,把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十年內戰、抗日戰爭等等統統納入救亡的范圍。其實,救亡與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救亡是指在遭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華民族出現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機面前,反抗外來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行為。對于革命的內涵,毛澤東作了科學的解釋:“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可見,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推翻舊的政權,建立新的政權。由于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國內的反動統治階級也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因而推翻本國反動統治階級的革命同時也打擊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這就使得革命具有一定的救亡性質。但是,不能因此而將救亡與革命混為一談。
什么是啟蒙?在李澤厚那里,“啟蒙”一詞的含義是始終一貫的。他認為,“啟蒙”就是在思想文化上“沖決各種傳統網羅,‘介紹西洋文化,攻擊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個體的‘自由、獨立和平等”。這種觀點從反封建的思想和文化的理性批判上來理解啟蒙并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對“個體的‘自由、獨立和平等”的理解。李澤厚認為,個體自由、個性解放等內容屬于“資本主義啟蒙思想體系”。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近代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經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正因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洗禮,文革之后人們便空前地懷念起五四弘揚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按照這種的理解,五四后“救亡壓倒啟蒙”未嘗不可。但問題在于,李澤厚對啟蒙的理解過于狹隘。在近代中國,對資本主義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思想的宣傳無疑屬于啟蒙的范疇,但啟蒙的內涵絕不僅僅止于此。五四之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分子用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思想向封建專制和蒙昧發起進攻,無疑也是屬于近代中國啟蒙的重要內容。
3 關系梳理
在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并非相互對立,二者同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重大課題,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首先,救亡喚起了啟蒙,救亡深化了啟蒙。
自鴉片戰爭開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日益成為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最為嚴重的威脅。在這一背景下,救亡圖存成為近代中國最為重要的歷史任務。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國的各個階級和階層都紛紛登臺亮相。在不斷的失敗中,先進的中國人逐漸認識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須要借鑒吸收近代西方的先進思想武器,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正是由此而起。綜觀近代中國的歷史,每一次思想啟蒙運動的興起,都是出于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戊戌維新運動就是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背景下開展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啟蒙運動。嚴復指出:“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在此。”因此,維新派在戊戌時期大肆宣揚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引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同時,維新派已經開始抨擊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嚴復在《辟韓》一文中,尖銳的指出,君臣之倫“不足以為道之原”,他批評韓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 梁啟超認為,“自秦以后君權日尊,而臣之自視,以為我實君之奴隸。凡國事之應興應革,民事之應損應益,君之所為應直諫犯顏者,而皆緘默阿諛為能,奴顏婢膝以容悅于其君,而‘名節二字掃地盡矣。至于今日,士氣所以萎靡不振,國勢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實千古最大關鍵矣。”對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無疑具有民主的啟蒙意義。除維新派之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甲午戰爭后對西方民主思想的宣傳也屬于資產階級民主啟蒙運動的范圍。
李澤厚認為,五四后“徹底改造社會的革命性政治,又成了焦點所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接受、傳播和發展,危亡的局勢和劇烈的革命使政治救亡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這無疑是把馬克思主義排斥在科學與民主之外,認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接受、傳播和發展打斷了中國近代的啟蒙運動。這種觀點不正確的。事實上,五四以后中國人對馬列主義的接受、傳播與發展,不僅屬于近代中國啟蒙運動,也進一步深化了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并沒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爭。相反,給了反封建以更銳利的思想武器。”在接受、傳播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偉大的思想武器,對中國封建思想文化開展了必以往更為有力的批判。
其次,啟蒙的目的是救亡,啟蒙必然促進救亡。
啟蒙作為一種思想文化領域的現象,是由特定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決定的,并為之服務。近代西方啟蒙運動發展的背景在于一方面資本主義初步發展,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另一方面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仍然是封建主義的。啟蒙的目的就是使人們從落后愚昧的中世紀思想禁錮下解放出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障礙。近代中國的啟蒙與西方的啟蒙有很大的不同。近代中國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其中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決定了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面臨的最主要的歷史任務。要救亡圖存,就必須依靠民眾的力量。離開萬眾一心的努力奮斗,就談不上真正的救亡圖存,救亡圖存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如何獲得億萬民眾的支持?如何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救亡圖存?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必需啟蒙以開民智,實現中華民族的覺醒。可見,在近代中國是救亡喚起了啟蒙,啟蒙的目的是為了救亡。近代中國的啟蒙可以稱之為“救亡型啟蒙”或“啟救亡之蒙”。甲午戰爭之后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掀起的思想啟蒙運動,直接源自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有著明確的救亡圖存的目的;五四運動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接受與宣傳,無疑也是一種救亡型啟蒙。
鴉片戰爭之后,為了救亡而對西方各種思想武器的引進都應從屬于啟蒙的范疇。這種救亡型啟蒙運動的發展也必然會促進救亡運動的進行。孫中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曾做過這樣的評價:“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可以肯定,沒有新文化運動在思想解放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就不可能有徹底的不妥協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沒有五四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廣泛的接受與宣傳,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后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是近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不僅僅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面貌,更使得近代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得以順利解決。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不應將救亡與啟蒙對立起來,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中國近代的救亡總是以啟蒙為先導,而啟蒙總是融入救亡運動之中。戊戌維新運動既是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又是偉大的民主啟蒙運動;五四運動也是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這樣。
參考文獻
[1]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下)[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830-832.
[2]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M].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2.
[3] 金沖及.救亡喚起啟蒙[N].人民日報,1988-12-5.
[4] 丁守和.關于五四運動的幾個問題[J].歷史研究,1989(3).
[5] 杜文君.十年來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評[J].中共黨史研究,1992(l).
[6] 彭明.關于半個世紀以來五四運動史研究的若千情況[J].中共黨史研究,1997(6).
[7] 李良玉.啟蒙、救亡與革命時代的終結——再論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J].南通師院學報,2002(2).
[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嚴復.嚴復集(1)[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0] 梁啟超.梁啟超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11]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12]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5)[M].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