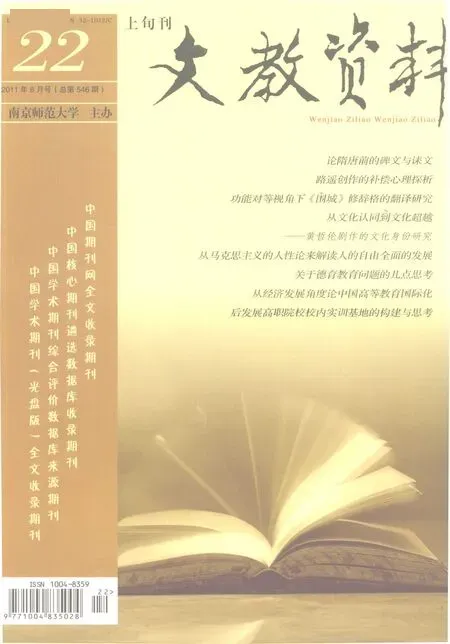詩可以群和而不同止于至善——關于古代儒家群育思想的美學審視
譚志偉
(華南理工大學 思想政治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1)
群育,即“群體適應性教育”,旨在通過對受教育者進行合群、合作、共處等內容的教育,促進其個體的群化和社會化過程。群育思想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孔孟為代表的古代儒家思想體系包含大量的“群育思想”,有博大而厚重的關于“群育思想”的智慧。它以“仁”為核心,始終圍繞如何構建和諧有序的人際與社會關系秩序這一問題來展開自身的群育觀念及理論。 “仁”通“人”,字形從“人”、從“二”,既表明人必定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又表明“仁”是作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存在的。在儒家看來,人與人之間和諧有序關系的基礎和紐帶正是“仁”與“愛”。“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 ”(《論語·顏淵》)有“愛”方成“仁”,不“仁”則難以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儒家“仁愛”思想由親及疏,由近而遠,以家庭為出發點,將孝悌觀念不斷擴大,表現在社會關系上,則視人若己、推己及人,恪行“忠恕”之道。一方面,從自身出發,視人若己,盡其在我謂之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另一方面,推己及人謂之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把“克己復禮”和“推己及人”相統一,凸顯教化的作用,強調個體的人格完善和人生責任,強調群體的人倫儀軌和道德規范,從而建立起各安其位、各膺其德的和諧群體關系和社會秩序,以最終實現“以中國為一人,以天下為一家”(《禮記·禮運》)的大同世界理想。
在此教化施行及其強調個體實踐的過程中,儒家群育思想始終堅持“凡先王教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記·文王世子》)這一塑造和實現理想人格的“雙途徑”施教道路,對藝術—審美采取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注重藝術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強調:“樂者,通倫理者也。 ”(《樂記·樂論》)強調以美導善的方向和理念,強調美育對人格培養和人際關系秩序構建的積極作用,從而使其群育思想之玉與美育思想之泉相互滌蕩,閃爍出情理相融、美善雙輝的審美意趣。
一、詩可以群,彰顯禮樂相運的藝術功能美
“《詩》可以群”一語出自《論語·陽貨》,是孔子著名的關于《詩經》社會功用的“興觀群怨”觀其中的一個命題。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之名”。對“《詩》可以群”的理解,孔安國注釋為“群居相切磋”,是指詩歌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交往和關系認同,促進個體與人群的和諧相處。一方面,《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的基本內容與儒家“禮”的倫理規范和價值取向相一致。學習《詩》,其中所滲透的宗法倫理道德必然會對人起著潛移默化的訓導作用。同時,《詩》是禮儀活動所奏的樂歌,包括禮與樂的精神,當《詩》被配上合于雅正之義的音樂后,便與禮儀進一步相結合,使“禮”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從而發揮出和諧上下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成為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群體關系和諧的一種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詩可以群”這一命題積極肯定了詩樂對個體道德情感培養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對群體的精神培育和人文化成功能。以詩的優美意境和音樂的獨特魅力娛樂人的心志,凈化人的靈魂,通過對生命主體的普遍關懷和精神慰藉,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從而使原本氣息相關、生命相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達致生命契合,形成人人友愛相處的融洽氛圍,將社會維系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在這里,詩樂,并不單指詩歌和音樂,它具有很強的綜合性,音樂、詩歌、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各種藝術形式和手段也被包含其中,近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藝術教育或美育。事實上,儒家正是把這種綜合性的藝術教育視為其君子培養的必然途徑。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一個人主觀意識的修養,要從詩開始,用樂來完成。在孔子看來,理想人格固然需要規范的“禮”和行動的“踐”來實現,但是作為人生境界之美的體驗必須通過心靈來完成。藝術、藝術教育或美育恰恰是直接指向人的心靈和情感的,蘇霍姆林斯基說:“美是一種心靈的體操,它使我們精神正直,良心純潔,情感和信念端正。”藝術教育具有鮮明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又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說教與規勸。它通過運用語言、動作、線條、色彩、音響等各種手段塑造出立體、多彩、直觀的藝術形象去影響受教育者的感官和心理,以其鮮明的形象性和強烈的感染性影響著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從而使受教育者在美的享受中得到熏陶。情感性和愉悅性,是藝術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通過藝術的滲透將人的審美情感內化為道德情感,并作用于人的道德行為,從而使受教育者不僅從理智上認同教育者的道理和觀念,而且激發起兩者之間的情感認同,并使審美情趣與道德情感相互交融,達到感性與理性的和諧統一。同時,藝術教育注重營造和諧、寬松和快樂的教育氛圍,充分利用各種生動有趣的藝術素材和使受教育者喜聞樂見的各種方式、手段和組織形式,讓受教育者在愉快輕松的狀態下投入教育活動之中,在學習和實踐過程中能體驗到其中的快感和樂趣。藝術教育,正是通過這種“寓教于樂”的教育教學,使人學有所樂、樂有所得,真正收到使受教育者“悅耳悅目、悅心悅意、悅志悅神”的教育效果。
可見,藝術教育在實現以“樂”求“禮”、以“樂”成“禮”的過程中,一方面,始終以情感培養為目的,以情感交流為橋梁,具有強烈的“動情性”,能引發受教育者的情感運動,激發他們的審美情趣,達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的情感共鳴和理性認同。另一方面,“禮”與“樂”在功能上又是相輔相成的,藝術、審美需要正確的審美觀和高尚的思想情操為基礎,藝術教育需要把藝術性和思想性相結合,只有當受教育者對事物的美丑評價與善惡評價相一致時,隨之而來的道德情感才能有助于他們的審美情感得到進一步增強,才能在藝術教育的過程中真正以情感人、以美趨善乃至美善合一,從而實現提升受教育者道德情感、深化受教育者道德認識、改善受教育者精神風貌的目的。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孔子之所以重視詩樂教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君子明于禮樂,舉而措之而已。 ”(《論語·陽貨》)對于孔子來說,禮樂都不過是手段,是一種以禮樂方式和諧群體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的手段,“和群體、正天下”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二、和而不同,追尋平等性共存的人際和諧美
“和而不同”的命題是孔子在繼承春秋以前“和”、“同”觀念,以及史伯、宴嬰“和同之辯”基礎上,著重從社會和人倫的角度所提出的一個重要理念,其中蘊含著深刻而豐富的儒家群倫思想。“和而不同”語出《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句意為,君子和諧相處卻不盲目茍同,小人盲目茍同卻不和諧相處。“和”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字義為口聲相應、聲樂調和,并以此引申出和諧、和睦之義。“同”者,則強調儀軌、外在行為的絕對一致,而不管內心如何。孔子把“和”與“同”作為區別君子與小人的標準之一,宋儒更明確地以義利觀來解釋“和而不同”,認為君子的“和”是“義”的結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驅使。正如朱熹所言:“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從哲學角度看,“和而不同”揭示了社會事物的多樣性統一。“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平衡或統一;“同”則指事物的絕對一致、等同。“和而不同”這一命題揭示出:差異,使萬物品類豐富,相輔相成;和諧,則使萬物處之有道,共生共長。自孔子后,“和而不同”思想成為儒家的一個重要價值觀,它主張人的獨立性,主張在尊重個體觀念獨立和差別的前提下,尋求個體自身的立己、處世法則,探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共處之道。儒家把一種上下內外的高度和諧作為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生活的最佳狀態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儒家和諧觀是一種具有辯證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普遍的和諧觀。
和諧,作為美學研究的對象,對“和而不同”同樣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和諧,不僅是一種圓融的狀態,而且是一種美的境界。和諧美之所以形成的一個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事物間相輔相成,對立統一。在古代中國,《易經》通過陰爻(--)與陽爻(—)這兩種不同性質卦象的交互變化,闡述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對立統一、生生不息的內在規律。《樂記》指出:“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將“中和”與音樂藝術相結合,這既是對儒家中和之道的發揚,又是對音樂藝術和諧論的美學創造。在古希臘,畢達哥拉斯首先提出了“美即和諧”的命題,赫拉克利特也指出:“相反者相成,對立造成和諧。”“由聯合對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諧,而不是聯合同類的東西。藝術也是這樣造成和諧的。”古希臘美學家普遍認為:和諧起源于差異的同一,對立的統一,不協調的協調,不一致的一致。這種看法一直被西方美學家奉為美的圭臬。事物間的和諧美如此,人與人的和諧美也如此。人,不僅作為生物學上的自然人,而且是社會學上的社會人。人之美,既屬自然美,又屬社會美。而社會美的中心恰恰是人之美,是人與人關系的和諧之美。正是在這個意思上,我們所理解的儒家“仁愛”說應同時也是一種美學原則,一種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美學原則。正是儒家“仁愛”說賦予了“和而不同”命題更深刻的內涵。它使我們認識到,群體的融洽和諧必須建立在承認和尊重社會個體差異性,并促進和造就差異性個體平等共存的文化心理、信仰和價值觀念基礎上。“不同”者,社會個體和角色的多樣性也“和諧”者,統一于“仁愛”之美也。把每一個社會個體都視為具有道德自覺的平等主體,并具備可以進行平等溝通和交流基礎的平等主體。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努力通過對人與人之間角色、身份差異性的肯定,促進其彼此間的相互認同、尊重、理解和關愛,使平等成為一種價值追求,樂群、愛群、協群成為一種道德素養,這樣,才能真正把社會維系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因此,人之美,應是一種群體和諧之美,一種建立在平等性基礎之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諧美。“和而不同”不僅成為一種處世法則,而且成為一種社會理想和人性美的境界。
三、止于至善,涵養文質彬彬的人格精神美
對于和諧的追求,無論是中國古代儒家立足于社會倫理的闡釋,還是近現代美學理論立足于心理觀照的論述,我們都不難發現,強調通過對個體自身美(即人的自身和諧)的修煉與加持來達致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間的和諧,是實現自身道德超越和自他、物我、天人和諧共處、無間契合的一條必修之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大學》)開篇明示儒家君子道德修養的三種途徑和境界。“明明德”,朱熹在《四書集注》中注釋:“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朱熹將第一個“明”釋為“使之明”,即將人天性中就存在的高尚德行重新顯現。“親民”則與“明明德”相互呼應,指在道德的養成過程中,以“明明德”為道德理想,以“親民”為道德實踐,通過為民、利民、服務于民來實現入世利人的理想,而且,只有將“明德”與“親民”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人、自利利人,從而使個體的精神境界升華到“至善”之境。所謂“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已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是鎖定目標不動搖,“至善”是道德修行到達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這種境界的實現,從來都不僅僅是一種純道德的恭行與實踐,而是一種將美善合于一身的身心統一之境,是身體、氣質、德性、意志和精神的有機統一,是生命的感性具體和美學超越。它是一種倫理道德而又超越倫理道德的審美境界,具有令人欣賞、景仰和不懈追求的審美狀態,是一種“浩然之氣”的人格美。
人格修養,既是一個道德問題,又是一個美學課題。人格修養既關涉到個體的安身立命,又與社會道德風尚和精神追求緊密相連,其理想狀態將達于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美學境界。在儒家看來,這種美學境界與“君子”人格是合而為一的。它不是一種外在的物境,而是一種通過修煉達成的自由心境。君子,是孔子思想體系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中國古代儒家對實現或努力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社會個體的尊稱與肯定。孔子贊美“文質彬彬”的君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這里的“文”與“質”都是就人品道德的修為而論的,其中,文,類似于我們今天的行為、語言和文飾之美;質,則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心靈、精神和道德修養之美。二者的結合與相濟相成,才能謂之“彬彬”。可見“文質彬彬”是孔子從內外兩個方面對他的培養目標——君子所提出的道德訴求和審美要求。孟子也認為,人性是善而先驗地存在的,人格美所內含的善不是一般的善,而是由仁義所充實的善性:“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孟子·盡心下》)但人格美不是天生的,這些天賦的道德秉性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它需要社會個體通過主觀的努力,通過意識的修養,在善的基礎上不斷充實擴張、磨煉修養而成。因此,一方面,人應該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煉自己:“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另一方面,要寡欲清心,“善養浩然之氣”,積極追求“萬物皆備于我”、“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一個人必須從自身出發,從自身和諧美的建設著手,通過自身道德涵養和審美升華來實現人身心、人格的和諧發展。其中,身心和諧是自身和諧的起點,只有身體健康、心理正常才具備成為一個自身和諧美的人的基礎;人格和諧是自身和諧建設的關鍵,只有思想與時俱進、人格健全完善才能超越小我,擔當起社會建設的責任,從而努力達致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更好地體現及處理自身與外部的各種和諧關系。在此基礎上,自覺、主動地接受美的熏陶。無論是自然美、藝術美,還是社會美,都蘊藏著精神理想和思想境界,都能使人在美的觀照中心靈受到震撼,情感得到陶冶,精神得到凈化,氣質獲得升華,進而達致高尚的人格和審美超越。“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這樣,天與地、人與人,何其美也,何其和諧。
[1]杜衛.美育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102-103.
[2]王朝聞.美學概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王旭曉.美學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趙伶俐.百年中國美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陳小鴻.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冉祥華.美育的當代發展[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7]向春.中國傳統群育思想及其現實意義[J].高等教育研究,2008,8.
[8]劉金榮.試論孔子詩可以群的命題含義及文化意蘊[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11.
[9]李廣龍.孔子詩可以群的歷史成因及內涵管窺[J].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10,9.
[10]孫光貴.和而不同疏證[J].長沙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5,1-2.
[11]王敬華.儒家和而不同思想與和諧世界[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2009,4.
[12]顧勤.孔子的樂教觀及其對當代藝術教育的啟示[J].北方工業大學學報,2006,6.
[13]黎紅雷.孔子君子學發微[J].中山大學學報,2011,1.
[14]伍永忠.儒家君子人格的美學內涵與和諧社會[J].長沙大學學報,2007,11.
[15]于民雄.孔子的君子人格[J].貴州社會科學,2009,12.
[16]王明居.美與和諧[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