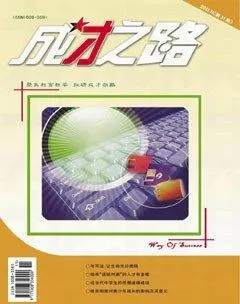岑可法:讓生命充分燃燒
浙江大學熱能工程研究所至今已有近30位學者前往大洋彼岸深造。幾乎所有人在學成后,又都重回母校。
吸引這些年輕人“回歸”的是岑可法。
上世紀60年代,岑可法自己正是坐了7天7夜火車,從留學4年的莫斯科回到北京。再往前追溯30年,他留學法國的父親,放棄去往瑞士的優厚待遇,毅然回到日本侵略下的戰亂中國。
對信仰的追求終生不渝
熱能所的年輕人將岑可法視為“偶像”,34歲的教授羅坤就是其中一人。從本科院校考入浙大,他追的就是岑可法這顆“星”,即使后來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時被校方挽留,他依舊決定回國追隨岑可法。
“岑院士的這個團隊,讓我看到希望,這不僅指科研上有機會,而且是人生價值有實現的可能。無論從事哪一行,這不就是我們最大的盼望么?”羅坤說。
岑可法也有自己的“偶像”——“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這位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兵工事業的開拓者,在生產與研制武器彈藥中,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殘,但仍以頑強毅力堅持戰斗在生產第一線。20世紀50年代,吳運鐸的自傳體小說《把一切獻給黨》出版,這本書深深影響了正讀大學的岑可法。在后來的人生道路上,無論是宿于豬圈旁,還是蝸居斗室,吳運鐸都是他心中的一盞明燈。
岑可法對事業的追求百折不撓,對信仰的追求更是終生不渝。
岑可法的童年正值日本侵華期間,全家顛沛流離,目睹生靈涂炭,深感國家強大之重要。“中國共產黨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也給了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出國深造的機會。”1959年,正在前蘇聯留學的岑可法第一次向黨組織遞交了申請書。然而,正當黨組織考察通過他為預備黨員時,1966年,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他的預備黨員資格也不了了之。
1976年,岑可法再次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1983年,也就是在遞交申請的第24年,岑可法終于得償心愿,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正是因為有了堅定的信仰,岑可法為黨的事業付出了自己的所有。2010年1月,岑可法在他75歲生日的時候,將多年積蓄的350萬元捐給了浙江大學設立獎學金:“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辦法解決能源問題,學科的發展要從基礎抓起,培養要從青年開始,我希望浙江大學能夠培養出未來的大師。”
把“冷門”做成“顯學”
能源的清潔利用,是21世紀的“顯學”。作為擁有多項自主知識產權的科研負責人,岑可法帶領團隊獲得過11次國家獎,取得一百多項發明專利,在世界能源技術發展中刻下了中國符號。
但在五十多年前,這可是個冷門。當時他剛大學畢業,被國家選拔赴當時的蘇聯留學。同行者大多填報火箭制造、潛艇和自動化等尖端學科,只有他一人,選擇了“煤的清潔燃燒”。負責專業填報指導的錢偉長問他原因。岑可法說,自己本科讀的是熱力發電,中國的電主要來源于煤,很多問題還沒有國產的解決方案,研究煤雖然又臟又不起眼,卻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1962年,獲得副博士學位的岑可法回到國內,到浙江大學任教。
科學無國界,而科學家有國籍。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不僅要發出聲音,還要站到前沿,岑可法畢生為此奮斗。他說,國家和人民的重大需求就是我的立身之本。
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幾位美國同行掏出一小袋黑色泥漿似的東西,不無炫耀地說:“今后,你們國家肯定要掏幾千萬元來購買我們這個‘寶貝’。”
岑可法偏不信邪。他帶著攻關小組日夜鉆研,終于在1982年試驗成功用煤、水和少量添加劑混合的“寶貝”,在鍋爐和工業爐窯中100%取代了油。如今,“水煤漿代油清潔燃燒技術及產業化應用”技術已運用在我國近500臺鍋爐上,每年為國家節約燃油約250萬噸,使我國在這一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由于岑可法所帶領團隊數十年的研究推動,在中國這個產煤大國,對煤的利用不再是簡單地一把火燒了——煤還可以熱解氣化、制油,甚至從煤灰中提煉礬、鋁、鈾等金屬,煤渣還可做水泥,總之,煤渾身是寶。
由煤的高效利用,岑可法又聯想到了生活垃圾的處理。“垃圾是被放錯了的資源,為什么不用?”岑可法和他的團隊研究開發了生活垃圾循環流化床清潔焚燒發電集成技術。2006年,這個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這也是生活垃圾發電技術第一個國家獎。
垃圾發電的二惡英污染問題,是個國際難題。岑可法及團隊建起了超潔凈二惡英實驗室進行攻關。根據比利時SGS二惡英實驗室的監測數據,其排放大大低于國家標準甚至優于歐盟標準。這項處理技術被國際廢棄物處置協會主席Themelis譽為當今世界五大主流焚燒技術之一。而同等規模的國產化設備,投資比進口技術設備至少要少一半。由于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推廣,目前國外技術也不得不把價格降下來。
如今,岑可法又帶著團隊開始“985”新一期重大研究計劃“微藻能源”項目的研究。這是為解決石油危機布下一枚長遠的棋子。
啟迪思維:多教青年人想法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岑可法看來,好的老師只能給學生傳授七成的專業知識,另外三成并非是有所保留,而是要給學生留下思辨的空間。“我們不能一味照本宣科,要在課堂上激發同學們的好奇心,迫使他們去思考;讓他們領略到國際前沿的動態,培養他們創新的思維。”岑可法說。
上世紀90年代,岑可法在為研究生講授專業課程時,就經常告誡同學們,課本上的知識很多都是幾十年前的內容,比較陳舊;而且大多只是對現象進行描述,細節和過程的解釋不甚清楚,這些內容對目前的科研創新沒有什么幫助。因此,同學們要自己去思考和鉆研這些問題,爭取有自己的創新想法。
“岑老師在講課時,對課題的前沿方向談得很多,總是會講到國內的研究現狀與國外的差距,鼓勵學生有自己的思考。”岑可法早年的研究生邱坤贊副教授說:“岑老師認為專業基礎知識比較成熟了,同學們自己自學也可以掌握。老師要多教些國際上知名科學家們正在研究和準備研究的方向,了解他們的觀點,特別是思考的方法。”
現在,在每年的新生教育周,岑可法都會為新進校的本科新生作入學教育輔導講座。他提醒同學們,他在一堂課上講述的內容70%是成熟的知識,剩下的部分是國際上最前沿的觀點和看法,未必正確,需要同學們自己去思考、去辨別。他還專門為本科生總結出在知識經濟時代競爭成才的22個方法,包括正確的哲學思想和方法論指導、轉變傳統觀念為競爭的觀念、勇于創新、敢于學科交叉、即時反省、把個人利益融于國家集體利益、抓住事物本質看問題等。
周勁松教授還清晰地記得,有一次上專業課時,岑院士用“清明時節雨紛紛”這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詩句來講述科研問題。“他說,讀詩要學會把握核心,這句話描述的重點只是‘雨’,那么在科研上也一樣,要學會抓住重點,想問題、解決困難都是要通過攻克核心問題來達到目標。”周勁松說,岑院士教給他的這種學習和科研的方法,讓他在努力成為好老師的過程中,深深受益。
冰成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岑可法常常以此鼓勵年輕人努力去超越自己,超越前人。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長江特聘教授駱仲泱說,在剛開始接觸科研的時候,在知識、學術經驗、工作方法上,深受岑院士的影響和啟發。即使到自己也在學術科研上慢慢立足后,岑院士科學的方法和思路,特別是宏觀思路的把握,還對自己在大局上把握學科發展的方向起到指導作用。
岑可法曾打過這樣一個生動的比喻:跑一萬米有兩種跑法,一種是慢跑,大家都可能到達終點,成績不相上下;另一種是快跑,很多人會體力不支,中途退出,但也有人會繼續保持速度跑下去,創造新的紀錄。“年輕人要堅持快跑,勇于領先于常人。”岑可法說。
一捆折不斷的“筷子”
岑可法說:“一根筷子,再堅硬也會被折斷;一捆筷子,想折斷就難了。”
他的科研成果引人注目,而更為人稱道的是他帶出的一捆折不斷的“筷子”——科研團隊。30多年來,岑可法培養出5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2位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5位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3位提名獎獲得者以及20多位國家級高層次人才。他周圍,堪稱群英薈萃。
只要年輕人有能力,岑可法就一直壓擔子、出課題,把出國出名的機會讓給你,千方百計“逼”你成才,一路上不知打破了多少“慣例”。
20世紀80年代初,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對教授來說都是稀罕事,而岑可法卻跑到北京為博士生倪明江爭取參加在美國舉辦的世界煤漿會議:“倪明江有能力參加,資歷不能等同于能力。”如今倪明江已是我國工程熱物理學科首位博士學位獲得者,浙大可持續能源研究院院長。
按照當時慣例,不到60歲成不了教授。岑可法卻力主打破年齡限制,純以業務能力來考察評定資格。熱能所的許多教師在35歲之前就晉升為教授,如此年輕的教授團隊,在大學校園并不多見。
“岑老師幫我較早地獲得了一個廣闊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我得以做到以前沒有資歷去做的事情,可以更自由地開展研究。”倪明江說,“有一些學科,常是‘領頭雁’一枝獨秀,老先生一旦離開,學科發展后繼無人,熱能所的人才隊伍卻有梯度,保證了學科的可持續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長江學者”樊建人說,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岑院士很少成為第一獲獎人,其實獲獎項目他都參與,而且在不少項目中是負責人,可他總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為的是讓更多年輕人走上學術舞臺。
2002年,有件小事曾令岑院士傷透腦筋:自己的熱能工程研究所要招研究生,除了本系學生外,尚需材料、力學、低溫、化學甚至農業等方面的人才,可是怎么招?他更看到了傳統的導師——博士生一對一培養方式的弊端。“現在,我們強調的是跨學科交流和合作,但一對一單元式培養方法卻限制了博士生的研究范圍,也不利于充分發揮導師和博士生的長處,難以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和完成高水平的學位論文與科研成果。”岑可法說。
為了造就高水平、優秀的工學博士,經過多年實踐和探索,岑可法創造性地提出了“導師群體”的人才培養新方法:以他本人和倪明江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由18位高水平教授組成的導師組集體指導博士生科研團隊,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圍繞能源與環境學科發展前沿,以導師群體和博士生科研團隊的形式承擔各類科研項目,分工合作,協作攻關。
“只有心底無私、甘為人梯的學術帶頭人,才可能成就一個團結的學術團隊。”倪明江說。
眼見接班人一茬又一茬地起來了,欣喜使這位76歲的老人活力倍增,校園里常見他健步如飛,討論課題從中午到凌晨也不見疲態。
岑可法:男,1935年出生。廣東南海人。著名工程熱物理專家。1956年畢業于華中工學院動力系,1962年獲莫斯科包曼工學院動力機械專業副博士學位,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浙江大學工學部學術委員會主任,熱能工程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動力工程學會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第四屆專家顧問組成員,中國顆粒學會常務理事,教育部高等學校能源動力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在水煤漿燃燒技術、流化床技術、煤的清潔、高效燃燒及強化傳熱、煤炭多聯產綜合利用及污染防治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