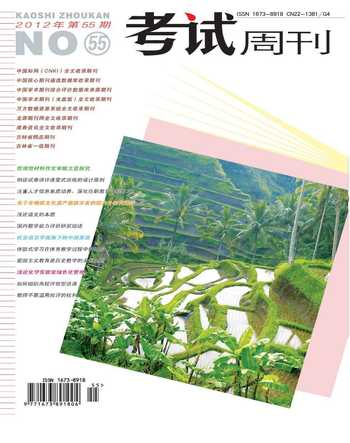從張愛玲和伍爾芙看東西方女性主義在文學作品中體現的異同
摘要: 女性的地位問題一直是全世界女性關注的話題,東西方由于文化的不同,女性覺醒的方式也不同。本文擬選取相同時期西方和中國女性主義作家代表——張愛玲和弗吉尼亞·伍爾芙進行分析并比較她們寫作方式的異同。
關鍵詞: 弗吉尼亞·伍爾芙張愛玲女性主義東西方差異
在全世界,女性的地位問題一直是人們,尤其是女性關注的問題。西方的女性主義如果從1791年發表的《女性與女性市民的人權宣言》算起,比中國女性主義的覺醒要早了很多年。中國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潮影響,五四前后出現了第一批既受過傳統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的現代知識女性。本文擬選取西方和中國的兩個女性主義作家代表——張愛玲和弗吉尼亞·伍爾芙進行分析并比較她們寫作方式的異同。
伍爾芙出生在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典范家庭,早期遵循著嚴格的社會禮儀規范。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中女性往往被塑造成“家庭天使”的角色而被迫充當繁重的家庭經濟事物的管理者。但是作為文人雅士的父親實際上依然是父權制的家長,一直按照“女人的最高天性就是為男人服務”的教條來管理家庭。男性潛意識里對女性的蔑視和母親的早逝為伍爾芙的女性主義思想提供了自由發展的機會。
五四運動期間,西方文化大量傳入中國,男女平等,婦女解放是許多進步女性仿效西方提出的口號,張愛玲的母親是最早逃出腐朽的封建官僚門庭,留學英法的新女性。但是她們的受教育是在父權制允許的范圍內,依靠家庭經濟上的救助實現的。因此她們對父權社會的抗爭是極不徹底的,但畢竟為中國的女權運動開了一個好頭,同時更為張愛玲做出了勇敢的榜樣,在張愛玲身上及她后來的作品中均表現出了強烈的女性意識。
從家庭背景來看,伍爾芙和張愛玲的家庭是不同文化體制下的父權社會的縮影。共同點是她們的女性主義思想都受到了家庭的影響,她們已經認識到了“菲勒斯中心”對女性的壓迫并且有了反抗的意識。不同點是張愛玲的母親以親身經歷從正面引導和幫助了張愛玲,使她勇于與封建家庭決裂,伍爾芙的母親則從反面使伍爾芙感到解放女性的緊迫性。
20世紀初葉的英國,女性意識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衍生、發展已達到了高潮。伍爾芙作為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見證人,繼承和發揚了女性文化的傳統。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伍爾芙說:“女人要有一間自己的屋。自然是女性獨立的標志。因為我們首先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將這間屋子租下來或買下來。在這個有鎖的房間里能夠隨心所欲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之前在西方國家開展的女權運動大多以男性社會權利和語言形式作為參照物,忽略了對父權制社會文化本身的質疑。比如《簡·愛》的女主角已經取得了經濟上的獨立,并且發出了男女平等的呼聲。但是不難看出,她對羅切斯特情感上的依賴依然是父權社會女性的悲哀,她所追求的平等是依附于男性的平等,也可以說這并不是一種“自覺”的女性運動。與此相比,伍爾芙的《一間自己的屋子》就是一封女權主義的宣言書。
在女性主義剛剛傳入中國時,它更多是依附于革命的需要而產生,女性還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與男性相對的個體出現。一直到了三四十年代聽見了真正來自女性的聲音。張愛玲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使男性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對女性都形成了很大的優勢。張愛玲小說里的男性在生理或心理上存在著某種缺陷,這也正體現了女性對男性統治地位的挑戰。在《連環套》中,十四歲的霓喜被賣給綢緞店老板雅赫雅,她和他生活了十二年,卻始終沒有正式的妻子名分。霓喜的正當要求卻得不到丈夫的滿足,反而招致毒打。當雅赫雅發現霓喜與崔玉銘有染時,作為“家長”象征的丈夫便逼霓喜離開這個家,他“手握著剪刀口,立在她跟前道:‘你給我走!你不走我錐瞎你眼睛!”丈夫對“妻子”的淫威在此毫無保留地表現了出來。這是宗法父權賦予男性的一種權力,也就決定了女性從屬于受虐的命運。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充滿了對男性社會權威的反抗和嘲弄,她筆下的男性角色被有意識地矮化了,這也反映了經過長時間壓迫的中國女性開始對男性引以為傲的地位和體力提出了質疑。
在19世紀到20世紀,女性的戰場主要是家庭,所以伍爾芙和張愛玲無一例外地把寫作的焦點放在女性的家庭問題。女性要想真正在社會上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首先應在家庭中擺脫對男性的依賴和服從。在西方國家,女性往往被塑造成“房子里的天使”,為了男性的利益犧牲了“自我”。在東方,“賢妻良母”是女性應該扮演的角色,忍耐和馴服是女性的美德。所不同的是,伍爾芙提出的女性主義觀點更多是以挑戰西方的理性主義文化為前提的,而張愛玲則有意識地撼動儒家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統治。
西方現代文化是以理性主義思想為前提的,主張以理智抑制人性的欲望,以真理的取得為終極目標。這種理性至上的觀點給西方的男性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男性蔑視女性,貶低女性找到了借口。伍爾芙的小說《到燈塔去》塑造了拉姆齊夫婦。拉姆齊性格孤僻,處事刻板,被男權社會看做最偉大的哲學家和理性的代表。拉姆齊夫人則是情感與人類美好品質的化身,相對于拉姆齊的呆板,不近人情,拉姆齊夫人是賓朋之間、家庭成員之間傳遞情感、建立穩固關系的紐帶。拉姆齊先生狂熱追求所謂“生硬的真理”,完全忽視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強烈鄙視女性的想象世界,但是他又離不開情感的慰藉。當拉姆齊夫人以人類的想象支撐起了感情的、希望的世界時,伍爾芙反諷地顛覆了理性與情感的等級關系。《到燈塔去》中的燈塔正體現了兩股勢力——理性與情感沖突的結束。伍爾芙在這種小說中就是要為男女兩性所代表的兩種對立情感與原則找到合理的途徑,以使它們達到有機和諧與統一。拉姆齊對妻子的依賴正說明了理性不可能統治情感。理性不是真理。沒有了情感,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了。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認為人、家庭、社會和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天地萬物渾然一體。在家庭中,“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把女性禁錮在從屬的地位。儒家文化是宗族制的文化,本質上是父權制的文化,宗族制為其外在表現形式。《金鎖記》中的七巧是張愛玲小說里難得的非常徹底的人物。她本身可以說是父權制文化的犧牲品。因為姜二爺的殘疾,她得以“幸運”地嫁入姜家,但因著她的出身和丈夫的原因,她在這個封建大家庭中一直被人看不起。曹七巧是語言粗魯,舉止怪異,甚至勾引小叔子。一切違反父權制文化的事情七巧都敢做,所以才有分家一節中,當所有的人對九老太爺的分家方式保持沉默時,只有七巧說出了異議。曹七巧把自己裝束成一個可怕的女巫與惡魔般具有威懾力的女權主義者進行生存和發展,但她畢竟還是抗爭了,在暴發中顯示了女性的力量。
從女性主義的大旗豎起至今,歷史已經經歷了兩次思想的浪潮。在西方和中國,伍爾芙和張愛玲都用她們的智慧和思想為女性主義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陳紅玲.蘇青與張愛玲的女性意識[J].求索,2005,3.
[2]陳志杰.文化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化——伍爾芙與張愛玲的女性主義思想比較研究[J].宜春學院學報,2004,7.
[3]郭元波.從《一間自己的屋子》解讀伍爾芙同時代女作家的社會空間[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05,5.
[4]李紅梅.伍爾芙的敘述藝術與女性主義[J].學術交流,2005,8.
[5]瞿華兵.反抗背后的人性掙扎——《金鎖記》中的女性主義[J].銅陵學院學報,2005,3.
[6]潘華凌.殊途同歸神交與往——伍爾芙與張愛玲的女性意識比較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