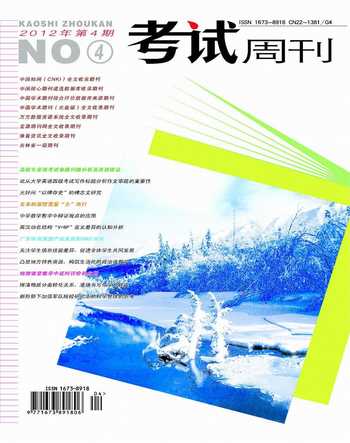文本的深挖需量“力”而行
陶梨
教學要能促進學生的發展,教學內容必須定位于學生的最近發展區。教師對文本的深挖必須與學生的實際掌握能力相結合,教師的個性解讀同樣也要量“力”而行,對學生的真實情況要有準確的把握。只有學生真正有所“得”的課堂,才是理想的課堂。
在一次青年教師“同題異構”的比賽活動中,我聽了兩堂課,所選的文章都是課外的《借你一個微笑》,講述的是一位富有智慧的老師通過向學生借微笑的方式,讓一個曾經內向而不自信的孩子變得樂觀而堅強地面對生活中的困苦的感人故事。兩位任課老師的教態都親切自然,語言流暢,教學層次又清晰,教學環節的設計也很巧妙,都能循序漸進引領學生解讀文本。但是同為借班上課,對象同為初一年級學生,課堂氣氛卻是截然不同,一個是沉悶平靜至極,參與的學生寥寥無幾,老師幾乎陷入孤軍奮戰之局面;一個是活躍熱鬧異常,學生個個躍躍欲試,師生之間不斷形成互動,學生們“妙語連珠”,引來聽課老師的喝彩。
反觀這兩位任課老師的教學設計,前者通過分析故事曲折、有波瀾的特點,理解抓住人物描寫中的神態描寫來透視人物心理、表現人物性格特征的寫法,最后請學生發揮合理的想象,運用相應的人物描寫方法進行“牛刀小試”,評課者認為盡管這堂課學生的配合很不到位,卻是扎扎實實地將閱讀與寫作緊密結合在一起。后者在理清故事情節、掌握人物形象之后,對文章精彩的神態描寫片段進行賞析,進而深入掌握“微笑”的內在含義,從而把握文章主旨。評課者認為,這堂課的課堂氣氛很好,學生真正動起來了,但老師對文本把握的深度頗為不夠。
諸多評論之下,我十分困惑。深挖文本,老師卻得不到學生的“待見”,難道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師生實現互動,課堂氣氛融洽,卻又說老師對文本的把握過于淺顯,難道“魚”和“熊掌”,就不能兼得?
心理學家維果茨基在“最近發展區”的理論中指出:“教學必須走在發展的前頭,為發展開路。教學要能促進學生的發展,教學內容必須定向于學生的最近發展區。”[1]大量事實證明,只有針對最近發展區的教學,才能促進學生的發展;如果教師不切實際,教學內容遠離“最近發展區”,那對學生而言,定然會心理上屢受挫折壓抑,課堂氣氛自然是沉寂了。因此,語文教學的起點就是要了解學生到底知道什么,探明了這一點,語文教學才有開展的理由和前提。
一、文本深挖必須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告訴我們,學生都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教師應適時滿足學生的基本需要,讓他們在課堂上獲得“成功的體驗”,這樣可以增強他們的自我效能感,進而充分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調動他們的學習積極性[2]。教師在引領學生深入解讀文本的同時,若能站在學生的角度,深諳他們的喜好,了解他們的已知和未知,定能更好地實現學生、教師、文本三者之間的對話。在對話的語文課堂上,師生積極參與介入,教師在與文本的對話實現解讀后,便能正確發揮好自己的角色和作用,通過啟發教學,引導學生拓展創造性思維,引發學生進行創造性探究學習,不斷將對話引入更高的層次,從而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文本的深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文本細讀。唯有細讀,才能深入文本;唯有細讀,才能演繹文本精彩。文本的細讀主要包括對重點字詞的推敲、文章主題的探究、寫作背景的關注、人物形象的剖析、精彩語言的賞析、寫作手法的分析等。但是教師深挖文本,并不是說越深就越好,越多就越好,把文本所掩藏的文化性質或藝術性都翻出來就是“解讀得好”。解讀文本,必須把握一個“度”和“量”,立足于學生實際,從而引領學生在閱讀文本中有所獲益,這些獲益應該是貼近學生生活和認知水平的。否則,你在講臺上聲嘶力竭,說得精彩無比,而臺下的學生卻仿佛與你有一億光年的距離。如上述的第一位任課老師,他既要讓學生了解小說故事曲折、有波瀾的特點,又要讓學生理解抓住人物描寫中的神態描寫來透視人物心理、表現人物性格特征的寫法,實在是顯得力不從心。
我認為,時下十分流行的教師對文本的個性解讀(另類解讀)其實也是文本深挖的一種,只不過它更多地帶有教師個人的立場觀點、思想感情、生活經驗、文化修養、藝術趣味,是語文教師基于自身生活閱歷和認知結構對文本進行的獨特解讀,再將此種解讀用自己擅長的教學方式(方法)傳遞給學生,或是跟學生對話。《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指出:“逐步培養學生探究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創意的閱讀,利用閱讀期待、閱讀反思和批判等環節,拓展思維空間,提高閱讀質量。”[3]課程標準要求教師培養學生學會創造性閱讀文本,那么教師在解讀文本時自然也要率先進行創造性解讀,正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么它是否需要考慮學生“學”的問題?王榮生教授在評議郭初陽老師上的《愚公移山》一課時說:“在這堂課中,老師按自己的解讀思路闡釋文本的意圖非常明顯,但似乎在學生身上沒有顯效;老師在這節課設計最巧、用力最猛的地方,即由一系列的‘假如牽引的討論,也許對學生的閱讀行為并不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他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質疑:“這堂課是教《愚公移山》這篇課文呢,還是教《愚公移山》的一種‘另類的解讀方法?換句話說,學生是‘學老師對這篇課文的解讀結論呢,還是學習一種‘另類的解讀方法并據此由自身出發去探詢文本或者‘引發思考和討論呢?”[4]王榮生教授說,語文教師教的是語文課程,學生是學語文課程里的“語文”,所以語文教師教學的內容必須“有道理”,并且足以達成語文課程與教學目標。看來,個性解讀也需量“力”而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接近一堂語文“好課”的最高境界。
二、正確把握學生的真實情況
學生的實際掌握能力,我認為便是我們平時所說“學情”的一部分,上海師范大學的陳隆升博士認為“學情”主要包括“學生在從事課堂學習時的學習起點、學習狀態及學習結果等三大要素”[5],而學生的實際掌握能力即是“學習起點”,它是學生在進行語文課堂學習時的基礎、需要與準備,是課堂教學的起點。如何尋找學生的起點?教師不能再憑主觀的分析或解釋去代替學生真實的情況,因為如今的學生獲取知識信息的渠道很多,他們的學習狀態可能遠遠超出教師的想象,必須采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認定。
首先,教師必須了解所教對象的個體經驗。學生在進入課堂前,已經有著豐富的生活和學習的生命體驗。因此,教師不能無視學生的原有經驗。不同年齡階段的學生,他們的身心發展程度定然不同;不同地區生活的學生,他們個人的生活體驗也定然不同。教師若課前分析學生的個體經驗,把學生的已有經驗代入知識的形成過程之中,學生就可以在自己對問題理解的基礎上獲取知識,這樣的知識與學生的已有經歷和體驗結合在一起的,成為和他們關系最為密切的知識,因而也最富于真實的意義。如教授梁衡的《夏》第四段時,在引導學生體會“快割,快割”“快打,快打”兩個短句的妙處之前,我先詢問班級中那些來自農村的孩子:你的父母在夏天農忙季節要做哪些事情?學生自然是如數家珍。此時我再順水推舟結合文本中的內容,引導學生體會夏天“人們的每一根神經都被繃緊”的含義,如此,就能體會到上述兩個短句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夏天“緊張、急促”旋律的特點。
其次,教師可以通過檢查預習作業,初步了解學生對本節課內容的理解情況,避免每節課都從“零”開始授課的重復費時現象。比如,在教授文言文之時,教師可以將文字的翻譯任務交給學生,遇到難以理解的字詞,再在課堂上直接提出疑問,師生共同解決。這樣既能使教師清晰地了解學生的實際掌握情況,同時又能節省學生的學習時間,進而提高他們的學習效率。
最后,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發問,分析學生對本課所授內容的掌握情況,及時調控教學程序。比如,在前一堂“較有深度”的課中,老師一開始就問學生:看到這個標題時,你們有沒有什么疑問?學生們各抒己見。但是,老師在后面的教學環節中只是更多地關注對作品主題和思想情感的分析解讀,更多地引導學生學習作者細致的觀察和生動的描寫,而對前面學生提出的幾個問題只有極少數的回應。也就是說,老師的設疑環節僅僅起到了“擺設”的作用。學生的困惑、疑難無法得到滿足,老師不去關注他們的“期待”,勢必就會造成“教學過度”,浪費的不僅是學生的時間,還將是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學習興趣。在很多時候,“我們的教學設計與學生的閱讀‘期待視野有較大的差距,對學生閱讀能力的提高作用可能也是比較有限的”[6]。
因此,無論教師依據課程標準、文本的語文教育價值、教材編者的意圖確定什么教學內容,都必須依據學情作必要的篩選,把那些學生“讀不懂”“讀不好”但通過努力能夠讀懂讀好的內容作為“教的內容”,在課堂上著力解決它,絕不能以個人對文本的解讀完全代替學生的理解。因為只有學生真正有所“得”的課堂,才是理想的課堂[7]。
參考文獻:
[1]張春興.教育心理學[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116.
[2]張大均.教育心理學[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95.
[3]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S].2001,(9).
[4]王榮生.語文課課程論基礎[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86.
[5]陳隆升.語文課堂教學研究——基于“學情分析”的視角[D].上海師范大學,2009.
[6]黃本榮.“教的內容”等于“學的內容”嗎[J].中學語文教與學,2011,(3).
[7]王家倫.學生“所得”是語文課堂評價的終極目標[J].中學語文教學,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