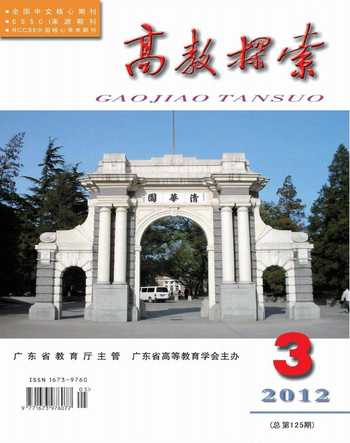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的倫理審視
摘 要:從政策倫理上講,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應(yīng)以倫理上的正當(dāng)性與合理性而存在。然而,從制定來(lái)看,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是利益相關(guān)者“不在場(chǎng)”下的產(chǎn)物;從執(zhí)行來(lái)看,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處于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公地困境”;從評(píng)估來(lái)看,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處于效益“隱退”狀態(tài)。從這個(gè)意義上講,獨(dú)立學(xué)院辦學(xué)模式是中國(guó)高等教育轉(zhuǎn)型過(guò)程“政策失范”的產(chǎn)物。
關(guān)鍵詞: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倫理;利益相關(guān)者;公地困境;政策績(jī)效
從政策倫理來(lái)看,任何教育政策都應(yīng)以倫理道德上的正當(dāng)性和合理性而存在,都蘊(yùn)涵著一定的道德觀念和價(jià)值選擇。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自它誕生之日起,關(guān)于它的爭(zhēng)議就沒(méi)有停止過(guò)。特別是2010年浙江大學(xué)城市學(xué)院“賣(mài)地”與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浙江學(xué)院“停辦”等事件,重新喚起人們對(duì)這種辦學(xué)模式的質(zhì)疑。那么,作為一種政策安排,倫理視野下的獨(dú)立學(xué)院辦學(xué)模式到底是“政策創(chuàng)新”還是“政策失范”呢?
一、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制定:利益相關(guān)者的“不在場(chǎng)”
“政策的形成過(guò)程,實(shí)際上就是各種利益群體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輸入到政策系統(tǒng)中,由政策主體依據(jù)自身利益的需求,對(duì)復(fù)雜的利益關(guān)系進(jìn)行調(diào)整的過(guò)程。”[1]從這個(gè)意義上講,教育政策的決策過(guò)程是決策者與利益相關(guān)者之間或者利益相關(guān)者之間經(jīng)過(guò)N次重復(fù)博弈所達(dá)至“重疊共識(shí)”的契約過(guò)程。因此,無(wú)論在教育理念或教育決策上,應(yīng)該為各種意見(jiàn)的表達(dá)提供渠道和平臺(tái)。“政策是各種影響力和議程重新‘裝配的產(chǎn)物。在政府內(nèi)部,在政策制訂過(guò)程中充滿了臨時(shí)性、偶然性和討價(jià)還價(jià)。”[2]然而,由于壟斷和缺乏監(jiān)督,轉(zhuǎn)型期體制改革的重要特點(diǎn)被稱為“內(nèi)部人”改革,政策決策領(lǐng)域內(nèi)部形成了封閉性的政策主體網(wǎng)絡(luò)。政策決策不是各利益相關(guān)者博弈和公共選擇的產(chǎn)物,更多遵循“精英+權(quán)力”相結(jié)合的決策邏輯。
“內(nèi)輸入是當(dāng)代中國(guó)決策過(guò)程中利益表達(dá)與綜合的主導(dǎo)形式。亦即當(dāng)代中國(guó)‘人民的利益是由權(quán)力精英‘為民做主的;它所依靠的不是多元決策下的社會(huì)互動(dòng)過(guò)程,而是權(quán)力精英的政治折沖。”[3]從《關(guān)于規(guī)范并加強(qiáng)普通高校以新的機(jī)制和模式試辦獨(dú)立學(xué)院管理的若干意見(jiàn)》(以下簡(jiǎn)稱《若干意見(jiàn)》)到《獨(dú)立學(xué)院設(shè)置與管理辦法》(以下簡(jiǎn)稱《辦法》),這兩項(xiàng)政策的決策過(guò)程鮮明體現(xiàn)了權(quán)力精英“為民做主”的特點(diǎn)。這種“以國(guó)家與行政機(jī)關(guān)的政治精英的話語(yǔ)為中心、單向度政府選擇的精英主義模式”的決策邏輯[4],在一定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母體大學(xué)、投資主體與學(xué)生等利益的博弈均衡。但受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影響的其它利益相關(guān)者則處于“不在場(chǎng)”的境遇,比如“純”民辦高校、公辦高校的學(xué)生及家長(zhǎng)、用人單位等往往被排斥在決策體制之外。這種“畸變”的決策權(quán)力機(jī)制為權(quán)力擁有者進(jìn)行“政策創(chuàng)租”和“抽租”提供了便利條件,導(dǎo)致“政策尋租”的出現(xiàn)。中央政府通過(guò)頒發(fā)《若干意見(jiàn)》與《辦法》優(yōu)先授予獨(dú)立學(xué)院稀缺的政策資源,限制其他院校的進(jìn)入與競(jìng)爭(zhēng),獲得壟斷利潤(rùn)。正如有學(xué)者所言:“獨(dú)立學(xué)院制度正是通過(guò)對(duì)獨(dú)立學(xué)院某種教育特權(quán)的制度性授予,變相地造成了對(duì)民辦高校市場(chǎng)進(jìn)入的限制,回避了應(yīng)有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從而確保了獨(dú)立學(xué)院的壟斷性利潤(rùn)。”[5]
這種“政策尋租”產(chǎn)生的獨(dú)立學(xué)院辦學(xué)模式既兼有公辦的優(yōu)勢(shì),又能靈活運(yùn)用民辦的機(jī)制優(yōu)勢(shì),且在開(kāi)辦之初就是本科起點(diǎn),對(duì)學(xué)生更具吸引力,從而可能“擠占”純民辦高校的生源,打擊社會(huì)力量舉辦“純”民辦高校的積極性。如獨(dú)立學(xué)院可以在較低的標(biāo)準(zhǔn)下直接舉辦本科教育,傳統(tǒng)的普通民辦高校則受到政策歧視,被限制升為本科院校。正如西安翻譯學(xué)院院長(zhǎng)丁祖詒所言:“擁有200多萬(wàn)‘民學(xué)大軍的中國(guó)1300多所民辦高校,正整體遭遇由某些公辦大學(xué)‘校中校暗渡陳倉(cāng)的‘獨(dú)立本科以假亂真的空前尷尬。”[6]
這種決策主體的單一性,容易造成其他政策主體的利益需求與價(jià)值期望得不到充分的表達(dá),使這些利益相關(guān)者在政策活動(dòng)中處于“失語(yǔ)”狀態(tài),導(dǎo)致公辦高校“一枝獨(dú)秀”情況的產(chǎn)生。有學(xué)者認(rèn)為:“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有違政府應(yīng)當(dāng)營(yíng)造公平市場(chǎng)秩序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有違民辦學(xué)校與公辦學(xué)校享有平等法律地位的法律精神,片面維護(hù)公辦學(xué)校的利益,傾斜性地為公辦學(xué)校爭(zhēng)利,打壓民辦學(xué)校的辦學(xué)空間和利益。其可以預(yù)見(jiàn)的后果,迫使民辦高校在不公平競(jìng)爭(zhēng)中‘破產(chǎn),或者成為公立高校‘輸血的獨(dú)立學(xué)院,從而使獨(dú)立學(xué)院獨(dú)大,成為民辦高等教育的主體,形成‘公立學(xué)校通吃的格局。”[7]
二、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執(zhí)行:多重制度邏輯下的“公地困境”
教育政策執(zhí)行“是一個(gè)充滿著連續(xù)不斷的交易、談判和政治互動(dòng)的復(fù)雜過(guò)程”[8]。在此過(guò)程中,不同的利益相關(guān)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獨(dú)立學(xué)院)處于不同的“制度場(chǎng)域”,往往會(huì)采用不同的態(tài)度與方式對(duì)特定的政策加以“闡釋”和“踐行”,導(dǎo)致政策執(zhí)行的“公地困境”。
由于政策部門(mén)(中央教育行政部門(mén))的“亂象之憂”,中國(guó)的教育改革一般采取“漸進(jìn)式”而不是“激進(jìn)式”的改革邏輯。政策部門(mén)一般采用“政策試點(diǎn)的積極妥協(xié)原則”進(jìn)行教育改革,避免發(fā)生大的動(dòng)蕩。為此,教育部于2003年頒發(fā)《若干意見(jiàn)》規(guī)定“試辦獨(dú)立學(xué)院要貫徹‘積極支持、規(guī)范管理的原則”、“今后各地、各部門(mén)和各高等學(xué)校,都要繼續(xù)有步驟、有計(jì)劃地推進(jìn)獨(dú)立學(xué)院的試辦工作……注意并堅(jiān)決反對(duì)一哄而起和‘刮風(fēng)現(xiàn)象,確保獨(dú)立學(xué)院穩(wěn)妥、健康地發(fā)展”。然而,由于受到對(duì)民辦教育不信任、不承認(rèn)等意識(shí)形態(tài)與“潛規(guī)則”的隱性制約,再加上國(guó)家政府各部門(mén)的多重目標(biāo)與利益的沖突,導(dǎo)致國(guó)家政策滯后于實(shí)踐的發(fā)展,從而產(chǎn)生“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之間的“落差”。這種“落差”意味著中央政府在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供給中存在多重不一致、甚至相互沖突的目標(biāo)。在政策執(zhí)行過(guò)程中,“當(dāng)政策目標(biāo)出現(xiàn)膠著或沖突時(shí),政府會(huì)出現(xiàn)所謂的‘遲疑或‘不決的現(xiàn)象”[9]。在此情況下,政府會(huì)容忍政策執(zhí)行失范的現(xiàn)象,不進(jìn)行嚴(yán)厲的處罰。如《若干意見(jiàn)》第二條規(guī)定,“不允許以各種變相形式把高職(大專)學(xué)校改為獨(dú)立學(xué)院”,但事實(shí)是在《若干意見(jiàn)》頒布之后已經(jīng)這樣做的學(xué)校只能追認(rèn),甚至將公立中專學(xué)校改為獨(dú)立學(xué)院的也照樣追認(rèn)。很多不符合規(guī)定也得到教育部的“事后追認(rèn)”,如以申辦高校的校辦企業(yè)或者國(guó)有控股企業(yè)作為出資者的同樣得到追認(rèn),甚至以地方政府財(cái)政性資金投入的也不得不追認(rèn)。
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中制度環(huán)境的改變,使地方政府演變成為擁有特殊利益結(jié)構(gòu)和效用偏好的行為主體。為了地方的利益,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門(mén))傾向于那些能給本地區(qū)帶來(lái)最大利益的政策,在執(zhí)行中央政府政策時(shí)采取諸如“靈活變通”、“打擦邊球”等不規(guī)范的做法來(lái)規(guī)避現(xiàn)有體制和政策。由于各地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教育發(fā)展不平衡,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掌握獨(dú)立學(xué)院實(shí)踐運(yùn)行的信息,或者要為掌握這些信息付出極其高昂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教育行政部門(mén)制定的政策必然是基本政策,只是對(duì)一些主要問(wèn)題進(jìn)行“模糊性”規(guī)定,“宜粗不宜細(xì)”、“要留有充分的余地”。然而,這種“模糊性”的政策文本(如“原則上”、“基本上”、“視情況”、“情節(jié)嚴(yán)重”等詞語(yǔ))卻給地方政府執(zhí)行政策留下了靈活性的彈性空間。如《若干意見(jiàn)》第六條規(guī)定,“獨(dú)立學(xué)院原則上應(yīng)在申請(qǐng)者所在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范圍內(nèi)試辦”。第七條規(guī)定,“獨(dú)立學(xué)院正式招生時(shí)生均各項(xiàng)辦學(xué)條件應(yīng)基本符合國(guó)家規(guī)定標(biāo)準(zhǔn)”。“這種不完善之處就為制度不能充分實(shí)施提供了可能。因?yàn)橹贫鹊膶?shí)施過(guò)程實(shí)際上是一種博弈和互動(dòng)過(guò)程,博弈者都努力尋求對(duì)自己最有力的行動(dòng)方案,制度漏洞就成為雙方搜尋的目標(biāo)和對(duì)象。只要找到了制度漏洞,就可以繞過(guò)已有的規(guī)定,甚至使現(xiàn)行制度成為無(wú)效和無(wú)用的東西。”[10]正是由于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的“模糊性”給予地方政府為了自己利益而重新解讀政策的機(jī)會(huì)空間,導(dǎo)致政策意圖(“獨(dú)”、“民”、“優(yōu)”)的“異化”。
作為一種試辦的政策傾向,一些獨(dú)立學(xué)院擔(dān)心未來(lái)政策的變化或倒退。因此,在辦學(xué)過(guò)程中,往往采用“搭便車”的機(jī)會(huì)主義,抓住有利的政策空間大力提取政策資源(“民”原則),進(jìn)行規(guī)模擴(kuò)張,而對(duì)“獨(dú)”、“優(yōu)”原則則找各種借口與困難進(jìn)行推托,來(lái)獲得這種“時(shí)間差”。“中國(guó)制度運(yùn)作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是通過(guò)中央和各級(jí)政府下達(dá)文件來(lái)推動(dòng)。這些文件有時(shí)只規(guī)定目標(biāo)和‘精神,而不規(guī)定手段;即使規(guī)定了手段也往往是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該做什么,而對(duì)不能做的邊界常常只有少數(shù)規(guī)定。這樣就使制度安排在‘應(yīng)該如何和‘不能如何之間出現(xiàn)了許多空白點(diǎn)。”[11]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獨(dú)立學(xué)院就會(huì)采取“偷天換日”、“瞞天過(guò)海”等各種方法來(lái)達(dá)到目標(biāo)。這符合鮑爾(Ball)的看法:“政策通常不告訴你要做什么,它創(chuàng)設(shè)某種環(huán)境,縮小或改變你能做什么的決策范圍,或者僅是提出了特定的目標(biāo)和結(jié)果。”[12]因此,對(duì)獨(dú)立學(xué)院而言,即便中央政府為獨(dú)立學(xué)院的辦學(xué)設(shè)置了一定的要求,但仍留下充余的彈性行動(dòng)空間。
三、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評(píng)估:績(jī)效的“隱退”
政策績(jī)效主要通過(guò)政策評(píng)估予以考察。“政策評(píng)估就是了解公共政策所產(chǎn)生的效果的過(guò)程,就是試圖判斷這些效果是否是所預(yù)期的效果的過(guò)程,就是判斷這些效果與政策的成本是否符合的過(guò)程。”[13]即主要考察某項(xiàng)政策的有效性。從價(jià)值的角度來(lái)看,政策的效益就是政策目標(biāo)完整、真實(shí)地轉(zhuǎn)化為政策結(jié)果的過(guò)程。政策的成功或政策的失敗實(shí)際上就取決于政策過(guò)程是否有效地實(shí)現(xiàn)了政策目標(biāo)到政策結(jié)果的轉(zhuǎn)化,也就是取決于政策過(guò)程中獲得價(jià)值選擇和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選擇的政策行為過(guò)程的有效性。[14]從政府視角看,獨(dú)立學(xué)院辦學(xué)模式按培養(yǎng)成本全額收費(fèi),極大地緩解了政府的財(cái)政困境,提高了母體大學(xué)辦學(xué)積極性,滿足了人民群眾享受優(yōu)質(zhì)高等教育的需求。例如,到2008年,浙江省的22所獨(dú)立學(xué)院在校學(xué)生169182名,其中在校本科生165065人,占全省466909名本科在校生的35.4%。[15]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zhǎng)褚子育2008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shí)指出:“浙江省的獨(dú)立學(xué)院已成為全省高等教育事業(yè)發(fā)展新的增長(zhǎng)點(diǎn),為實(shí)施‘創(chuàng)業(yè)富民,創(chuàng)新強(qiáng)省總戰(zhàn)略培養(yǎng)高級(jí)專門(mén)人才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獨(dú)立學(xué)院已被浙江省社會(huì)各界、學(xué)生家長(zhǎng)所廣泛接受,呈現(xiàn)出‘招生、就業(yè)兩旺的良性發(fā)展態(tài)勢(shì)。”[16]
然而,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目標(biāo)(“獨(dú)”、“民”、“優(yōu)”)并沒(méi)有完全實(shí)現(xiàn),獨(dú)立學(xué)院政策實(shí)踐過(guò)程存在“不規(guī)范”辦學(xué)行為。除獨(dú)立發(fā)放文憑之外,其余“四個(gè)獨(dú)立”通過(guò)“政策變通”的方式僅僅從形式上達(dá)到教育部的政策要求。招生不獨(dú)立、沒(méi)有獨(dú)立的財(cái)務(wù)核算、不具有獨(dú)立的法人資格與法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如由各種舉辦者(包括社會(huì)投資者和公辦高校等)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chǎn),迄今仍沒(méi)有轉(zhuǎn)到獨(dú)立學(xué)院名下的有189所,超過(guò)現(xiàn)有獨(dú)立學(xué)院總數(shù)的60%。[17]
“‘民就是民辦機(jī)制,必須按照民辦機(jī)制運(yùn)行,不準(zhǔn)走民不民、公不公的路子。教育部黨組對(duì)這一條的態(tài)度十分明確。不管是省級(jí)教育行政部門(mén)還是申辦高校,都不要試圖走混合型的路子。”[18]然而,教育品牌與民間資本“不結(jié)合”或“假結(jié)合”大量存在。到2010年底,某省22所獨(dú)立學(xué)院中,只有4所合作方是民間資金介入,由母體高校自辦或與政府合辦的為18所,達(dá)81.8%。又如某省12所獨(dú)立學(xué)院中只有一所引入了民間資本,其余11所都是公立大學(xué)辦的“校中校”或“校外校”,大約占92%。[19]辦學(xué)資金來(lái)自母體大學(xué)教育發(fā)展基金會(huì)或XX高教園區(qū)建設(shè)發(fā)展有限公司,都是國(guó)有資金投入,甚至有的獨(dú)立學(xué)院根本就沒(méi)有所謂的投入,辦學(xué)資金是以母體大學(xué)的名義向銀行貸款來(lái)獲得啟動(dòng)資金,是一種變通執(zhí)行“民辦機(jī)制”的表現(xiàn)。作為舉辦方之一,很多的母體大學(xué)根本沒(méi)有博士學(xué)位授予權(quán),母體大學(xué)僅把舉辦獨(dú)立學(xué)院作為一種“斂財(cái)”的工具和途徑,排斥優(yōu)質(zhì)民間資本進(jìn)入獨(dú)立學(xué)院市場(chǎng),沒(méi)有專注于教育質(zhì)量的提高,導(dǎo)致政策目標(biāo)“優(yōu)”沒(méi)有實(shí)現(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陳慶云主編.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7.
[2][英]斯蒂芬·鮑爾.教育改革——批判和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視角[M].侯定凱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31.
[3]胡偉.政府過(guò)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83-284.
[4]張鐵明.中國(guó)高教大眾化進(jìn)程中制度兩難之抉擇[J].當(dāng)代教育論壇,2005(19).(下轉(zhuǎn)第85頁(yè))
[5]王建華.我國(guó)獨(dú)立學(xué)院制度:?jiǎn)栴}與轉(zhuǎn)型[J].教育研究,2007(7).
[6]彭華安.新制度主義社會(huì)學(xué)視角中的獨(dú)立學(xué)院制度構(gòu)建[J].當(dāng)代教育科學(xué),2010(21).
[7]楊東平.制約民辦教育發(fā)展的觀念障礙[J].民辦教育研究,2005(1).
[8][英]米切爾·黑堯著.現(xiàn)代國(guó)家的政策過(guò)程.趙成根譯.北京:中國(guó)青年出版社,2004.129.
[9]趙德余.政策制定的邏輯:經(jīng)驗(yàn)與解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8-39.
[10]張曙光.制度·主體·行為——傳統(tǒng)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反思[M].北京:中國(guó)財(cái)政經(jīng)濟(jì)出版社,1999.139.
[11]孫立平.實(shí)踐社會(huì)學(xué)與市場(chǎng)轉(zhuǎn)型過(guò)程分析[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2(5).
[12]董輝,盧乃桂.從“指令”到“行動(dòng)”:擇校治理政策的實(shí)施[J].教育發(fā)展研究,2010(22).
[13][美]托馬斯·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鞠方安等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201.
[14]劉復(fù)興.教育政策的價(jià)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3.48.
[15]周光迅,周國(guó)平.從獨(dú)立學(xué)院辦學(xué)實(shí)踐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浙江經(jīng)驗(yàn)”[J].高等教育研究,2009(11).
[16]朱振岳.加強(qiáng)規(guī)范 注重提高質(zhì)量——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zhǎng)褚子育談促進(jìn)獨(dú)立學(xué)院健康發(fā)展[N].中國(guó)教育報(bào),2008-04-25.
[17]馮向東.獨(dú)立學(xué)院新一輪發(fā)展的制度支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0).
[18]張保慶.統(tǒng)一思想 提高認(rèn)識(shí) 注重質(zhì)量 嚴(yán)格管理 努力促進(jìn)獨(dú)立學(xué)院健康、持續(xù)發(fā)展[J].中國(guó)大學(xué)教學(xué),2005(5).
[19]彭華安.析獨(dú)立學(xué)院制度合法性危機(jī)[J].國(guó)家教育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10).
(責(zé)任編輯 劉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