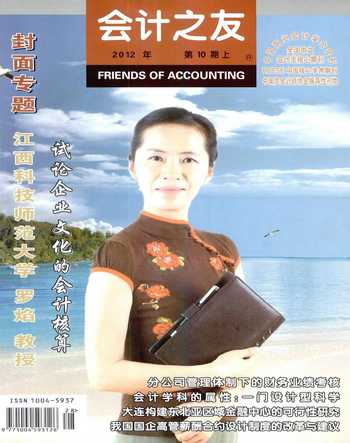資產負債表債務法下會稅差異研究
盧美玲 區永健
【摘要】 資產負債表債務法下,暫時性差異產生會計和稅收差異,企業往往通過這種差異進行盈余管理,進而進行避稅。通過以滬深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從會計收益與應稅收益差異的視角,實證分析企業會計—稅收差異與所得稅實際稅負、資產規模、總資產報酬率之間的關系對研究企業盈余管理具有重要意義。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稅收差異與所得稅實際稅負、資產規模存在著顯著負相關關系,與總資產報酬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關鍵詞】 會計—稅收差異; 企業所得稅避稅; 所得稅稅負
一、引言
財務報告依據企業會計準則編制,而納稅申報則依據稅收法規。會計準則與稅法在目的、基本前提和遵守的原則等方面都存在著差別。因而,財務報告披露的會計利潤與納稅申報的應稅所得之間必然存在著差異(以下簡稱為會計—稅收差異)。新企業會計準則規定計算企業所得稅時采用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新方法下企業的避稅行為是否也通過對會稅差異來實現,即在不影響稅前會計收益的前提下減少應稅收益,提高了會計收益的水平,致使會計—稅收差異被擴大,相應的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也被拉大。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分析上市公司會稅差異來了解上市公司企業所得稅避稅問題。
二、文獻回顧
國內外學者關于會計—稅收差異與企業所得稅避稅行為相關文獻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認為會計收益與應稅收益差異是企業所得稅避稅的主要原因之一。Manzon & plesko(2001) 、Mihir A. Desai(2002)、Desai(2003)發現美國會計收益與應稅收益之間的差異大小由于避稅行為而呈現顯著上升的趨勢。二是上市公司通過擴大會計—稅收差異的方式操縱利潤,很好的進行了企業所得稅的避稅,使盈余管理的稅負成本最小化。如Mi11s & Newberry(2001)、張林(2007)、孫崢嶸(2008)、曾富全,呂敏(2010)都證實了這一觀點。三是葉康濤(2006)、宛成鋼(2009)、曾富全、呂敏(2010)發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差異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過操縱非應稅項目損益,以規避盈余管理的稅負成本。但也有證據表明企業為隱瞞財務困境而虛增利潤卻不惜稅費支出,Erickson,Hanlon & Maydew(2004)以美國證監會在1996至2002年期間認定財務欺詐和虛增利潤的27家公司為分析樣本研究表明,公司每虛增1美元利潤,平均要為此支付12美分的所得稅成本,這表明上市公司愿意為盈余管理行為支付高額所得稅成本。新會計準則頒布后,企業所得稅稅率由33%下調為25%,同時所得稅的核算由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二選一改成資產負債表債務法。因此其研究結論是否具有持續性,還要待進行實證。
本文以2007年《企業會計制度》的實施及2007年以后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加強協作的背景為切入點,通過使用資產負債表債務法估計會計—稅收差異,為研究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源提供重要的經驗證據,相信對加強會計準則與稅收法規的協作具有積極意義。
三、研究設計
按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會稅法執行標準的不同會導致執行結果產生差異,這差異分為永久性差異和暫時性差異。其中,永久性差異是從收入和費用的發生額中計算出來的,在當年的納稅調整中解決,不涉及或者不存在會計處理問題,需要進行會計處理的是暫時性差異(即賬面價值與計稅基礎不一致)。本文研究的起點是會計—稅收差異。
(一)相關變量設計
1.會計—稅收差異的計算
會計—稅收差異=利潤總額—應納稅所得;應納稅所得(應稅收益)=本期所得稅費用/實際稅率
2.所得稅稅負
企業實際所得稅負是指企業在一定時期內實際繳納的所得稅稅款占其會計利潤的比率。一般用所得稅實際負擔率來反映企業的稅負水平,可以直觀地反映出各種稅收優惠對企業所得稅負擔的影響,它反映了上市公司的所得稅避稅程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3.規模的測算
本文的規模采用的是期末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其計算公式如下:
Scale=LN(期末資產總額)
4.總資產報酬率的測算
(二)研究假設
會計收益數據要比應稅收益數據更易人為操縱,在應稅收益因稅法剛性難以被人為操縱的情況下,則可以合理推測是會計收益被操縱的程度越大,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也越大(實際稅負越低)。因此,可以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
假設1:會計—稅收差異與實際稅負負相關,即實際稅負越低,會計—稅收差異越大。
已有研究表明,規模大的公司更容易受到證券市場的監管,操縱會計盈余的成本更高,因此規模與會計—稅收差異可能負相關。因此,可有假設2:
假設2:會稅差異與公司規模負相關,即公司的規模越大,會稅差異越小。
竇魁(2007)研究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強,實際所得稅率越低。因此,可以提出本文第3個假設:
假設3:會稅差異與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正向關系,即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強,會稅差異越大,則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就越大。
(三)模型設計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模型如下:
BTD=β0+β1ETR+β2Scale+β3ROA+ε
其中BTD(Book—Tax Differences)為因變量,表示會計—稅收差異即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ETR(Effective Income Tax Burden Rate)為自變量,表示實際稅負;Scale為自變量,表示規模;ROA為自變量,表示總資產報酬率;ε為殘差。
(四)數據采集與樣本選擇
本文以滬深證券交易所全部A股上市為研究對象,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數據(CSMAR)。由于2007和2008年先后實施的新會計準則和新企業所得稅法后,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25%,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一致;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等。為了保持數據可比性,本文將選取新會計準則實施后,我國滬深A股非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的合并報表數據為研究樣本,并進行了如下數據的剔除:未披露所得稅率或所得稅費用的公司;所得稅費用≤0的公司;當期應交所得稅費用數據未披露或缺失;當期應交所得稅費用≤0;所得稅稅負≥100%的公司;當年虧損的公司。因為虧損公司的虧損額可以在以后年度結轉,抵減以后年度的所得稅費用,從而不便于準確計算以后年度的會計—稅收差異。經過上述剔除,最后得到的2008年至2010年樣本公司數量共計3 669個樣本。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由表1得知,各數據呈服從正態分布,會稅差異(BTD)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非常大,意味著會稅差異可操作的空間很大。所得稅實際稅負率(ETR)、規模(Scale)、資產回報率(ROA)都為正值,說明數據沒有統計上的差錯。
(二)實證結果分析
大多數情況下橫截面數據存在異方差,如果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檢驗,有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首先,檢查方程是否存在異方差,這里采用懷特檢驗法。表2表明,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懷特檢驗拒絕同方差的假設,即存在異方差。
為解決異方差問題,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3。
結果顯示,會稅差異與所得稅稅負率、規模為負相關關系,與總資產報酬率正相關。即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就越大(實際稅負越低),會計—稅收差異越大;資產規模越小,會稅差異越大;總資產報酬率越大,會計稅收差異就越大,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就越大,支持全部研究假設。
(三)模型擬合度
表4顯示模型調整后的R2=0.839654,Durbin—Watson stat=1.988361,表示模型的擬合程度很好,自變量能夠很好的解釋因變量,因而可判斷得出的結論具有可靠性。
(四)穩健性檢驗
方程中引入其他變量進行檢驗,不影響上述檢驗結果;分年度進行獨立樣本檢驗,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的檢驗,結果沒有實質性差異,因此,結論具有穩健性。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會計—稅收差異為研究起點,發現會計—稅收差異越大,所得稅避稅程度就越大,表現為所得稅實際稅負率就越低;上市公司規模越大,會稅差異越小,避稅程度越小;上市公司的企業所得稅避稅程度與總資產報酬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強,會稅差異越大,所得稅避稅程度就越大。
上述研究結論都說明了我國上市公司可能通過所得稅進行避稅籌劃,通過擴大會計—稅收差異方式來進行所得稅避稅,降低企業相應的實際所得稅稅負率。由于上市公司可能會通過調節不影響應稅收益而影響會計收益的盈余管理手段來進行避稅籌劃,在不增加所得稅稅負的情況下,提高會計盈余水平,因此,國家財稅部門應加強會計制度與稅法之間的協調,完善各項會計準則及稅法制度,使利用會計—稅收差異操縱的空間縮小,從而壓縮企業避稅的空間。
【參考文獻】
[1] Gil B. Manzon,Jr. and George A. Plesko.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and Tax Reporting Measures of income[J].Working Paper 4332—01,2001(5).
[2] Mihir A. Desai. The Corporate Profit Base,Tax Sheltering Activity,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Employee Compensation[J].NBER Working Paper,No.8866,2002(4).
[3] Mihir A. Desai.The Divergence between Book and Tax Income[J].Tax Policy and Economy,2003(17):169—206.
[4] Lillian F.Mills,Kaye J.Newberry. The influence of tax and non—tax costs on book—tax reporting differences:public and private firm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2001,23(1):1—19.
[5] 張林.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6] 孫崢嶸.會計—稅收差異、盈余管理及市場反應[D].西南財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7] 曾富全,呂敏.會計—稅收差異與企業所得稅避稅——來自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初步證據[J].會計之友,2010(8):71—74.
[8] 葉康濤.盈余管理與所得稅支付:基于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之間差異的研究[J].中國會計評論,2006,4(2):205—224.
[9] 宛成鋼.盈余管理與上市公司所得稅稅負關系的實證研究[D].重慶大學,2009.
[10] Merle Erickson,Michelle Hanlon and Edward L.Maydew. How much will firms pay for earnings that do not exist Evidence of taxes paid on allegedly fraudulent earnings,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79(2):387—408.
[11] 竇魁.上市公司所得稅負擔的實證研究[D].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