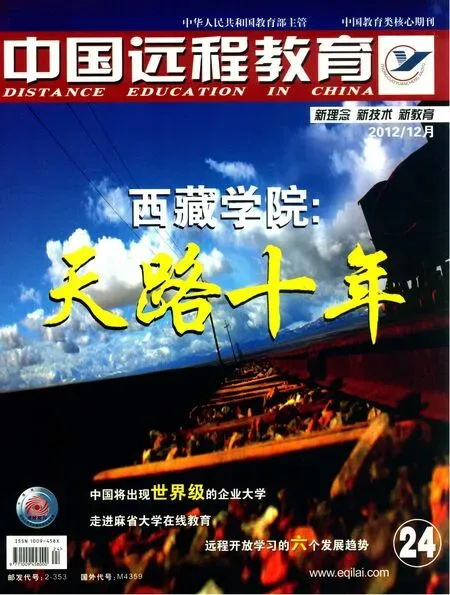混合式校本研修中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校本研修團隊的差異分析
□ 喬 霞 趙曉亮
一、問題引入
當前我國教育發展和改革進入了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歷史新時期。教師是教育改革發展的第一資源。《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要“將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作為教育發展改革的重要保障措施,將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作為國家教育發展的戰略性任務”[1]。教師培訓是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教師繼續教育和終身學習體系的重要構成。教育部從2009年就實施了“中小學骨干教師培訓計劃(國培計劃)”,把教師培訓推入到了快速發展時期[2]。
校本研修作為一種以學校為本、以教師為本、以解決問題為主要目標的研修方式[3],在中小學教師培訓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和青睞。然而,目前對校本研修中的團隊建設及如何提升校本研修團隊績效等方面的研究尚少。筆者以遠程校本研修助學者的身份參加了由首都師范大學王陸教授團隊主持的“國培計劃(2011)——高中數學骨干教師集中培訓與校本研修一體化項目”,該項目是2010年教育部師范教育司為了更好地探索教師培訓的有效模式而開展的“集中培訓與遠程校本一體化研修”的試點示范項目。研修項目首先集中培訓了100名“種子教師”,然后運用遠程方式指導“種子教師”帶動1000名周邊教師開展校本教研活動,從而拓展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范圍,提高教師培訓的效益。從項目的階段性績效評估結果來看,涌現出了一批優秀校本研修團隊。本研究聚焦于優秀校本研修團隊和其它校本研修團隊在實踐性知識和教學行為改進兩個維度的差異分析,總結出了優秀校本研修團隊的若干個特征,從而為進一步開展遠程校本研修培育出更多的優秀團隊提供了一定的實證研究基礎。
二、文獻綜述
(一)混合式校本研修的基本概念
格林漢姆(Graham)認為,混合式學習是“一種將面授教學與基于技術媒介的教學相互結合而構成的學習環境”[4]。而麥森和萊恩尼(Mason&Rennie)則認為“混合式學習是技術、場所、教學方法的多方面融合”,而不僅僅是教學組織形式的結合[5]。李克東教授等認為混合學習(Blended Learning)是人們對數字化學習(E-Learning)進行反思后,出現在教育領域尤其是教育技術領域中較為流行的一個術語,其主要思想是把面對面(Face to Face)教學和在線(Online)學習兩種學習模式有機地整合,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一種教學方式[6]。
所謂校本(School Based),包含三方面的含義:一是為了學校;二是在學校中;三是基于學校[7]。根據校本發展的理念,校本研修包含校本培訓和校本研究兩方面含義,其中校本研究是校本培訓的拓展[8]。校本研修主要是指立足于本校工作實際,根據教師自身專業發展的需要,開展自主、合作、探究性學習和鍛煉,提高教師的專業修養,促進教師專業化發展的一種新型的教師繼續教育形式[9]。從概念分析來看,校本研修首先要以教師的工作環境為基本場所;立足本校校情,以學校教育教學實踐中的實際問題為研修內容;以研修教師為主體;以提高教師的實踐性知識、促進教師教學行為改進為直接目標,并構建成專家、學校領導、研修教師共同參與的學習型組織;以最終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和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為根據目標的教師教育形式。它是一種集學習、教學和科研三位為一體的學校及教師行為;是一種基于教師教育教學實踐,來自于教師、服務于教師的專業發展活動;是一種對教育教學經驗理論提升的過程[10]。此外,校本研修需要特別關注教師的三個方面的內在需求,即要符合教師的職業特點、認知特征和滿足教師的情感需求[11]。
本文提出的混合式校本研修模式是將混合學習(Blended Learning)的相關理論和實踐應用于校本研修的一種新型研修模式,充分發揮和利用了網絡學習和傳統學習的優勢,將兩者進行有機的結合。混合式校本研修在形式上是在線研修與面對面研修的混合[12],其目的是采取豐富多樣的信息傳遞方式以適應不同的學習需求,從而最大化地提高校本研修的效果,拓展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范圍,提高教師培訓的效益,幫助教師實現其專業發展。
(二)優秀校本研修團隊的特征
斯蒂芬·羅賓斯認為,團隊是指一種為了實現某一目標而由相互協作的個體所組成的正式群體[13]。本研究中的校本研修團隊是團隊的一種形式,是指由10~15名教師組成的,立足于本校工作實際,以促進教師實踐性知識增長和教學行為改進為目的,通過專家引領、自主探究、團隊協作的方式實現教師專業化發展的一種學習型組織。
高效團隊的特征以斯蒂芬·羅賓斯的研究最為典型。他認為一支高效的團隊應具有以下八個基本特征:明確的目標、相關的技能、相互間信任、共同的諾言、良好的溝通、談判的技能、合適的領導、內部與外部的支持[14]。
IDEO公司的總經理湯姆·凱利認為優秀團隊應具備以下特點:第一,他們在總體上致力于實現最終目標;第二,他們毫不畏懼即將到來的最后期限,每個人總會有一種在最后期限前實現目標的強烈意識;第三,團隊中沒有尊卑和等級之分;第四,團隊的組成是多樣化的,并且也尊重多樣化;第五,他們在一種開放的、崇尚自由選擇的氛圍中工作,而這樣的氛圍最有利于機動性、團隊工作和集體討論[15]。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優秀校本研修團隊應具有高效團隊和優秀團隊的特征,對優秀校本研修團隊的特征總結如下:
●團隊成員擁有共同的研修目標或愿景,每個人對此都擁有熱情;
●異質化的團隊成員,分工明確、相互信任、團隊認同感高、無尊卑之分;
●自由開放的氛圍,良好的溝通技巧;
●恰當的領導;
●外部支持。
三、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分為數據收集與數據處理兩個階段。在數據收集階段,為了考查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校本研修團隊在實踐性知識和教學行為改進兩個維度方面的差異,研究者收集了整個國培遠程校本研修過程中四個省73個校本研修團隊有關實踐性知識和教學行為改進方面的數據。這些數據包括四個活動階段的校本研修團隊作業、校本研修團隊會議記錄、教學設計、教學視頻、課堂觀察記錄數據等。
(二)研究方法
在數據處理階段,作者針對“混合式校本研修中優秀校本研修團隊及其它校本研修團隊的差異分析”這一研究問題,運用了內容分析法、統計分析方法和視頻案例分析法等三種研究方法(見表1)。

表1研究方法簡介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參加“國培計劃(2011)——高中數學骨干教師集中培訓與校本研修一體化項目”的803名教師組成的73個校本研修團隊為研究對象。根據遠程校本研修過程中四個活動階段的階段性績效評估結果,將各個階段都入選的6個優秀校本研修團隊作為本研究中的優秀校本研修團隊,統一編號為1。另外的67個校本研修團隊為本研究中的其它校本研修團隊,統一編號為2。
四、數據的分析與討論
作者根據教師實踐性知識評價指標體系,對73個校本研修團隊的數據運用內容分析法、視頻案例分析法和統計分析方法進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數據分析。
(一)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研修團隊在實踐性知識維度上的差異性分析
首先根據教師實踐性知識評價指標體系對73個校本研修團隊的教育信念、自我知識、人際知識、策略性知識和反思知識共五種實踐性知識綜合分數分別進行了計算。以教育信念為例:

(公式-1中)n為內容分析所得出的編碼個數,即教師實踐性知識編碼體系對收集的教學設計、校本研修團隊作業、校本研修團隊會議記錄等文本資料分別進行的實踐性知識的編碼;P(i)為i編碼所對應的特征函數,反映了73個校本研修團隊實踐性知識的得分;4代表了校本研修活動的四個階段。
得出73個校本研修團隊實踐性知識的得分后,又利用SPSS軟件對6個校本研修團隊的實踐性知識數據與其它67個校本研修團隊的實踐性知識數據運用兩個獨立校本Mann-Whitney U方法進行了差異檢驗,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結果表明:在教育信念方面的相伴概率為0.023;自我知識方面的相伴概率為0.046;人際知識方面的相伴概率0.553;在策略知識方面的相伴概率為0.054;在反思知識方面的相伴概率為0.032。
綜上所述,6個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校本研修團隊在教育信念、自我知識與反思知識方面存在著顯著差異,而在人際知識與策略知識等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
(二)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研修團隊在教學實踐行為的改進維度上的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中將教學實踐行為的改進聚焦在課堂提問方面,筆者對73個校本研修團隊在具體經驗獲取階段、反思性觀察階段和積極實踐階段三個階段的教學錄像運用視頻案例分析法中的記號體系分析法進行了分析,得出教學實踐行為改進度。

表2基本統計結果

表3實踐性知識差異檢驗結果

(公式-2)中的m為記號體系分析的教學行為種類數;C(i)為i編碼所對應的特征函數,反映了73個校本研修團隊教學行為改進度的得分;3代表了校本研修活動的三個階段。
得出73個校本研修團隊教學實踐行為改進度的得分后,作者利用SPSS軟件對6個校本研修團隊的教學實踐行為改進數據與其它67個校本研修團隊的教學實踐行為改進數據運用兩個獨立樣本Mann-Whitney U方法進行差異檢驗,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基本統計結果

表5教學實踐行為改進差異檢驗
在教學實踐行為改進方面,相伴概率為0.264,大于顯著性水平。所以不應該拒絕零假設,認為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校本研修團隊在教學實踐行為改進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
五、研究結論
(一)優秀校本研修團隊的特點
1.教育信念是優秀校本研修團隊建設的核心
上述數據分析顯示出: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校本研修團隊相比,在團隊教育信念知識這一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陳向明教授認為,教師的教育信念具體表現為教師對教育目的,學生所應接受的教育,“好”的教育以及如何實施和評價“好”的教育,教師職業等問題的認識和理解[17]。教師的教育信念是教師堅守教育事業并不斷為之奮斗的根本動力,在教師的實踐性知識中占有最中心的地位[18],對教師專業發展起統帥、引領和定位的作用。教師專業發展之路上如果缺乏教育信念的支撐,就如同廣袤的大地上沒有了指路標,就會使教師迷失專業發展的方向,喪失專業發展的主體性,只會成為一個以教師職業為謀生手段的教書匠,而不會從一個研究者的視角出發把教育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去奮斗。
2.自我知識是優秀校本研修團隊建設的保障
帕爾默(Palm,erRJ.)指出:“真正好的教學不能降低到技術層面,真正好的教學來自于教師的自身認同(identity)與自身完整(integrity)”[19]。上述數據分析也顯示出: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校本研修團隊相比,在自我知識這一維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教師的自我知識,包括自我概念、自我評估、自我教學效能感、對自我調節的認識等[20]。自我知識是當前的教師群體中最為缺乏的,但它又是保證教師理解其本身工作特性的關鍵因素,并且是支持教師進行更高層次反思的必要因素。自我知識是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基礎,對于教師的教學實踐和專業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教師只有實現對自我的認識,才能更好地處理自身發展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并且才能把自身的發展當作自己認識的對象和自覺實踐的對象;教師只有實現自我認識,其自身的成長與發展才能更具有計劃性和目的性;教師只有實現自我認識,才能成為自己完整意義上的發展主體,才能有自我發展的意識,才能實現自我的專業發展[21]。
3.反思是優秀校本研修團隊實現專業化發展的有效途徑
教學實踐經驗是教師實踐性知識最重要的來源。但是,當經驗受習慣和常規支配的時候,就常常成為理性和思考的相對面[22]。所以,教師必須經常對教學實踐經驗進行深入反思,用審視的目光觀察分析自己的教學實踐行為,并通過反思指導新的教學實踐。
上述數據分析顯示出:優秀校本研修團隊與其它校本研修團隊相比,在反思知識這一維度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教師的批判反思知識,主要表現在教師日常“有心”的行動中,其實是教師與自我的一種內部對話,反思有助于教師將理智的思考轉化成為教師自身的實踐性知識,反思的過程實質就是教師專業成長與專業發展的過程。所謂“反思”就是深思熟慮的思考。教師的反思是一種實踐取向的反思,表現為“對實踐反思,在實踐中反思,為實踐而反思”[23]。眾多的研究表明,教師反思是改變教師實踐的重要成分,教師反思被看作是教師協調他們的信念與實踐之間矛盾的關鍵[24][25]。
(二)培育優秀校本研修團隊的建議
校本研修團隊是實現教師專業發展的主導情境。建立一支優秀的校本研修團隊,也是學校教師專業管理的目標追求和必然選擇。首先,團隊教師應確立共同的專業發展愿景,設定相同的目標,以教師個人愿景為基礎,以學校發展愿景為導向,樹立使全體團隊成員都愿意為之奮斗的理想追求。共同愿景建立之后,團隊成員在團結、和諧、相互信任的氛圍下開展專業學習,使團隊成員的智慧力量實現最大化。同時,不能忽視教師的個體性和創造性,在協作中更好地發揮教師的個性特點,擴大教師的創造空間。此外,研修團隊還要在教學實踐中不斷使用反思工具進行強化、鞏固、改進和修正,并通過實踐、反思、再實踐的研修形式促進教師實踐性知識的持續增長,最終實現教師的專業化發展。
除了以上因素外,培養優秀的團隊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激發自身能量、創造激情、組建親密無間的團隊、合理的付出、尊重成員的個性等[26]。由于本文以教師實踐性知識為主要影響因素,所以對上述幾點不再贅述,但在培育優秀校本研修團隊時卻不容忽視。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基于實證研究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基于階段性績效評估的數據以及總結性績效評估的數據,從教師實踐性知識和教學行為改進這兩個維度,對混合式校本研修中的優秀校本研修團隊和其他校本研修團隊進行了差異分析。所以,在樣本量較少的情況下沒有結合個案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未來的研究中,建議感興趣的研究者可以更多地關注一些混合式校本研修中優秀校本研修團隊的個案,為今后開展遠程校本研修培育出更多優秀團隊提供更豐富的依據。
]
[1]劉利民.認真總結“國培計劃”實施工作經驗努力開創教師培訓工作新局面——在“國培計劃”總結交流工作會議上的講話[J].中小學教師培訓,2011,(5):3-6.
[2]金彥紅,郭紹青.基于網絡的分級分層混合式中小學教師培訓模式研究[J].中國遠程教育,2010,(11):65-68.
[3]周劍波.校本研修:源于實踐的專業發展之路[J].教學與管理,2011,32:6-7.
[4]Graham,C.R.Blended learning systems:definition,current trends,and future directions[A].edited by C.J.Bonk and C.R.Graham InHandbook ofBlended Learning:GlobalPerspectives,Local Design,San Francisco,CA:PfeifferPublishing.2006:3-21.
[5]Elizabeth Stacey,Philippa Gerbic.Success factors for blended learning[EB/OL],http://www.ascilite.org.au/conferences/melbourne08/procs/stacey.pdf[2010-12-26]
[6][12]李克東,趙建華.混合學習的原理與應用模式[J].電化教育究,2004,(7):1-2.
[7]鄭金洲.走向“校本”[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0,(6):12.
[8]王陸.大學支持下的校本研修教師專業發展模式[J].中國電化教育,2005,(3):9.
[9]周冬祥.校本研修:理論與實務[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0]王祖琴.繼承與超越:從“校本培訓”到“校本研修”[J].現代中小學教育,2006,(10):50-53.
[11]顧泠沅.校本研修應成為教師的內在需求[J].教育發展研究.
[13]Hank Williams,The Essense of Managing Groupand Team[M].1Prientice Hall Europe,1996.
[14]王美美.項目團隊及其團隊績效改進研究[D].北京化工大學,2007.
[15][23]湯姆·凱利,喬納森·利特曼.創新的藝術[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6]王陸,張敏霞,楊卉.教師在線實踐社區(TOPIC)中教師策略性知識的發展與變化[J].遠程教育雜志,2011:27-32.
[17][18][20][23]陳向明.實踐性知識:教師專業發展的知識基礎[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3,(1):104-112.
[19]丁立群.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及其現代效應[J].哲學研究,2005,(1):76-79.
[21]李佳琳.初任教師與經驗教師實踐性知識比較個案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09.
[22]約翰·杜威,姜文閡譯.我們怎樣思維[M].經驗與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68.
[24]Breyfogle,M.L..Reflective States Associated with Creating Inquiry-based MathematicalDiscourse[J].Teachersand Teaching:Theory and Practice,2005,11(2):151-167.
[25]Thompson,A.G..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ers’Concep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Teaching to Instructional Practice[J].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1984(15):10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