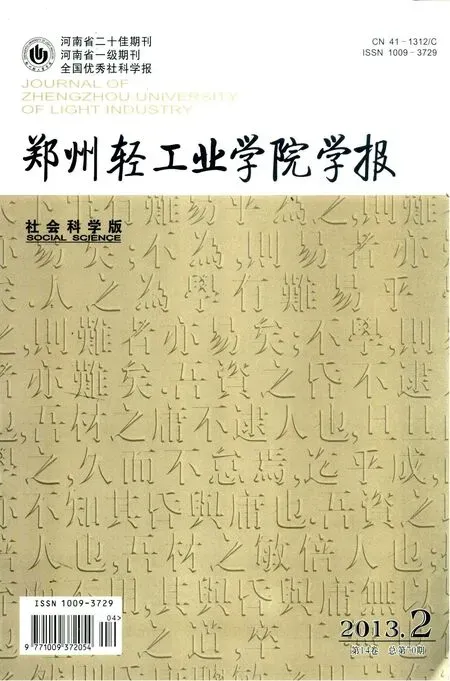現代西方語言學關于理解的本質及其把握方式研究
朱林
(上海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上海 201620)
當代西方語言學關于理解的本質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在討論中大體上形成了三種認識,即“歷史重構說”及其心理移情法、“合理應用說”及其意義預期法、“交往互惠說”及其視域融通法。分別來看,這三種把握方式都有道理,因為任何合理解釋既需要對文本結構的客觀分析和細致甄別,也需要基于主觀的意義期待對之進行再創作,更需要讀者與作者在交流中實現視域融通并達成普遍共識。但是,筆者認為只有將其內在地整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積極的文本理解。本文擬從學理上厘清當代西方語言學關于理解的本質及其把握方式三種認識,探析當代西方語言學未來發展的大致走勢,以期有利于我們借鑒西方語言學發展的積極成果來推進我國語言學的發展。
一、“歷史重構說”與心理移情法
西方語言學關于理解的第一種理論認為,理解本質上屬于一種歷史重構,其方法在于心理移情。如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威廉·狄爾泰、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等人就曾經反對在單純技術環節或者方法層面規定文本理解的本質,并提出一種文本語義的“歷史重構說”,認為凡是理解都是歷史性的理解,理解的本質就在于它的歷史性。一部作品只有深深扎根于它的緣由所出的現實生活和文化根基中,基于特定歷史背景和特定的“歷史上下文”,才能獲得真正的理解。如果作品從特定歷史語境中抽身出來并進入歷史文化的實際交往時(被不斷應用時),作者原意和文本意圖就會在很大程度上丟失,且不能很好地予以復原。由于經典文本遠離了它的原始語境和本然世界,早已變成了不可理解的陌生性的歷史傳承物和“一種不透明的光”,故而,當代語言學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盡可能客觀地重構這種原始語境和本然世界,盡可能詳盡地收集與整理關于經典文本及其原始作者的寫作過程、刊布情形以及版本源流和最初設想,以便重構出經典作品的生態原貌及其作者意圖。經典作品的內在意涵是文本產生時的那個原初世界所規定、所賦予的,對它的把握和理解,實際上就是對原始文本緣由產生的原初語境及其文化底蘊的重建或重構。離開經典作品的特定歷史視域,文本的任何意義和當代價值都變得不可理解。只有從它的內在本源處和思想發祥地出發,對經典文本所隸屬的文化原貌、生活世界進行復制與復原,即通過歷史重建和文化復歸的方式,才能揭示出經典文本的作者意圖和文本結構,才能彌補由于歷史間距和時間間距所造成的意義迷失。顯然,倡導歷史重構方法的學者也意識到,作者意圖和讀者意圖有著各自不同的視域間距,二者保持著內在的緊張關系,如果讀者從自身存在的當代視域出發,展開對文本意義的當代性理解和應用性詮釋,則讀者純粹性、主觀化的意義預期將會遮蔽經典文本中所蘊涵的作者原意和文本結構,從而導致要么詮釋不足、要么詮釋過度的非正當性理解。在對經典文本理解、解釋和應用過程中,讀者應盡可能懸置自己的主觀預期和價值判斷,努力借助于心理移情的內在體驗來實現視域轉換和歷史還原。真正的解釋既不是按照現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實現所謂“化腐朽為神奇”,更不是按照主觀預期而肆意地構造新的意義,而是要重新認識作者與他的受眾之間的原始關系,使讀者設身處地地回到文本生成時的原初氛圍中“表一番同情的理解”,準確地進入作者創制文本時的文化根基中,以便徹底消除由于歷史間距和時間間距所造成的理解障礙。
然而,吊詭的是,撇開歷史重建的復雜性與艱難性不談,即使能夠實現本然如初的意義重構,真正返回經典文本的原生語境和作者原意,對文本實現了真正的歷史理解,但這種歷史性理解真的能夠詮釋出文本的實際意義和當代價值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對于一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典文本的理解來說,重建其借以實現思想生成的各種原始條件,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就理解的一般性前提而言的。其實,真正的歷史性理解即便能夠實現原始語境的二度創造,再造出來的也不是富有靈性的意義世界,只是提供了一個想象的“僵尸”而已。因為,時間的流失、文化的交融、文明的演進、社會的變遷,注定了任何真正的歷史還原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對歷史語境的修補和恢復也都是“無意義的”和“無效的”;被歷史重建的、從陌生化轉換回來的文化生命,并非原來的真實生命與活的靈魂,贏得的只不過是某種文化的外觀,獲得的也只是“一種僵死的意義的傳達”[1];而且歷史重建只是一種外在性的抽象活動和各種文化碎片的理性雜湊與隨意陳列,并不能真正召喚活生生的文化生命的再度回歸,不能實現文本思想的再生與轉世,它給予我們的只是對當代現實性訴求的一種朦朧的回憶。更重要的問題還在于,每一個經典文本都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時空構架,都是對人們生存方式的某種特殊申認,都有它存活的特殊歷史情境和內在生命周期,其超穩定結構很自然地造就了它的獨特個性、發展形式與存在樣態。那么,讀者能夠通過心理移情真實還原作者當時所處的具體語境嗎?即便能夠成功回到作者的思想源頭,成就的也只是原始文本獨特的話語系統和表達方式,又怎樣通過愛心、同情心的內在體驗而使其獨特的精神品質和內在靈魂得以再生與轉世呢?可見,如何實現歷史重建的同時又確保破除文化系統的封閉性和保守性及其深層結構中固守著的文化惰性,并升華與活化出一種經典文本中原本蘊含的當代意義,這才是“歷史重構說”內部的真正緊張,也是它被“合理應用說”取代的關鍵之點。
二、“合理應用說”與意義預期法
西方語言學關于理解的第二種理論認為,理解本質上屬于一種合理應用,其方法在于“意義預期”。當代西方語言學家,如保羅·利科、卡爾-奧托·阿佩爾、姚斯等人認為,在進行語義詮釋或者理解時,能否執行一種跨文化理解和對話的策略,對把握一個文本的復雜性語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每一種文本都必須被理解,理解本質上屬于一種語言學的自覺運用,文本學必須并入語言學而且被視為語言學的內在組成部分,文本的語義才能因為獲得合理理解而生成。伽達默爾也認為,一切文本只有在理解過程中,才能實現由“無生氣的意義痕跡”(僵死的語義)向有生氣的“意義活體”轉換,文本的意義域、信息域是在其獲得的對話和理解中不斷自我生成的,它的復雜性的意義結構也是隨著閱讀者恰如其分的接受不斷得以向深層開掘的,換言之,文本有沒有意義或有什么意義,“完全在于理解者如何接受”[2](P342)。即使是對于那些歷史性的經典文本的語義生成,閱讀和理解同樣發揮著關鍵作用,二者一同被視為頗具語言學意義的精神性事件。解釋和理解是同一個東西,或者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要達到理解必須要通過解釋,而解釋中理解無處不在,解釋和理解其實水乳交融、內在一體。二者統一的過程其實就是文本被應用、意義被增殖的過程,只有在應用中的解釋才是最高意義上的解釋,只有在理解中的應用才是最恰當的應用。任何理解都是應用性的,理解的本質就在于應用。現代語言學在理解基礎上分析語義及語用問題時,反對那種“語義客觀外在說”,從不主張有一個純然外在的原始語義能夠普遍地被應用到各處,更不認為讀者只有完全懸置自己的主觀意見才能去做純粹性的理解。恰恰相反,讀者往往是通過應用才達到合理理解的。理解、解釋和應用三位一體這一事實本身表明,凡理解都是相互理解、科際合作,凡解釋都是跨文化交流、創造性的生成,凡應用都是合目的、合規范的自覺應用。積極的應用無論對于作者抑或讀者來說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主導因素,任何一個文本語義總是與它在某種具體范圍內的實際應用中一道被顯發、被照亮的,沒有真正的應用,再完美的語義也不可能被接受。可見,語用學知識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本詮釋中,值得我們把它作為一個一般性的詮釋學基礎問題加以探討。
理解的應用性或者實踐性本質表明,對文本的理解其實就是對文本意義的主觀預期,是解釋者對生活經驗的未來可能性的一種籌劃。文本的意義并非為文本自身所固有,并不存在一個純然的客觀外在的作者原意或文本意圖,文本意義是在與讀者的接受關系中產生的,并隨著解釋者主觀預期的變化而變化,一切都取決于解釋者意義預期的能力與水平,離開讀者對文本意義的籌劃與預期,就不能實現任何積極的意義接受與合理應用。進一步說,文本在與讀者的接受關系中能夠產生的意義并非只有一種可能性而是有許多種可能性,究竟哪一種可能性的意義能夠實現,這完全取決于主觀預期的方向和意義籌劃的性質。文本的意義完全取決于應用,它不是一個意義自足性的完成物,而是一個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它充滿著各種各樣為人所用的可能性,而積極正當的理解就是對各種可能性做出恰當選擇與最佳規劃,在應用中獲得合理理解,在合理理解中獲得內在超越。可見,理解就是在文本的各種可能性中通過主觀預期而籌劃新義,沒有應用就沒有理解,應用是理解的本質構成,換言之,理解與應用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由于任何理解都存在自己的前結構、前理解,任何應用也都存在自己的詮釋學處境,因而理解與應用總是根植于解釋者先前已有的東西,以某種預先假定的意義預期為前提、以某種先行理解和先入之見為基礎。解釋本質地建立在前把握之中,任何解釋都是主觀期待與實際應用的結合。理解最終都是“自我理解”,理解都包含著對自身的籌劃,都是對主觀預期的意義做出理解。[3]誰理解,誰就是在理解自己,也就是按照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去籌劃。而誰理解文本誰就是對之進行意義籌劃,一旦這個最初籌劃的意義在文本理解中出現了,解釋者實際上就為整個文本的理解定下了基調,并帶著這個意義的整體期待做出全面的理解。主觀期待好像是“過早行動”,它為理解這個文本預先籌劃了一種意義,作為一種內在牽引力促使解釋者按照自我規定的方向做出解釋,理解說到底就是對主觀意圖的自我理解。當然,這種前理解也有可能出錯,但是持續不斷的深入理解總是在對意義預期做出合理的修正,理解不是一成不變的,解釋者也并非頑固地堅持其前理解,而是時時處處保持理解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是雙向的,不是要求理解者放棄自己的前見,而是將之帶入理解中并整合到文本所啟示的內容上,從而實現文本意義的自我生成。
三、“交往互惠說”與視域融通法
西方語言學關于理解的第三種理論認為,理解本質上屬于一種交往互惠,其方法在于視域融通。在尤爾根·哈貝馬斯、米歇爾·福柯、理查德·羅蒂等人看來,其實文本的意義并不是僵化、靜態地凝固在原始文本中,也不是純粹主觀上心靈預期的結果,作者意圖、文本原意與讀者的主觀預期和積極應用密不可分。對文本的理解和詮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作者和讀者圍繞文本意義的開發不斷展開對話與交流的過程,而不是讀者擺脫一切先見聆聽作者心靈獨白的體認過程。作為理解和詮釋的積極成果,文本意義的自我生成、自我創造與不斷增殖,不是對作者意圖或者文本原教旨意義的簡單復歸,而是在作者意圖和讀者期待這兩種視域的交互作用、雙向交流下產生的交往互惠、重疊共識。凡理解都是通過對話而進行的精神交往,交往性是理解的本質屬性,或者說理解本質上就是交往。具體說來,首先,任何一個文本新義被詮釋,都是作者意圖、文本意圖與讀者意圖交往互惠的結果,只有當文本意圖和作者意圖與解釋者的積極理解、合理應用相結合時,才能不斷生發出新的意義,離開了真正的理解和應用就沒有任何意義可言。文本是用于被理解、被應用、被創造的,讀者預期參與了作者對文本意義的一同創造,離開讀者的意義接受,文本意義歸于零。其次,任何一個文本,從根本上說都是未完成性的,都具有許許多多的未定點和空白處。只有通過多種視域的融通,解釋者通過主觀性的預期、想象性的理解與合理性的應用,才能將這些未定點和空白處填充并豐富起來,為文本再造出各種各樣的活生生的意義來。再次,文本意義并非自在的存在體,任何文本都沒有單獨存在的權力,并不存在一個可以脫離解釋視域的文本原意。文本意義不是等在那里需要讀者客觀性地予以描述和再現,而是與解釋者的理解一同存在、一同生成的,若沒有解釋者對文本意義的積極籌劃和善的選擇,若撇開解釋者不斷從當下的可能性向著未來推進,文本就是一堆毫無價值、不可理解的文化垃圾。只有通過作者、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問答和質疑,唯有在問答邏輯中發生思想交往,積極的理解與合理的應用才能使文本意義從死的語言材料中脫離出來,變成具有現實意義的時代精神與活的靈魂。最后,文本理解總是受主觀預期之“流動視點”的制約。解釋者的意義期待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前理解和前結構也總是不斷被作者意圖和文本結構所修正,這樣,基于意義期待而形成的內在牽引也不是凝固不變的,它總是引領著解釋者向前、向上地做出善的選擇和意義提升,不斷在作者意圖、文本意圖、讀者意圖的內在本質處實現通約、達成和諧。
對于同一文本,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不同讀者,基于不同的而且是流動的意義期待(流動視點)獲得不同的理解。而一個文本所潛在的意義不會也不可能為某一時代的讀者所讀盡,只有在不斷發展的接受過程中為不同讀者所不斷挖掘。這表明,理解不僅是歷史的,同時又是現代的;不僅是作者的創造,而且也是讀者的創造。文本意義在本質上既隸屬于歷史又隸屬于當代,是歷史與當代的意義匯合,是作者意圖與讀者意圖的內在融通。因為,理解不僅要以作者原意、文本結構為基礎,而且要基于主觀期待經常對之實現意義增殖;解釋不僅要以前理解為根基,而且在它的內在牽引下還要對當前的可能性做出合理的未來籌劃。當讀者以自己的當代視域去理解作者的原始意圖和文本結構時,作者意圖、文本意圖、讀者意圖就發生內在緊張甚至會導致相互對立,只有各自放棄自己的片面性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視域整合,才能構成一種新的和諧或者深層通約。合理的詮釋,事實上就是一種基于視域融合的內在溝通與和合取向;也只有通過視域融通才能克服各種意圖的局限性,使得理解能夠向一個更高的普遍性上升,在歷史基礎上產生普遍交往的合理化,真正實現跨文化交際和主體間共識。
總之,只有在視域融通的意義上,將這三種把握方式整合起來,才能獲得積極合理的理解。因為,文本理解的視域融合也存在限度問題,正像交往存在“偽交往”[2](P329)與合理交往一樣,視域融通也存在文本如何實現內在契合的性質問題。提高文本之間、意圖之間的契合度,既依賴于對文本語境的歷史還原、語境重建和語義復歸,更需要提高文本之間和各種意圖之間與當代實踐視域的相關度、參與度,唯有將作者原意、文本結構與讀者期待一同融入到實踐視域中,實現文本邏輯、問題邏輯與實踐邏輯的內在統一,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性指向與讀者現實處境的特殊性指向之間建立一種雙向性的實踐批判關系[4],才能使這種雙向理解向更高的層次躍遷,使文本語義在更高的普遍性中生長。
四、三種把握方式的內在整合與未來走勢
當代語言學關于理解本質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無論是“歷史重構說”及其心理移情法、“合理應用說”及其意義預期法,還是“交往互惠說”及其視域融通法,都重視語言學的主體認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強調對理解及其本質問題要在應用中予以激發與活化。事實上,離開合理而積極的文本理解,語言的意義構造及其邏輯關系的每一步推理都無法準確進行,文本的真義就會枯竭、思維靈性就會墮落、生活語義就會低迷。若語言學中的生活語境不能使人的心靈睿智在享受快樂中產生靈異和飛動,就很難成為一切文化的藝術之母和思想創新之源。唯有實現文本理解之上述三種把握方式的內在整合,那些充滿瑰麗的詩意之思和深邃雋永的睿智之辯,才內在地構成當代語言學的生命之源并為之注入強大的活力。
唯有實現三種把握方式的內在整合,才能產生和推動語言學的原發動力,激活與驅動思維的固有能量,放大表述對象的意義蘊含,使人的精神境界處于高峰體驗狀態,不失時機地撲捉到盡可能多的有用信息,使之靈思泉涌。語言學獲得創新的源泉既需要歷史重構又需要視域融通,但是只有在合理理解基礎上,才可以將人帶入一個虛擬世界,構造生活中不可能實現的理想意境,使人的思想在享受快樂、享受驚奇、享受自由中激發出少有的靈性和飛動,產生“思極則奇”的語言召喚力。語言學史上的那些思想家們大都是些富于心理移情和視域融通的人,他們總是積極主動地使用合理想象進行意義構境,在思入生活時總是用它開道,在理想的遙遠彼岸獲得啟示之后再返回到現實之中,因而其當代語言學思想的跨度極大,獲得的是一種思維的跳躍和瞬間的靈感。[5]
在未來發展上,當代語言學關于理解本質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歷史重構”、“合理應用”和“交往互惠”的視域整合,每一個語言學的當代理念都要靠這種整合來養育。如果缺乏對新語言元素的整合和對當代語義的召喚,就會使人類的語言學智慧走向委頓。如果一個語言學者丟掉了合理理解、意義預期這種可貴的思想品質,而僅僅面向符號本身的奇跡進行抽象致思,就會導致人類靈性的墮落和擔當意識的飄散,這才是人類文明開始走向衰落的真正征兆。進一步而言,如果語言學者缺乏科學語言觀指引下的內在整合機制,他的語言學操作就會產生病態的語素、尷尬的語境、失真的語義,無法提供合理應用語言的充足理由。缺乏對語言世界的意義整合也很難拔高人的文化交往質量,并使其獲得精神境界的提升。[6]人類憑借當代語言學的合理理解方法,對可能性的未來文化世界實現視域整合,將為人類文明的繼續發展奠基,這是人類語言學思維發展的關鍵性環節。一般來說,“歷史重構”、“合理應用”和“交往互惠”的實際整合能力,就是現代語言學思維所能達到的深度,沒有一種思想能力比合理理解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研究文本本身。現代語言學的生活語境及其對人性的善的選擇和對詩意存在的開敞,是打開人的一切能動的活知識大門的金鑰匙,是一切創造力和智思之流的必由之路,是人類靈魂得以凈化和飛升的奧妙玄機。
[1]洪漢鼎.理解的真理——解讀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188.
[2]夏基松.現代西方哲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朱林.略論西方語系的內在悖論及后學語義對它的解構[J].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1(1):66.
[4]彭啟福.文本詮釋中的限度與超越——兼論馬克思文本詮釋的方法論問題[J].哲學研究,2007(2):18.
[5]舒開智,葉若蘭.走出語言的牢籠——語言學轉向背景下的形式主義文論作者消解論批判[J].殷都學刊,2009(3):106.
[6]朱林.現代經驗主義的語言學轉向及其對形上語義的消解[J].開封大學學報,2012(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