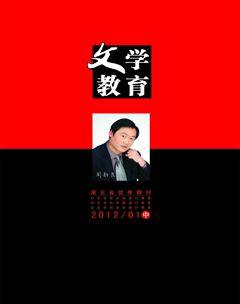天道性命的貫通與儒家的道德形上學
陳靜靜
【摘要】儒家的形上學一直是學界熱議的關鍵,儒家的形上學將“天”、“道”、“性”、“命”、“德”、“心”、“理”貫穿起來,且是道德的形上學。
【關鍵詞】儒家;形上學;天;道;德;性;命;心;理
對于儒家,可能為更多人所熟悉的是它提倡的綱常倫理,這是由儒家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的地位決定的,而關于它的形上境界,普通大眾知之不多。實際上,儒家不僅具有形上意義,而且其形上學境界可以與佛、道媲美。
儒家形上學濫觴于春秋時期的孔子,后經《孟子》、《中庸》、《易傳》的闡發,董仲舒的發揮,經宋明理學家的大膽詮釋,至當代新儒家將其發揮到空前高度。當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認為,儒家的形上學是“道德的形上學”,牟宗三的這個認識應該說準確地把握住了儒學的特征,儒學確實是通過道德的進路進入形上學的,這集中體現在儒家“道”、“德”、“天”、“性”、“命”、“心”、“理”諸概念的內在貫通上。
“道”原意為人行的路,與“行”字相通,以后引申出原則、規則、規矩、規律、道理或學說等多種意義。孔子打破了“道”的一般意義,而將“道”定義為做人治國的根本原則,并且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在其看來,“道”是排于“德”與“仁”之前的最高概念。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可見在這里,孔子將“道”作為一個獨特的概念,與人生的最高目標聯系在一起,使“道”具有了終極真理的意義。
“德”在先秦儒家的理解中特指德行、品德,只有至德之人才能體現至道。“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禮記·中庸》)孟子認為“德”是標志“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或本性。
在孔子那里關于“命”的言說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憲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可見,在孔子這里,雖未講天命,但也未否認天命。孔子也很少就如何為“仁”,何以為“仁”的形上學依據作理論上的探究。但孔子也未否定“天”、“命”的形上性。
早期儒家人物則已開始致力于為“仁學”建構形上學,把仁與天道、性命貫通。《性自命出》中講“情生于性”,其中指人的喜怒哀悲之氣為性,并言“性自命出”,把主體“性情”歸于“天命”稟賦。至《中庸》更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得出性源于天命。至此,“性”與“天”、“命”相貫通。
孟子提出了“心”,他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在此“心”是認知器官。孟子還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指出人性本善,此處的“心”是道德本心。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即“盡心知性知天”。他認為盡自己的道德本心去行事,就知本性為善,就知“天”了。至此,“天”、“天命”與“性”、“心”相貫通。在孟子看來,仁、義、禮、智“四德”既已成為本心本性的內在稟賦,則道德修養自然需要“反求諸己”。如是,則本心即性,心與性為一也。
而《易傳·乾》中指出“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此“性”與“天道”貫通。既然將“天道”看為形上本體,那么“性”與“天道”貫通后,“性”也獲得了形上意義。“心”、“性”亦同。
漢代的董仲舒以陰陽的不同性質解釋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關系,以天為人的價值本原,把人類道德歸原于天。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使得三綱五常等道德原則和規范成了天意的直接體現。儒家道德被進一步宗教化、神秘化,并通過這一過程使得現實的人倫準則具有了超驗的形上意蘊。
至宋明理學家這里,張載強調“天人之本無二”(《正蒙·誠明》),認為人以天性作為自己的本性,天是人的存在和價值的本體根據。人需要通過道德來覺悟、擴充自己的本性,從而發揮、完善天的本性。二程進一步提出了“理”的概念,認為天規定了人的本性,作為人的本性的道德就是天賦予人的理,人的價值就在于獲取了天理。朱熹則明確指出:“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他將儒家道德規范與天相通。陸王心學更是將儒家形上學發揮到極致,提出“心即理”,“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陸九淵集》)王明陽把天的實質規定為“心”,認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王文成公全書》卷六),心即宇宙萬物的本體,這里顯然把人的價值提升到極高的位置。宋明儒學將道德明確地定位于宇宙的本體,極大推進了儒學形上學的發展。
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們,承接了傳統儒學道德本體論的思想,以新的視角從“天道”論證道德形而上學的存在。牟宗三主張“以形上學本身為主,而從‘道德的進路入,以由‘道德性當身所見的本源滲透至宇宙之本源。”與傳統儒學相比,現代新儒家更加強調突出道德存在的超越意義,使儒家的形上學趨于完善。由于儒學道德性命相貫通,超越性的天道內在于道德本性之中,發而為人的道德生活,所以儒家形上學必然將道德領悟貫徹到實際生活中,形成“道不離器、器不離道”,形上與行下相統一的理論特征與實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