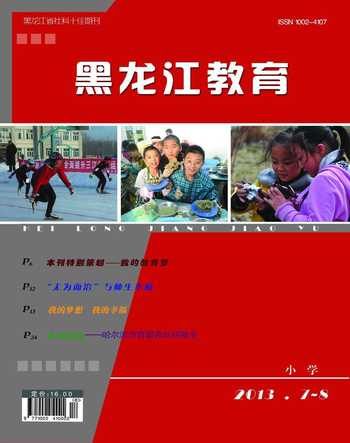“課堂在山里”
朱向明
之所以用此作題目,源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故事“拜人民為師”。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鄉,陶行知請他到曉莊學校教生物課。第一次上課,陶行知就讓他先把書本擺到一邊去,要“隨時教育、隨地教育、隨人教育”。姚老師教了10多年生物課,從來沒有不帶書本去上課的時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
傍晚,他看見陶先生與兩個叫花子在親熱地交談。陶先生和那兩個人談完話,就叫學生領他們去洗澡,然后告訴姚文采:“這是我從南京夫子廟請來的兩位老師,來教大家捉蛇。曉莊附近有許多蛇,經常咬傷人,讓蛇花子來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樣?”姚文采沒說話。蛇花子開始為曉莊師生上生物課了,課堂在山里。
幾天以后,最膽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們說:“只要擊中要害,蛇并沒有什么可怕呀!”大家還懂得了蛇沒有腳為什么跑得快,蛇沒有耳朵怎么聽得見聲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識。姚老師終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帶領學生采集標本;把挖草藥的老農請來教認草藥;請種花木的花匠來教種植花木的方法。曉莊附近的花草樹木都掛起了學名牌,生物課從此上得生動活潑。
陶先生“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生活教育”核心理論影響甚廣,一直為我國現代教育人所推崇。他認為:做好學校和社會的聯系,加強社會實踐,引導學生從實際生活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教學時間不一定在課內,完全可以利用學生的課余時間;教學地點也不一定要在教室,社會是最好的課堂,讓孩子們走出去,親密地去接觸社會,在生活中學習和成長等。為了貫徹“生活教育”理念,在陶先生身上就出現過多例“課堂在山里”的案例,如“修表事件”“蜻蜓的故事”等。
所謂 “課堂在山里”,就是有時候因學情的需要,我們不妨將“課堂”從教室“搬到”生活中去,借助生活中的具體物象來更好地詮釋書本上那些較枯燥的文字或人生道理。想來,有些時候,作為老師真的不應僅拘泥于教室,不應僅拘泥于書本,學學陶行知,嘗試著把課堂搬到“山里”,那一定會成就別樣的精彩!
古今中外其實還有不少教育家給我們留下了“課堂在山里”的精彩案例。不妨再曬二例與大家分享。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最著名的教育家,他最深諳“課堂在山里“之道,最有名的當屬已選入蘇教版第十二冊的《最大的麥穗》,由于大家對此耳熟能詳,我就不再贅述。這兒,我想給大家說個蘇格拉底的另一案例——《尋找快樂》。
“快樂到底在哪里?”一群學生四處尋找快樂,卻終無所獲,他們只好向老師蘇格拉底尋求答案。
蘇格拉底思考了一小會兒,然后說:“你們還是先幫我造一條船吧!”
這群學生聽后,趕緊鋸倒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樹,挖空樹心,用了七七四十九天造出一條獨木船。
獨木船下水了,他們把蘇格拉底請上船,一邊合力劃槳,一邊齊聲唱起歌來。
蘇格拉底問:“孩子們,你們快樂嗎?”
他們齊聲回答:“快樂極了!”
蘇格拉底揭示了答案:“快樂就是這樣,它往往在你為著一個明確的目的忙得無暇顧及其他的時候突然來訪。”
“快樂到底在哪里?”倘若蘇格拉底在常規課堂上用書本上的現成語言描述,或許也能淺淺地說出個子丑寅卯來,但孩子們理解起來怕是多浮于淺表。把課“搬”到生活中后,學生們有了切身體驗,想讓他們迷糊都難!
現代文史大師劉文典也明了“課堂在山里”之道。
劉文典教學有個特點,就是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在西南聯大時,有一次,他課上了半小時,就結束了內容。同學們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后七時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歷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里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辟,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所返。
月下講賦,情景交融,一切物語皆情語,師生自然很快就進入到詩的意境之中,那效果無疑是常規課堂所無法比擬的。
作為一個愛動心思的普通老師,我在平時的教育教學中也時常踐行“課堂在山里”,效果不勝欣忭。
在教學蘇教版六年級下冊《廣玉蘭》這篇課文時,我忽然想到了學校操場的西南角有棵樹齡超過10年的廣玉蘭,于是就想,何不把課堂搬到那樹下?這時候,那廣玉蘭正葉茂花盛呢。
“孩子們,生機盎然的廣玉蘭活脫脫地展現在大家眼前,請對照課文中的文字,從不同的角度印證相應的描述對象,物文相照,以更好地讀懂作者帶來的廣玉蘭的獨特美。”我親切地招呼大家圍攏來,請他們以小組為單位觀察學習。
孩子們手捧書本,迅速以廣玉蘭為中心圍成幾個小圈。開始大家都還靜靜地觀察著,不一會兒,便發出了一聲聲驚嘆。
“喂,你們看,那葉背真的有鐵銹色的絨毛耶。”“真的真的,看這葉面真的好像涂上一層蠟!”——小楠那組發出的。
“咦,你用心聞聞,淡淡的,多像圖書室里的書香味兒。”“是有點兒,不過,你難道沒感覺出那還有點兒絲絲的甜味兒嗎?”“怪不得書上用了一個詞‘幽香,真好!”——小敏那組發出的。
“快來看,那盛開的花朵真的是‘潔凈、高雅!”“真是太美了,的確如作者所說,‘只憑幾個優美的詞句是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內涵的。”——小可那組發出的。
“哎,看這兒,有個剛打骨朵的。” “書上用‘含羞待放一詞來描述,讀來多親切!”——小陽那組發出的。
“唉,廣玉蘭開花真的有早有遲!看那兒,就是最上邊的那朵,‘花瓣雖然凋謝了,花蕊卻依然挺立枝頭,它的圓莖真有書上所說的近兩寸長呢!”“圓莖上面真的綴滿了像細珠似的紫紅色的小顆粒呀!“”書上說,‘這就是孕育著新生命的種子!”——小迅那組發出的。
…………
紛紛擾擾中,根本不用我多少口舌,孩子們在盡情享受愉快課堂的同時,已經高質量地完成了本節課目標——人、樹、文完全交融在一起。
“讓我們跟著作者卜曉芳再一次感受廣玉蘭旺盛的生命力吧——‘一天晚上, 我獨自在叢林中散步,感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在空氣中蕩漾……”在班得瑞《初雪》那舒緩的音樂聲中,師生一齊聲情并茂地朗誦起來。
把課堂搬到樹下,孩子們近距離接觸到廣玉蘭,更直接感受到書本上文字所透出的質感和美感,那是再好的常態課堂所無法比擬的。
以上案例,都是教者出奇制勝地把課堂搬到適合的地方去。的確,我們的課堂絕不應一味地窩在教室里,大自然、街道市場什么的都應該成為我們的教室。讓孩子走出去,去接觸外面的世界,去感知外面的人和事,去體察食物的變化,這不是能更好地促使學和用結合嗎?不是更能真真切切地去體驗人生的苦與樂、品味生活的苦與甜嗎?
陶行知先生在《教學做合一之教科書》一書中這樣說道:“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敬愛的老師們,請相信有些時候“課堂在山里”的確有其妙處——生活無處不課堂,大地無處不教室。我們做教師的,應該向陶先生他們一樣多讓學生走出去,多把課堂搬出去,給孩子一個開拓視野、增加見識的機會。否則,僅抱住常規課堂不放,那只能是一種“死教育”!
(作者單位:江蘇省睢寧縣官山中心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