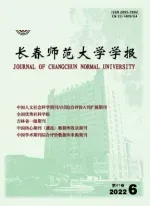解構視角下英語專業精讀課教學
董志浩
(湖北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0)
解構主義的出現在全球思想理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對于人文學科各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解構主義所提出的消解中心、反叛權威等思想也給精讀課教學帶來了新的啟示。本文從解構主義視角出發,探索高校英語專業精讀課的教學改革。
一、解構主義理論
20世紀60年代,解構主義的代表德里達先后發表了《論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和差異》三本著作,這宣告了解構主義的確立,西方思想界開始從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過渡。解構主義的領軍人物德里達反對西方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并且通過文本對語言符號的意義進行批判性解釋,將之推廣到一切事物上,認為“世界除文本外無物”[1]。解構主義的目的在于打破舊結構,顛覆原中心,釋放原有結構中的邊緣因素,進而提出一種新結構,且這種結構并不是恒定的,只是臨時性的功能[2]。由此,解構主義瓦解了邏各斯中心主義,消解了二元對立。
二、高校英語專業精讀課現狀
精讀課是高校英語專業一、二年級的專業必修課,目的是幫助學生全面提高聽、說、讀、寫、譯等五種技能,每周課時量也是所有專業課程中最多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一直以來,提高精讀課的教學質量是英語專業教學改革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傳統的精讀課教學出現了僵化、教條化的傾向,精讀課成為一種封閉式的教學。這些直接導致了精讀課教學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筆者所在的外國語學院每學期都會開展教學評價,聽取老師和學生對于課堂教學的意見和建議,從各個學期的匯總材料來看,精讀課的滿意度不是很高:一方面,教師經常會談到精讀課的備課量很大,需要做非常多的課前準備工作;另一方面,學生總是感覺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學到的東西不夠多。
三、解構主義對于精讀課教學的啟示
目前高校英語專業精讀課的現狀不容樂觀,解構主義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的理念,對于精讀課的教學有不容小覷的啟示:
第一,破除課堂上的權威論。解構主義消解了人們的定式思維:追求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絕對正確的標準,一個一成不變的等級模式。它的多元性、無中心性、多維思路,使人們超越了傳統的視界,從而發現了許多過去難以見到的新問題和新意義[3]。在傳統的精讀課堂上,教師的權威地位顯而易見且不容置疑。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有著絕對的話語權,掌控著教學進度和節奏,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計劃講授課文,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必然處于非常被動的狀態,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而只能被動接受教師的講解和看法。一些學生在教學反饋時提到在精讀課堂上一直記筆記:記單詞用法、記詞組用法、記句子釋義。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在短時間內解決大量的問題,但是卻沒有充分給予學生獨立思考的空間和時間,使學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也許是英語專業學生知識面普遍狹窄的原因之一。要改變這種現狀,應該借鑒解構主義反對權威的理念,合理調節優化精讀課教學中的師生關系,使教與學不再對立,而找到彼此最好的切合點,既不以教師為中心,也不走極端,完全以學生為中心。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通過課前布置、課堂提問、課后討論等方式來給學生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讓學生從被動接受老師的理解逐步過渡到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對于學生的理解,教師應給予充分的鼓勵和支持,在必要的時候要加以引導。
第二,消解課堂上的二元對立。在西方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進程中,邏各斯中心主義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由此孕育而生的二元對立也深入人心。人們想當然地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來看待這個世界,如正確與錯誤、理智與情感、主觀與客觀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邏各斯及與其相關的二元對立等西方傳統思想開始受到挑戰,解構主義者開始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邏各斯中心主義,指出了二元對立存在的荒謬。這一點對于當前高校英語專業精讀課的教學改革來說也很有意義。在傳統的精讀課堂上存在著教師與學生、正確與錯誤這樣的二元對立。然而,此二元對立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平等并列,而是有主次、等級之分的。比如,精讀課第二冊第2單元Say Yes 這篇課文,教師在講解課文主旨時,一般會先通過討論或者提問的方式了解學生的看法,最后總結后給出自己的理解,告訴學生這篇課文的主題與種族主義有關。學生一般會放棄自己的想法而去接受老師的解釋,認為老師是正確的。要克服這種非此即彼的簡單思維模式,就要消解課堂上的二元對立,這樣才能讓學生有獨立思考、分析批判的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氣,而不是去隨大流、趕時髦、瞎起哄;才能讓學生學會尊重不同的觀點,學會理性、客觀、全面地看待問題。精讀課教學應該培養學生發問的習慣、通過分析尋找真理的能力,而不是頭腦如同電腦軟件一樣,只能定向思維。
第三,“互文性”是解構主義中的一個關鍵詞,德里達用“延異”、“蹤跡”及“播撒”三個概念闡述了他的互文思想。他用嚴密的論證推翻了索緒爾提出的歷時與共時、能指與所指的對立,認為語言意義產生于內部因素的區別與差異,同時,這種區別與差異是持續進行的,因而不可能產生在場的所指。他認為文本的含義有著有空間和時間上的差異,因此意義一直處于無限延伸的過程中。他的這種理解也給精讀課教學帶來了一些啟示,即精讀課不應該成為一種封閉的教學,而應當借助互文性,不斷擴展學生的視野。互文性在精讀課上主要體現在語言文化、體裁、媒體等幾個方面。比如《現代大學英語精讀(第二版)》第一冊第一單元“Text A Half a Day”,從開始的描述中讀者知道文中主人公是個小男孩,講述了他第一天上學的見聞,但是到了文章最后一段卻是“He stretched out his arm and said:‘Grandpa,let me take you across’”。文章前后語言描述的對比讓讀者意識到這篇文章并不是簡單描寫小男孩上學的第一天,而是有隱含意義的。“The Rithe of Spring”這一單元,這個題目當然和文章的內容密切相關,但是也應該提醒學生,讓他們了解這個題目是來自20世紀美籍俄羅斯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的芭蕾舞劇。這樣的借用不但和文章內容十分切合,而且從風格上來看也是非常合適,因為阿瑟·米勒這篇短文充滿詩意,借用芭蕾舞劇的名稱再合適不過了。“Green Banana”這篇課文的題目指代的是其他文化中我們所不了解的精髓,由于大學班級學生來自很多不同地區,他們會想到與同學接觸時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以及借鑒作者對于其他文化的態度。總之,在教學中應當充分利用互文性,使更多的語義潛勢在學生和文章的互動中呈現出來,為精讀課教學提供一個立體的思考視角。
四、結語
盡管解構主義有著一定的消極意義,但我們可以借鑒解構主義的一些獨特視角來重新審視高校英語專業的精讀課教學,找出其存在的弊端,在課堂教學活動中要有所“解構”,同時也要有所“建構”,而不是一味“拆毀”、“打破”。對于高校英語專業精讀課的探索應不斷向前推進,使之適應時代的發展。
[1]肖錦龍.德里達解構理論思想性質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3]王岳川.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