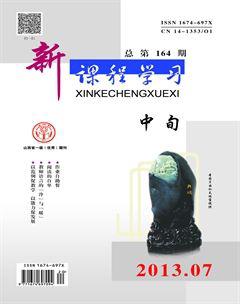知不足而自省
陸燕
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
——孔丘《禮記·學記》
當我在語文書上圈點勾畫時,我胸有成竹地對自己說,我準備充分了;當我看完網絡、教參寫下自己的教案時,我胸有成竹地對自己說,我準備充分了。但是,當我教學進入正題時,我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還沒有準備好什么呢?那就是廣大的聽眾,我可愛的學生。備課重要的一個內容還有學生,而不光光是你的課文。我依次回想了我以前的公開課:我發現我犯了一個同樣的重大毛病,那就是為了在公開課上秀出自己的特色,完全不把學生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還事后暗中埋怨:學生太緊張、學生不配合,或者是學生沒有能力。結果,越是想與平時上課不同,在公開課上秀一秀;講課的清晰度越是不如平時上課,學生接受知識的量越是不如平時上課所得。就拿這堂失敗的公開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為例談談自己的失與得。
一、“老師備課”與“學生預習”
老師備課尤其是備公開課怕自己對課本的把握不夠準確,就從網絡、教參上對此課的分析找了個遍,鋪天蓋地的資料要想把他自己消化。我想,只要知識點不沖突,任何一個老師都能做到,而且,自我感覺到對于這篇文章的研讀非我莫屬。學生預習:就算是最認真的學生也是將課文看一遍,查幾個生字詞。看一下練習冊。這樣就算師生雙方原本對陌生課文理解相差無幾的水平,此刻也成天上地下了。比如,當我在《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第一課時約20分鐘后上拋出問題:(答者)我從物質基礎角度研究,我發現,花呈某種顏色的原因。(評者)我覺得某某的回答有(條理、零亂、準確、真實……)因為他在介紹時運用了某種順序、方法。學生討論了5分鐘后,我問有結果了嗎,反應很小。頓時,我發現,我的問題可能過于難。那就引導吧,越是如此,越是“趕鴨子上架”,越是東拉西扯,越是讓不懂課文內容的學生和聽課老師覺得課堂知識內容的零散。
教與學不是單方面的事。因而,我們一方面把自己當成學生,勤做題。在接觸課文前做一份到兩份課文同步的習題。了解每一種題型需要花費的腦力來衡量知識點的難易指數。另一方面,也要精選學生的預習題來了解:與教學內容有關的課文內容學生是否熟悉;與教學內容有關的學生已學過的知識的情況學生是否還記得;與教學內容有關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學生是否掌握。
二、“避重就輕”與“化難為易”
《花兒為什么這樣紅》一文雖然有條不紊地從不同角度介紹有關花朵為什么呈現紅色和其他顏色的科學知識。但是,這篇文章運用了大量的生物、物理、化學方面的專業知識,這對于課文的深度理解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我本著不把語文課上成生物、物理、化學課的原則,打算避重就輕。比如:上課伊始,我為了帶學生理清課文的順序,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作者為何以“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為題?我預想學生通過預習應該了解課文的大概內容,如今粗略地看一遍課文,抓住課文每一部分的反復句,應該回答。不料,這時我就是沒有看見有哪位學生舉手,甚至看一看我。我發現成績好的同學,多是困擾在酸、堿、光譜之類專業術語里而不能自拔。他們的那種情景就像我們看到陌生的熱帶水果,明知道不管使用什么方法總可以吃,但就是不好意思嘗試一樣。我感到失望的同時,開始引導他們從課文的內容與結構角度去考慮。雖然,最終學生答出來了,但是,不但沒有節約時間,反而帶著學生繞了一大圈后還是讓聽課者聽的云里霧里的。
與其避重就輕不如化難為易。如果我想預先給學生講一講相關的術語,想掃清生字障礙一樣掃清術語障礙的話,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尷尬了。
三、“守株待兔”與“隨機應變”
在備課之際,許多人與我一樣,將上課的每一環節的問題與答案預設好了。但是,就算是把每一個環節的過渡句都預設好了,就算準備好了嗎?事實證明,不是,那種做法與“守株待兔”沒有區別。通過《花兒為什么這樣紅》這一課,我越發覺得學生與教者的思考思路不一定一致,答案也肯定不一致。這時,該怎么辦?是誘導學生跟你走,還是你跟著學生走?我想,如果我一味地要求學生順從教者的話,那也許徒勞而返,也就是學生能力、方法什么都沒有學到;也許挫傷學生主動思考,多向思維的能力,也就是學生自卑地認為自己總是出錯,自己沒有能力靠自己的能力解答問題了。
所以,雖然我不能完成這一堂課的教學任務,那就給學生點自信,給學生點興趣,給學生解題的能力與方法吧。既然,學生不懂酸性與堿性,那我就在教學僵局時,把原本備用的酸堿實驗做起來,雖然浪費了時間,但學生思維活了就行。既然,學生給出了答案,那我就要隨機應變地做最全面的評價:是對,是錯,是片面,還是不夠深入;思路是正,是反,還是不到位。當然,肯定的學生的同時也要注意分寸。不然,會導致學生瞎答題,走偏鋒。
學習然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授然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知道不足然后才能自我反省。知道困惑然后才能自強。沒有誰能鐵口說自己的教學沒有絲毫錯過。但是,通過不斷地反思,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能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
(作者單位 江蘇省武進焦溪初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