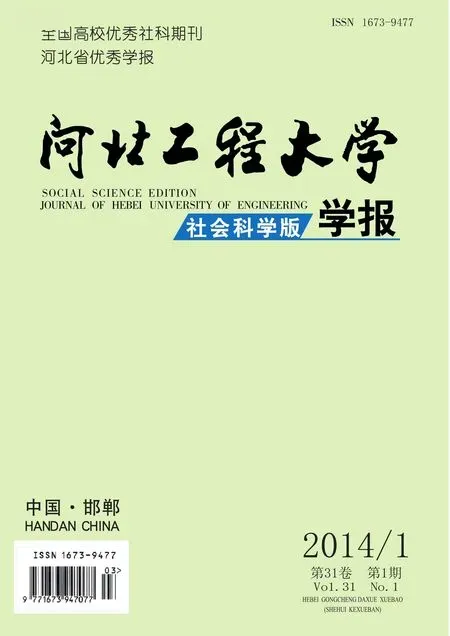從武安儺戲看中原儺的存留特征
何石妹
(河北工程大學;文學院,河北;邯鄲;056038)
儺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現象,它起源于上古時代逐鬼驅疫的巫術活動,發源于中原地區。由于當代采集到的民間儺事活動多分布在長江以南,學術界一度有“江北無儺”的斷言,關于現今中原儺文化的研究也曾是學術界的一項空白。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人們在河北武安發現了一種大型的儺事活動,以武安固義村西大社組織的《捉黃鬼》為代表,顯示出中原儺的典型特征。武安儺戲的發現,不僅改寫了“中國長江以北無儺”的斷言,而且為研究儺的起源、本質和以及儺文化的發展演變提供了一個完整豐富的中原儺的標本。但是直到今天,人們對武安儺戲的關注,多停留在其作為戲曲“活化石”的價值之上,并未對它作為中原儺的本質和特點做以深入的研究。本文認為,現存的武安儺戲,集中體現了中原儺的特征,并展示了中原儺的存留和發展情況,對其價值的挖掘還有待深入。
一、鬼神信仰和巫術行為的殘存
武安儺戲的核心環節是《捉黃鬼》表演,主要情節是在閻王、判官等眾神的監督和審判之下,由“大鬼”、“二鬼”和“跳鬼”把代表瘟疫和災害的“黃鬼”呼喝、驅逐,最終押赴“刑場”、極刑處置。這是一個基本的請神逐鬼、驅疫避災的過程。武安儺戲之所以可以稱為“儺”,正是由于保留了逐鬼驅疫這一核心的內容。
葉舒憲在分析神話結構時比較明確地表述了先民的“三分世界”觀念:“神話意識中的三分世界分別確定了神、鬼和人的空間分界。在正常情況下;三界之間的界限是不得混淆的。神界是永生的世界;凡人與鬼魅不可企及;人間是有生亦有死的世界,一切生物都要受到死亡法則的支配,它們的最后歸宿是地下的鬼域……”[1]而當人鬼之間的界限被打破,鬼出現在人的世界中時,就可能對人產生危害。按照原始思維的邏輯,鬼也是外部力量的一種,同樣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去控制和驅逐它。而儺,就是一種集中的巫術逐除儀式。
與眾多的南方巫儺相比,武安儺的鬼神信仰特征和巫術色彩相對淡化,但依然保留著許多相關的內容。首先“黃鬼”本身就是疾病和瘟疫的化身,一般都由乞丐或外鄉打工人員扮演,無論是其他參演成員還是圍觀的群眾,在驅儺過程中都唯恐避之不及。相反,對于能夠驅逐黃鬼的“大鬼”、“二鬼”和“跳鬼”,人們都歡迎他們進家歇息,家中有“臆病”患者的人家,會主動地邀請大鬼和二鬼去家里為自己捉鬼祛病。參加儺戲的成員在表演之前,要在三天之前也就是正月十二的上午進行統一的凈身子儀式,直至正月十七日,男演員都要禁止房事,叫做“壓身子”。驅儺時用的面具,也被人們視為神物,演出之前要對其燒香上供。驅儺時所用的騾馬,人們要精心喂養、不得打罵,還要在騾馬尾巴上捆綁紅布條,目的也是為了驅邪。在驅趕“黃鬼”時,人們手中拿著柳棍,因為人們認為柳樹有辟邪的功能。在驅鬼儀式完成之后,人們會把靈案上的貢品分吃掉,據說可以分得神靈的護佑,不懼惡鬼。
所有的這些思想、行為和禁忌,其實都是鬼神信仰和巫術行為在武安儺中的表現。這些現象一方面昭示了武安儺戲作為一種正宗的“儺”的起源,而并非有些人認為的地方戲曲和迎神賽會活動的嫁接;另一方面,這種行為類似于現代人在婚禮或節日上的某些習俗,例如崇尚紅色、偏好吉利的數字、懸掛有意義的牌符等等,究竟人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這些并不確定,但通過外力影響世界的愿望,是一種共同的集體無意識,千百年來長久地存留于人們的記憶中。人們對于儺事活動的熱衷,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此。
二、儺儀的完整性與雜糅性
(一)“大儺”之儀的完整保存
據史料考證,儺在商周時代開始確立為宮廷祭祀儀式,兩漢發展為聲勢浩大的宮廷大儺,相關史料對此有不少詳細的記載,如: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周禮·夏官·方相氏》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制,執大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仆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
——《后漢書·禮儀志》
武安儺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環節:
請神:請龍王、白眉三郎眾神即位。
亮腦子:即在演出前一天隊伍進行預演。
踏邊迎神:隊伍游走村內道路,驅除邪祟。
擺道子:正月十五早晨 7點之前,隊伍依次擺開,驅儺主角大鬼、二鬼跳鬼和黃鬼進入道子中間,開始“勾黃鬼”。
南臺抽腸:黃鬼被押至斬鬼臺破肚抽腸,處以極刑。
賽戲酬神:在村中戲臺上演出賽戲,并在戲臺上祭祀天地神靈。
祭祀蟲蝻王與冰雨龍王。
送神:正月十七,把龍王等眾神的牌位送回他們的廟宇里。同時,在奶奶廟中“燒完表”,即上香燒紙,并把寫有禱文的完表焚燒。
過廚儀式:即前文提到的社首之間的交接儀式。吃供餉:所有人員共同把祭祀神靈的供餉吃掉。武安儺戲的整個儀式和漢代大儺在形式和風格上十分相似。尤其是驅儺的方式也是佩戴面具,沿門游走,驅逐惡鬼邪祟,和“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索室驅疫”的方式類似;風格同樣是呼喝恐嚇,聲勢浩大;在驅儺前后的請神和送神等祭祀儀式,也使得它具有大儺的完整性和嚴肅性。
儺在中原一度成為國家性的大禮,但是隨著官方儀式形態的倫理化和現世化,儺文化和主流儒家文化的對立日益顯明,逐漸流落到民間和邊遠地區,直接導致了一度“江北無儺”的論斷。而武安儺戲的存在,向我們展示了中原儺獨特風貌,透過它我們可以依稀看到當年中原大儺的樣貌和風采。
(二)儺儀的世俗化發展
與南方巫儺相比,中原儺最大的不同便是在祭祀儀式上融合了儒家禮樂、民間信仰等因素的影響,雜揉了其他民間祭祀的形式,具有世俗化與現世化的特征。
被驅逐的“黃鬼”,最初是“黃病”、瘟疫的象征,但在后世村民的眼中,他還是忤逆不孝、危害鄉鄰的惡棍的化身。黃鬼受到處置之后,掌竹會有這樣一番唱詞:“勸世人父母莫欺,休亡了生爾根基,倘若是忤逆不孝,十殿閻君不饒你”。這種認識顯然滲透了儒家的禮教觀念。同時,在驅儺時請的眾神,既有源自于佛教的閻羅王,又有道教神如玉皇大帝,還有源于古代神話的龍王,甚至包括民間俗神白眉三郎。民間信仰與宗教有所不同,宗教信仰多是通過神性的感召使人們敬畏,民間信仰則通過人性的參透讓人們親近。[2]這個龐大的諸神群體,不分流派和身份,以實用性和多功利性為目的,比較鮮明地體現了民間信仰的特征,即典型的“唯靈是信”。[3]
和信仰對象的多功利性相匹配,武安儺的整個過程中除了驅除黃鬼,還摻雜了更加具體和世俗化的祭祀方式。例如祭祀蟲蝻王時,眾人端著乘有香、紙錢的端盤,挑著兩只盛滿清水的鐵皮桶,撒上小米和面粉,手持五彩紙旗和三眼銃,敲鑼打鼓來到南山下,點燃香紙,揚起彩旗,點放三眼銃和二踢腳,把之前鐵桶中的米面潑灑出來,眾人跪拜祈福。這些祭祀目的更加明確,方式更具有民間生活的意味,體現了人們對現世安樂的注重。
三、儺戲的演化與聚集
(一)隊戲、臉戲與賽戲
與南方一些特定的儺戲品種不同,我們今天看到的武安儺戲,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戲曲品種或單一的表演形式。“武安儺戲”是一個籠統的的稱呼,從表演形態上講,“戲”的成分既包括了驅儺隊戲,又包括了與驅儺情節相關的臉戲和小型賽戲,甚至一些與驅儺情節無直接關系的大型賽戲也被認為是武安儺戲的一部分。
《捉黃鬼》的核心環節,即大鬼、二鬼和跳鬼沿街捉拿黃鬼、押赴刑場的表演,在藝術形式上屬于隊戲范疇。所謂隊戲,主要指以沿街游走的形式演繹一定的故事情節,觀眾可以隨著隊伍的前進跟隨觀看,這種形式在隋唐時代就已存在。隊戲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很容易帶動觀眾的熱情,把一個請神逐鬼的情節完整地展演開來,但如果觀眾對演出的背景與內容不甚了解,將很難理解演出的實質意義。[1]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武安儺戲中,演員在表演時,也會通過一些道具手段或行為動作把表演情節更加明確。例如在黃鬼的胳膊上裝飾鮮血淋漓的尖刀,表示對他的懲罰,表演極刑處置時,會有腸子、獻血等道具。這些表演方式在早期儺戲中是沒有的。
在《捉黃鬼》進行的過程中,還會穿插一些和捉鬼相關的小型劇目。在黃鬼被捉住之后,演員會在玉皇大帝的神棚前表演《吊綠臉小鬼》、《吊四值》、《吊四尉》,這些劇目情節簡單、動作古樸,有街頭啞劇的特征。由于演員均帶面具,也被稱為“臉戲”。
“捉黃鬼”隊戲結束之后,就是形式各異的賽戲演出。關于賽戲,在山西上黨發現的明萬歷年間古賽抄本《賽上雜用神前本·聽命本》這樣解釋:“夫賽者,所以報天地生成之德,面樂享豐年之慶也。……既享大有之利,干望降福之由,于是琴瑟擊鼓,迎迓諸神而包賽焉。”概括地說,賽戲就是為報賽神靈而演出的戲劇。[4]
目前武安儺戲中的賽戲,有一類是直接與驅儺相關的神鬼戲,如《點鬼兵》,講的是驅儺神之一白眉三郎的來歷;《吊黑虎》講的是趙公明鐵鞭鎮黑虎的故事,而趙公明也是驅儺眾神中的一位。另外還有《吊八仙》等神仙道化戲,雖然敷演的神仙故事并非與驅儺直接相關,但按照民間信仰的理解,這些神仙同樣具有護佑百姓的神力,因此也可以稱為報賽的對象。
另外還有兩類賽戲內容和驅儺沒有直接關系,一類是歷史劇,講述著名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如《巴州虎牢關》、《討荊州》等;還有一類屬于街頭滑稽劇范疇,如《大頭和尚戲柳翠》,《十棒鼓》等。
(二)強大的“聚戲”功能
前文講到的儺戲形式,有的是伴隨儺儀直接產生的,有的和儺并無直接關系。但我們把它們統稱為“儺戲”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無論是怎樣的內容,它們都是在整個儺事活動中產生的,即使是沒有鬼神情節的賽戲,也是報賽表演的一部分。武安儺戲的這種多樣性,其實展示了中原儺強大的“聚戲”功能。儺逐漸從一種巫術和祭祀儀式,演變成為表演性極強的民間的賽會活動,伴隨著驅儺表演,衍生和附會了大量的民間表演形式。除了前文提到的賽戲之外,還有諸多民間藝術形式,如花車、旱船、竹馬、彩幃、舞獅、舞龍、霸王鞭等等。
這些表演并非隨意雜亂地進行,而是伴隨著驅儺的程序,在特定的環節進行的。例如在“擺道子”環節中,這些節目的表演者要按順序依次擺開。在“擺道子”和“南臺抽腸”環節之間,有竹馬、旱船等近一小時的表演。在“南臺抽腸”之后,又有近兩小時的表演。
如果說嚴肅的儺儀表現了人們對神鬼的敬畏,那么充滿現世歡樂的儺戲和各種民間藝術,則體現了人們對自身價值的關注、對現實生活的熱情。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能夠更容易地理解為什么在巫風消逝的中原地帶,還會有武安儺這樣一個完整盛大的儺文化存在。通過一場盛大的儀式和表演,表達了民眾與天地自然和諧相處、祈求美好生活的強烈愿望。因此我們今天在保護和弘揚這一珍貴的非物質為文化遺產時,要對它的文化價值有著更加深入的理解。本文希望能夠成為拋磚引玉之作。
[1]葉舒憲.中國神話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42.
[2]馬計斌.女媧民間信仰的世俗化演變及其文化意義[A].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21-24.
[3]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2.
[4]張振南.樂劇與賽.載1984年原晉東南地區文化局編《戲曲資料》: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