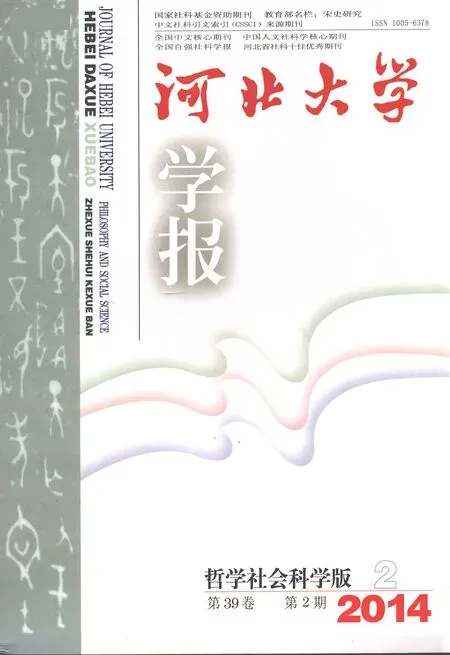語言接觸影響漢語詞綴的方式
趙艷平
(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保定學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任何一種語言在發展演變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和其他語言發生接觸,語言接觸常常會導致語言間的借用和影響,因而一個語言現象的發展演變可能是自身的內部演變,也可能是語言接觸影響下的外部演變。關于這一點,江藍生曾經指出:“我們考察和分析歷史語言現象時,應該跳出歷史比較法的框框,從語言滲透、語言融合的角度去把握,也就是說,語言不是一種同質系統,共時語言中的有些差異不一定都是其自身單線條歷時層次的反映,而可能是由于語言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造成的”[1]。語言接觸分為直接接觸和間接接觸兩種。直接接觸指個人或語言集團地理上相鄰或同處于一個社會環境,是一種面對面的接觸。間接接觸指不同的個人或語言集團在空間上有地理分隔,因而間接接觸也被稱作“遠距離的”或“跨地緣的”,這種接觸主要以文字和書面文本為媒介。本文討論的語言接觸主要是指間接語言接觸。漢語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和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語言發生接觸,在構詞法方面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其中印歐語系的語言尤其是英語對漢語影響最大,引發的漢語詞綴變化方式主要有三種。
一、詞綴用法從偶發罕見到頻繁使用
漢語里有的詞根語素由于語義虛化產生了詞綴用法,但這種用法發展緩慢,長期處于萌芽狀態,只是偶發罕見,在語言接觸的刺激下才突發為頻繁使用。如:“惡化”“簡化”的“化”,呂叔湘、朱德熙認為“化”是翻譯而來,王力也曾指出“五四運動以后,新興的動詞詞尾有‘化’字。這個詞尾大致等于英語的-ize,多數使名詞轉化為動詞,也有少數是使形容詞轉化的”[2]364,丁聲樹、任學良也都認為“化”由翻譯而來。
我們認為,“化”的詞綴用法不是翻譯而來。它的產生、萌芽是漢語自身內部發展演化的結果。“化”的初文為“匕”,本意指人的形體發生了變化,后隨著詞義的引申,“化”的語義從單指人的變化泛化到一切事物的變化。上古時期的“化”既有動詞用法,也有名詞用法,動詞“化”既可以單用,還可以帶賓語[3]。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時期出現了“X化”的萌芽,如:
(1)言卦爻陰、陽迭相推蕩,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圣人所以觀象而系辭,眾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周易·卷七·系辭上傳》)
(2)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莊子·知北游》)
(3)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漢書·董仲書傳》)
(4)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淮南子·原道》)
(5)鹖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脩諸己,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之於末。”(《鹖冠子·度萬》)
(6)震鱗漦于夏庭兮,帀三正而滅姬;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漢書·敘傳》
(7)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中多仆累、蒲盧。(《山海經·中山經》)
上古時期,“X化”結構雖已出現,但“X化”中的“X”主要是類名,和宗教文化密切相關,“化”有實在意義,“X化”屬于復合結構,還不是由詞綴構成的派生結構。到了清代中前期,“X”由類名泛化到形容詞,“化”的派生結構始具雛形。當“X”泛化到抽象名詞時,“化”具備了“X”屬性的作用,“X化”轉變為派生結構。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化”綴用法是漢語內部自身演變的結果,但其從上古時期出現萌芽直至清代前中期初具雛形,一直處于緩慢的發展狀態,而且使用頻率很低,清代前中期,“化”綴用法尚屬罕見偶發①我們選取了周朝的《山海經》、春秋戰國的《尚書》、漢代的《漢書》、魏晉六朝的《抱樸子》、隋唐五代的《北齊書》、宋代的《資治通鑒》、元明的《水滸傳》、清代的《兒女英雄傳》作為語料進行調查,雖然是抽樣調查,但也可以觀察“化”的大致用法。清代“化”主要用作動詞,名詞用法不占主流,《資治通鑒》名詞數量大,是因為包含了人名和地名用字,如“宇文化及”出現24次,單用“化及”就有86次之多。由此可見,“X化”用法雖出現較早,但一直處于緩慢的發展狀態。。五四運動以后,“化”綴用法一時大量使用,這確實和語言翻譯有關,誠如王力、朱德熙、呂叔湘等各位先生所言。“化”綴突變,在當時構造了很多漢語新詞,如“簡化”“惡化”“工業化”“機械化”“歐化”“庸俗化”“具體化”等,“同化”“退化”“文明化”等詞語使用頻率頗高。
綜上所述,“化”綴用法是語言內部演變和外部刺激雙重作用的結果。萌芽、發展是漢語內部自身演化的結果,大量運用則和語言接觸密不可分。萌芽是內因發展的結果,即使沒有外在因素,“化”已形成派生構詞的用法,而它的大量使用則是外因作用下的產物,語言接觸直接刺激了“化”綴的使用頻率,推動“化”綴構詞法的流行并由其構造出大量新詞。
二、詞綴的使用范圍擴大
語言接觸對詞綴影響的第二種方式是擴大了原有詞綴的使用范圍,即漢語里某個語素已有詞綴用法,由于語言接觸,該語素的詞綴用法不再局限于原有范圍,而是移植了語言接觸方的詞綴用法,從而引起其使用范圍的擴大。如漢語詞綴“們”②關于“們”的來源,目前主要有三種說法:“輩”字說(呂叔湘)、“物”字說(江藍生)、“門”字說(太田辰夫)。。近代漢語的早期白話中,“們”用在人稱代詞“我”“你”“他”之后,用來指人表示復數,這是漢語的表達習慣。五四運動前后,由于受到英語影響,“們”的使用發生了兩點變化。一是指物的第三人稱代詞加“們”出現了復數形式,二是出現了普通名詞后用“們”表復數的現象。這兩點變化導致“們”使用范圍的擴大。
(一)指物的第三人稱代詞出現復數形式
現代漢語里,“他”用來指人,書面上一般指男性,在性別不明或沒有必要區分時,“他”泛指男性和女性。這和五四以前的用法有所不同,五四運動前,“他”③第三人稱代詞“他”產生于唐代,郭錫良認為唐代最沒有疑義的例子是高適《漁歌父》中的“他”。(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鉤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不僅用來兼指男性、女性,還可以指代一切事物。如:
(8)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個皮殼了,又須識得他里面骨髓方好。(《朱子語類·卷一一六》)
(9)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里,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他”用來指人,有復數形式“他們”。用來指物,則只有“他”而沒有“他們”,“他”既可以表示單數,也可以表示復數。我們舉兩個“他”表示復數的指物用例:
(10)這些彩緞,全靠顏色,顏色好時,頭二兩一匹還有便宜;而今斑斑點點,那個要他?(《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
(11)連孔子都說,“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也可見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害臊的才拿他混比呢。(《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例(10)“他”指前文的“這些彩緞”,例(11)“他”指上文的“松柏”這兩件東西,都是指物的復數用法。我們考察了國家語委古代漢語語料庫,發現“他們”共有1948條用例,這1948例全部用于指人,沒有一例用來指物。賀陽曾對舊白話《水滸全傳》《西游記》《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8部作品全文進行考察,其中出現的1828處“他們”也都是用來指人而非指物[4]78-82,這和我們的觀察結果一致。英語中,所指事物是單數時用“it”,所指事物為復數時用“they”(主格)、“them”(賓格)。五四運動后,漢語在語言接觸中受英語的影響,指物的第三人稱代詞“他”出現了復數形式。關于這一點,王力曾指出“本來,指物的‘他’(即‘它’)在漢語里是非常罕見的。至于復數形式更是絕對不用了,但是,由于吸收外國語法的緣故,在書面語言里也漸漸有‘它們’出現了,甚至出現在典范的白話文著作里。”[2]319據我們對國家語委語料庫的檢索結果,指物的第三人稱代詞“他”出現復數形式確是在這一時期,但王力先生提到的指物的“它們”出現在五四以后,和我們的考察結果不同。我們在宋代的《朱子語類》檢索到4例“它們”。又在北京大學CCL語料庫中發現了“它們”在宋代的144個用例,而且“它們”多用來指物,偶用指人,如:
(12)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卻覺得意思舒暢。不知它們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
(《朱子語類》卷一〇七)
因此我們猜測“他們”出現的原因可能有兩種,一是受“它們”影響,由“它們”類推出“他們”,因為“他”和“它”有指物的共同用法;二是由于語言接觸受英語影響。從“他們”出現的時間點上分析,第一種猜測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它們”從宋代出現一直到五四前,近800年的時間并沒有影響到“他們”指物用法的出現,另外,長期以來,“他”和“它們”在指物的這一相同用法上,“他”處于強勢,我們在檢索過程中,發現宋代以后“它們”銷聲匿跡,指物的第三人稱代詞一直用“他”,“他”既指單數,也指復數。五四之后,“他們”新生,“它們”復活,而且使用數量增多,而這正是漢語和英語接觸較多的一個時期,因此我們推測,“他們”、“它們”用來指物是語言接觸的結果,二者是一組異形詞。如①以下幾例轉引自賀陽《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版)。:
(13)炸藥和雷電傷人更是可怕,利用他們便得了開山、治病及種種工業上的效用。(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號)
(14)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魯迅《秋夜》,《語絲》1923年第3期。)
(15)這種工房沒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門一樣。(夏衍《包身工》,1936年)
現代漢語里,“他們”“它們”已經有了比較嚴格的分工,“他們”指人,“它們”指物。在同時指人和物時,用“他們”而不用“他(它)們”。《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對兩個詞的解釋是:“他們,人稱代詞,稱自己和對方以外的若干人”;“它們,人稱代詞,稱不止一個的事物”[5]1252。
(二)指物名詞出現“名+們”的復數形式
漢語史上,“們”曾有過加在指物名詞后表示復數的用法,元朝的《蒙古秘史》和明代的《老乞大》《樸通事》中有不少指物名詞加“們”(每)的用例,據蔣紹愚、曹廣順,“們”的這種用法是漢語對譯蒙古語的結果,“中古蒙古語常見的名詞復數附加成分有-d、-s、-n等,這些附加成分在元代白話碑和《蒙古秘史》里通常對譯成‘每’。中古蒙古語附加成分可以用于所有的名詞和代詞之后,并不限于指人的體詞性成分。因此可以肯定,元代漢語‘們∕每’表示無生名詞復數的這種用法,雖然是漢語內部產生的,但動因卻是來自中古蒙古語的影響。”[6]489孫錫信也認為,《元朝秘史》是蒙文的漢譯本,因而保留了許多蒙古語的語法特點,因為《元朝秘史》是元代的官修史書,明代的《老乞大》《樸通事》可能受其影響,明朝中葉以后這種用法逐漸消失。因此,孫錫信認為,“們”用在指物名詞后表示復數形式,不是漢語的語法習慣[7]。英語等印歐語系語言中,名詞有復數用法,不論是指人還是指物。五四以后,漢民族共同語里的“們”新增了加在指物名詞后的用法,我們認為,這應該是受語言接觸的影響,如:
(16)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著,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著。(魯迅《雪》1925年11期)
(17)星星們——在他眼中——好似比他還著急,你碰我,我碰你的,在黑夜中亂動。(老舍《駱駝祥子》)
三、詞根語素增加類詞綴① 關于漢語類(準)詞綴,學界有兩種看法,一是把它看做詞綴的一種,二是把它與詞根、詞綴并列分立出來。本文參照了第一種看法。的新義項
語言接觸過程中,一個詞根語素使用原有字形,直接借用源頭語語素的詞綴用法,導致漢語詞根語素增加了類詞綴的用法,我們把這種語言現象叫“義項的移植”[8]323-324。具體可以表述為:A語素(源頭語,外來語)、B語素(目標語,漢語),A語素有A1、A2兩個義項,B語素有B1一個義項,且A1=B1,那么在語言接觸過程中,A2的語素義很可能會被直接加在B語素上,使B語素產生一個新義項B2,并且A2=B2,如漢語語素“—門”。
與《現漢》第5版相比,第6版《現漢》在“門”釋義中增加了新義項“⑩借指公眾關注的消極事件:賄賂門、考試門”。觀察“門”新增的這個義項,和前面的幾個義項并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引申關系。事實上,“門”新義項的增加和語言接觸有關,是受英語“-gate”影響,1972年美國歷史上發生了有名的“水門事件”,也叫“水門丑聞”。“水門事件”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聞之一,對美國本國歷史以及整個國際新聞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水門事件”的巨大影響,后來“Watergate”逐漸代替了“The Watergate Affair”(或“The Watergate Scandal”),因為只要提到“水門”,人們就很容易聯想到“水門事件”,“水門”和“水門事件”的這種密切關系,使“水門”發展出“指代與水門事件類似的政治丑聞”的用法,在后來的新聞報道中更有記者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別出心裁地把“Watergate”中的“gate”抽取出來,作為獨立的構詞語素使用,意指“國家領導人遭遇政治危機或政治丑聞”,如:Reagan's Iran-gate(里根伊朗門)、Clinton's Zip-gate(克林頓拉鏈門)等。后來“-gate”的意義開始泛化,從政治事件擴大到影響較大的負面事件。英語語素“門(-gate)”的語義發展過程可以表述為:語音形式(“Watergate”中的“門”)→與“水門事件類似的政治丑聞”(獨立為構詞語素“-gate”)→影響較大的負面事件。
我們在翻譯英語時,把發生在國外的“影響較大的負面事件”的“-gate”意譯成“門”,漢語語素“門”也因此新生出一種“公眾關注的消極事件”的義項,這個用法是語言接觸的產物,不是漢語詞“門”獨立演化的結果。當代漢語中,語素“—門”在這個義項下又構造出很多新詞,如:“解說門”“艷照門”“奶粉門”“假捐門”“感謝門”“獸獸門”“斗富門”等等,從語法功能上來看,“—門”是不成詞語素,構詞時位置固定、能產性強、標示詞性(名詞),具備了詞綴的很多特征,但從語義角度來看,它具備的是詞根特征,語義只是泛化還沒有虛化,所以我們把它定性為類詞綴。
[1]江藍生.從語言滲透看漢語比擬式的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1999(4):169-179.
[2]王力.漢語史稿[M].新2版.北京:中華書局,2004.
[3]朱慶祥,方梅.現代漢語“化”綴的演變及其結構來源[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1(2):153-155.
[4]賀陽.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5]現代漢語詞典[Z].第6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6]蔣紹愚,曹廣順.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7]孫錫信.元代指物名詞后加“們(每)”的由來[J].中國語文,1990(4):302-303.
[8]朱冠明.移植:佛經翻譯影響漢語詞匯的一種方式[C]//遇笑容,曹廣順,祖生利.漢語史中的語言接觸問題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