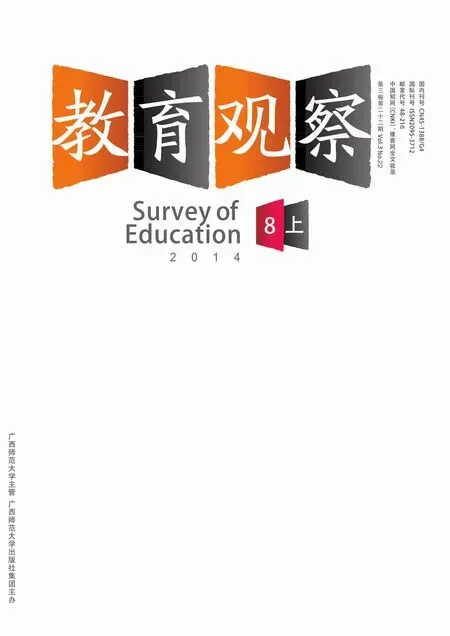以媒介融合為導向的新聞傳播教育改革途徑
肖 飛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新聞傳播系,福建廈門,363105)
一如傳統媒體行業在新媒體時代里進行轉型那樣,新聞傳播教育在上述趨勢下進行的改革也持續了多年。值得注意的是,當這樣的改革持續到今天,新媒體本身為我們昭示了越來越明晰的“媒體融合”特征:在行業里,報紙媒體開始組建視頻部門,廣播電視媒體開始積極尋求與移動互聯平臺的合作;在傳播本質上,“圖文音畫”等傳播符號已經開始被整合在一條新聞內容當中。
當我們借助最為簡潔的拉斯韋爾傳播模式對上述趨勢進行分析的時候,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趨勢中,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本質和內涵其實并沒有發生改變:一方面,新聞依舊是以“及時、顯著、接近”這樣的要素構成價值的傳播內容;另一方面,它依舊要進入社會化的傳播過程,依舊要重視受眾反映、重視社會效應。真正發生了改變并仍舊處在改變之中的,其實是受眾的媒介接觸習慣、閱讀習慣,以及與之契合和匹配的傳播渠道和傳播符號。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并不是根本性和革命性的,相反,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途徑,必須順應新媒體發展和新聞傳播教育雙重的內在屬性。
一、應根據本身的學科現狀,選擇需要被保留的課程與教學內容
這是改革開始的第一步。需要被保留的通常包括傳播學、新聞學、新聞采寫等課程或與之相關的教學內容。上述內容實際上涉及構成傳媒行業最為根本的元素,即傳播媒介和傳播符號。保留這些課程既要體現上述元素質的飛躍,又要對上述元素重新整合與構建。美國南加大新聞系曾經對“新聞寫作”根據紙質、廣電和網絡媒體分別開設,形成了“紙質媒體新聞寫作”“廣電媒體新聞寫作”和“網絡媒體新聞寫作”三門平行的課程。但在隨后的教學實踐中發現,這樣的拆分并不成功,除了教學內容大量重復之外,有學者將其中更為重要的原因歸結為:針對三種媒體分開進行的教學實踐與融合新聞實質相違背[1]。
更多院校的教育者采用了更加貼合“媒介融合”本質的做法:在優勢課程的基礎上增加媒介融合的相關課程和內容。比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采取四學期制和五學期制的輪流教學課程,將媒介融合的理念和應用技術滲透于相關課程當中;復旦新聞學院則采用獨立教學的模式,增加“融合報道”和“融合采編技術”這兩門課程[2]。
二、應根據傳媒行業對專業人才的新需求,對現有課程體系進行增補
在專業上,不管是新聞學還是廣播電視新聞學都相對集中地針對報紙以及廣播電視這樣單一的媒體進行人才培養。但就業界趨勢而言,包括傳統互聯網在內,都在進行融合性質的跨媒體整合。于是,有了在本質上超越早期“手機報”的“報紙手機端”,有了手機電視和門戶網站的手機端。這些趨勢性的媒介形態,無不寄托了傳統媒體突破困局實現拓展的希望。這時候,它們對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傾向于能夠駕馭多媒體平臺和整合全媒體符號的媒介融合人才。
以這一需求為培養目標,新聞傳播教育在優勢課程體系上增加了新媒體教育的內容,這些內容一方面可以突破原有的新聞傳播教育以單一媒體平臺作為培養目標的專業體系設置,更為重要的是,它在專業教育的本質上做到了跨媒體平臺和跨傳播符號的“全媒體融合傳播”。“媒介融合概論”“新媒體技術基礎”“手機傳播”“多媒體制作與編輯”等課程,開始作為傳播學相關專業共同學習的課程。同時在已有的針對傳統單一媒體進行專業培養的課程內加入了媒介融合的相關內容,比如有些院校開始將“網絡新聞寫作”“新聞網頁設計與編輯”等課程加入“新聞寫作”及“新聞編輯”等傳統課程中。
三、建設新聞傳播教育培養新模式
基于“融合”的命題開展新聞傳播教育對于學界和業界都尚且處于探索階段,在關于培養模式更大的范疇里,之前以各種辦法將業界流程化或者規范化的操作范式引入教學體系的培養模式在今天難以為繼。相反,當學界和業界都各自處于媒介融合的原點上的時候,雙方更需要發揮各自的優勢,以新的方式進行合作打破傳統的新聞傳播教育培養模式。
(一)“聯合+委托”模式
在人才培養和科研兩個層面,這個模式都可以發揮作用。在人才培養上,一方面,由專業的師資隊伍聯合企業的高級專業人才整合具有較高教學、實踐和研究水平的師資團隊,聯合對專業人才進行培養;另一方面,鑒于媒介融合人才本身的缺乏,企業或其他單位也可以將他們需要進行專業培養的相關人才,在一定的協議框架下,由高校利用其資源優勢,組織類似于管理學中的EDP或者EMBA,對其進行培養。事實上,日本的一些大學和企業就建立了這種合作,并稱其為“委托研究員制度”[3],即是指企業的技術人員到高校接受指導,把握最新的研究動態,同時也能夠讓科研與切實的市場需求相結合。
此外,相對于企業來說,高校在某些方面具有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數據調查和數據分析等需使用較多人力資源和要有較高專業要求的領域。因此企業在與高校進行聯合科研之外,可以開展更為深入的委托科研,就像橫向課題一樣,在委托科研的框架下,企業或政府部門將某類型的科研項目委托給高校,并提供相關的研究經費。由此而產生的科研成果歸雙方共有,由科研成果而帶來的經濟效益根據協議進行分配。這相對于橫向課題更具有持續性,是校企關聯更為緊密的一種產學研合作模式。
(二)組建研究聯盟
相對于企業或者政府機構來說,高校在研究領域的資源整合方面更具優勢。我們可以利用現有的師資團隊進行相關研究領域的跨專業甚至是跨院系、跨高校的學術資源整合,服務于相關行業的某一類需求。比如,整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符號學等學科的學術團隊,進行針對移動互聯媒介受眾的閱讀習慣、媒介接觸習慣甚至是消費習慣進行分析,定期發布研究報告;或者接受企業或政府機構的相關委托,進行更具針對性的受眾研究。德國知名的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正是整合了眾多領域的頂尖科學人才,具備了雄厚的研發科技積累和高水平的科研隊伍。合作方通過研究所的多學科合作,可直接、迅速地得到為其“量身定做”的解決方案和科研成果。除了創建學界的學術聯盟之外,業界的資深人才資源同樣可以聚合,形成業界聯盟。“One Show”廣告大賽相關方面就與國內很多高校的相關專業有過多年的合作。以上述廣告大賽的業界資源為依托,實現業界聯盟是可行的。
中肯地說,國內很多高校就現階段而言,即便采用研究聯盟的模式,也暫時難以達到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的規模和研究能力。但從現實出發,在需求極為旺盛的某些領域(輿論分析和受眾研究等),只要高校能夠依托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或業界帶頭人,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研究聯盟是可行的。
(三)跨行業多元聯合
就媒介融合專門人才培養整個過程而言,將學術隊伍、研究資源和企業需求的整合主體放在高校身上,只能在某些領域發揮其作用,而且對高校的學術和研究號召力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事實上,在上述過程中,可以有更多的主體參與,令研究力量和行業需求更為順暢地進行整合。韓國采用了一種可以借鑒的模式,即“政府—高校—企業”的多元聯合模式:政府劃出一定的區域并實施優惠政策,以大學作為基地、企業作為會員,集資建立中心。中心由大學和會員單位的研究實驗樓組成,雙方人員共享中心的實驗設備。這種緊密的合作方式充分利用了各自的優勢和資源,實現了效用的最大化。
上述模式的借鑒意義并不在于資金、設備等有形資源的整合,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具備相應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也具有資源整合的需求。比如,不少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設“移動城市”的設想,推動電信網、互聯網和有線電視網的三網融合。在這個愿景下,企業、政府、民眾其實都是受益的個體,問題在于:這種融合應該如何進行?在制度層面、技術層面、應用與服務層面,有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課題。在類似這樣的課題里,我們可以聯合政府相關機構,起一個平臺的作用,以政府研究課題的形式,前端整合企業需求,后端整合研究力量。
[1] 鄧建國.管窺美國新聞傳播院校媒介融合課程改革中的經驗與教訓[J].新聞大學,2009(1).
[2] 鄒軍.新媒體時代新聞教育變革的邏輯與路徑[J].當代傳播,2011(6).
[3] 祝東偉.國外產學研合作典型模式的研究與啟示[J].中國科技產業,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