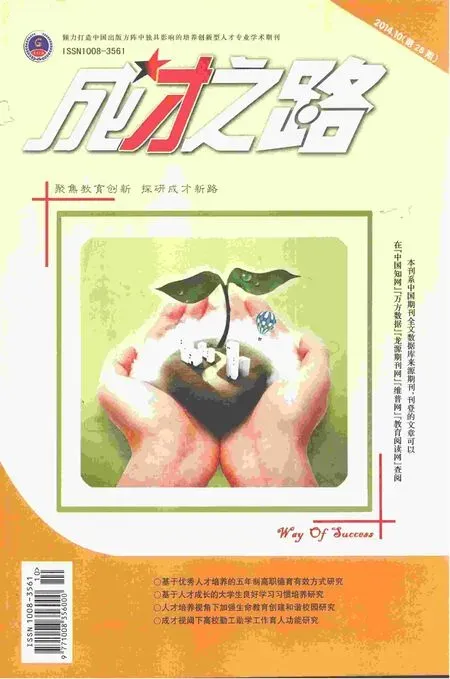初中英語語言變體與運用的得體性探析
仲雪
學習英語同學習漢語一樣,都是為了運用。有的中國人雖然學習了本民族語言,掌握了本民族語言的使用規則,但說話往往不受人歡迎,原因是說話不恰當、不得體,于是被人稱為“不會說話的人”。學習英語同樣存在這個問題。由于是學習其他民族語言,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突出。有些人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單詞、短語、語法知識,并能讀會寫了,但不能恰當、得體地運用英語進行交際。因為掌握了一定英語知識和運用英語語言進行交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掌握了一定的英語知識能為運用英語進行交際打下一定的基礎,但能不能恰當、得體地運用英語,還要看運用者會不會使用英語語言變體(variety)。如果對英語語言變體沒有掌握或掌握得不好,照樣達不到恰當、得體地運用英語進行交際的目的。
任何一種人類語言,都有各種變體,英語當然也不例外。漢語中所說的“見什么人說什么話”也是這個意思。所謂變體,是指在某種語言交際場合,某些人之間在某個區域所使用的某種特定的語言形式,如口語、書面語、方言等。英語語言的變體可以依此標準分門別類,如按不同的學科領域劃分出科技體英語、法律體英語、文學體英語、公文體英語等;又如按不同的語言交際場合而區別正式和非正式英語變體。各類語言變體的文體特征各異,不言而喻,科技體與法律體英語大相徑庭;在政府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所使用的文體與親朋摯友之間茶余飯后海闊天空的文體差異顯而易見。不同的交際場合,應使用不同的語言變體。“適當”“得體”兩個詞至關重要。要滿足語言交際的需要,其衡量標準并非言語的華麗、文體的高雅、詞匯的豐富,關鍵是“適當”“得體”。文體的選擇應視具體的交際需要而定,如科技文章須嚴謹、簡練、準確,而熟人之間的日常會話則隨便、文句松散、不拘一格。在語言交際中,如文體運用欠妥,不但達不到預期的交際目的,而且會適得其反。此類笑話,屢見不鮮,尤其源自那些英語作為非母語的使用者。如,有一位學者參加一次為外籍專家餞行的茶話會,會場氣氛輕松和諧,師生交談異常隨便,如同“侃大山”。這時,突然有一位學生起立發言,開場白以“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們、先生們),頓時場上爆出一陣哄笑聲。需要指出一點的是,這位學生詞正腔圓,一本正經,嚴肅認真,并非幽默詼諧而有意為會場平添一分“樂趣”。他使用的正式文體與場上的氣氛格格不入,因而顯得不恰當、不得體,只能引來一陣哄笑聲,其中不乏嘲笑聲。
下面再舉一個常被人引用的故事:一個年輕的姑娘剛上大學,放假回家,教她祖母吮雞蛋,說道:
“Take an egg and make a perforation in the base and a corresponding one in the apex.Then apply the lips to the aperture ,and by forcibly inhaling the breath the shell is entirely discharged of its contents.”(“取出雞蛋一只,在其底部穿鑿一孔,并在其頂端相應再鑿一孔。然后,將唇部置于孔徑處,借助強有力的吸氣,使蛋殼內部容納物全部排空。”)
祖母聽了,只好搖頭,嘆道:“When I was a girl they made a hole in each end and sucked。”(“我小時候,人們只在雞蛋的兩頭兒一邊兒打一個眼兒,用嘴去吸。”)
從以上例句不難看出,語言使用恰當、得體十分重要。Hymes在論述交際能力時提出了四種能力:能辨別和組織合乎語法的句子、能恰當得體地使用語言、能判斷哪些語言形式可接受、能根據語言形式的特征評估運用語言的風格。語言使用恰當得體,是指人在什么場合、什么時候、對什么人該說什么話。這一點在外語教學中往往被忽視。例如,有些青年教師業務水平不錯,然而他們的課堂用語,學生反映聽不懂。我們并不懷疑他們所講的英語的正確性,不過他們忽略了應針對學生的特點而使用適當的語言變體。要達到交際目的,首先應將信息傳遞給受話者,而不在于所使用的語言多么“elegant”。語言知識的掌握較易,而語言的活用則難。這一點,在英語教學領域辛勤耕耘的園丁們肯定會深有體會。有一位英國文豪留下一句名言:“The right word in the right place.”(在適當的位置選用適當的詞。)這句話現已成為眾所周知的寫作秘訣。此言與我們正在談論的得體性并無二致。可是,這一點在傳統教學法中尤其是應試教育中則往往被忽略。
傳統教學法強調語言的正確性,即注重語法知識的傳授,而忽視語言的實際應用。似乎語言規則掌握之后,語言運用則不在話下。而交際法則認為兩者不能等同,應特別強調語言使用的恰當性和得體性。這一觀點在外語教學界廣為接受,在此不再贅述。
(江蘇省新沂市高流初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