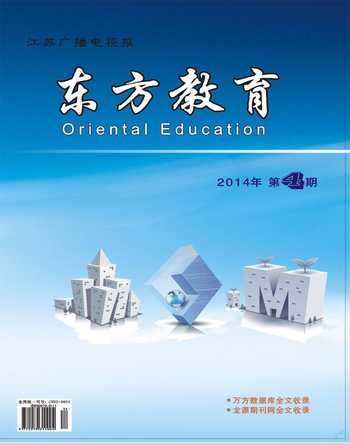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下完善我國環境資源立法
田亞鵬
【摘要】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世界性的話語,成為當代環境立法的主題和核心內容。我國環境立法面臨重大整改,其中也應貫徹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筆者在文中首先對可持續發展做一些簡要介紹,其次對我國環境資源法的整改提出一些想法。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環境立法;完善
一、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與我國的環境資源立法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即“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①(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編著:《我們共同的未來》,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頁)這標志著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成熟。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環境與發展大會把可持續發展作為未來共同發展的戰略,得到了與會各國政府的贊同。大會通過的《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第一次把可持續發展由理論和概念推向行動。
1994年中國制定《中國的二十一世紀議程》,從此,正式開始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1999年3月13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人口資源工作座談會”上鄭重指出:“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和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 ②(《中國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可以看出,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中,環境問題已經列入基本國策。
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志是資源的永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是實現“代際平等”。可持續發展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可持續發展要求人們改變傳統的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人類對于自然的態度,在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必須注重對環境資源的保護。因此,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以法律作保障。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環境與資源保護立法已經從無到有,積少成多,由偏到全,逐步建立起了一個由污染防治、生態保護、資源管理、防災減災等法律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規、政府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等構成的比較完整的可持續發展法律體系,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為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中我國環境與資源立法存在的問題
雖然我國已經基本上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以《環境保護法》為基本法,以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為主要內容和以我國締結參加的有關國際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條約、公約。協定為輔的較為完備的環境與資源法的法律體系,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主體為了達到個人的經濟利益,往往忽視社會效益和環境保護,加之我國環境和資源的立法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這就使我國的環境與資源法的法律體系面臨嚴重的挑戰。
(一)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尚未成為我國環境與資源立法的指導思想:
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發展的必由之路,可持續發展本身就包含著有序、公平、公正之義,但實現有序、公平、公正就必須由法律保障,因此,必須制定環境資源立法。由于我國現行的環境立法許多制定于80年代,所以在指導思想上沒有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重要的立法目的,例如立法目的及法律內容缺乏全面反映生態規律的要求,尚未建立起有利于環境與發展相結合的綜合決策機制和經濟社會運行機制。由此,對自然資源開發中的生態環境保護缺乏具體的規定,致使這些自然資源的法律難以適應生態的環境保護的需要。這就導致出現了重環境污染防治、輕自然資源保護的思想。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與完善的今天,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后,環境資源問題出現了新發展,原來集中于城市的污染問題正在向農村蔓延,生態惡化進一步嚴重,污染問題防不勝防。
(二)我國的環境與資源立法不能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1、環境立法中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忽視了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我國于1992年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立法原理上,環境立法仍受計劃經濟體制觀念的影響。在原理指導、原則確立、制度設計、體系構建和法律實施等方面,強調并習慣于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立法領域,基本原則和制度都是建立在行政管制基礎上的,依賴行政實施,具有行政制度的性質。資源立法領域亦貫穿著行政主導的指導思想,法律規范的安排與實施都是圍繞著政府供給與行政分配而進行,市場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很少進入法律制度的規定中。不適當的行政干預方式嚴重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和資源產權制度的建立以及資源市場的培育。③(《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中國環境出版社,1994年版,P107-108)從而使對于符合市場經濟和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市場機制在自然資源管理中的基本性作用原則、資源有償使用和資源利用與國家產業政策相協調等,我國現行各法或未反映,或反映不多、不明確。
2、我國現行環境立法不足以體現“預防原則”,不能最大程度的推動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我國現行環境立法中確立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原則,其中“預防”要求主要是以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④(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六條: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作為基本支柱。但具體的講是以設施、項目控制為方法以為滿足“達標排放”要求。這樣的“預防為主”實質上是少排放的要求,具有事后抑制性質,尚不具有體現少產生或不產生污染物的要求的事前抑制性質。
目前執行的超標排污收費制度只是對超過濃度標準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費,這種超標排污收費制度實質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以資源分配、無償使用力主要特征的產品經濟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具體體現。排污者只要不超過污染物排放標準,就可以無償使用環境納污能力資源,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這并不完全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的要求,
(三)我國環境在制定各種立法規定時未能綜合考慮,缺乏協調和配合,不能合理的保護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目前我國有關環境管理體制的立法分散在各種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中,由于授權不一導致的立法不集中使各種立法之間難免出現一些交叉和矛盾。例如,《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國家環境保護局和地方各級環境保護局是環境保護工作的主管部門,統管全國或地方的自然資源保護工作和污染防治控制工作;然而在各自然資源的法律、法規中只規定了各自然資源專管部門的職責和權限,卻未規定環保主管部門的權限。這種立法傾向顯然是把環保主管部門排除在自然資源保護管理部門之外,明顯與《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相沖突,從而造成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環境保護監管部門之間的權責不清。再如,根據《標準化法》的規定,國家制定的強制性標準必須執行,對違反者要處以罰款甚至追究其刑事責任;而現行環境法只要求超標排污者繳納排污費即可,并不認為超標排污系違法行為。這就直接違反了《標準化法》的規定,造成法律體系內部的不協調,還有,我國雖然已制定了各種環境區域的環境噪聲標準,但并未將其列入《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中;《水污染防治法》將水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制定權劃給各級政府的環保行政主管部門,這些做法的結果使得大量的相關法規散見于國務院和各級政府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中,實質上是法出多門,重規章而不重法,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環境法律體系結構上的一個缺陷。由于在立法時未能綜合考慮,使得法律的權威性和法律的執行和遵守受到嚴重的影響。從而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時候很難準確的做到“有法可依”,造成一部分環境資源無法受到良好、合理的法律保護。
(四)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缺乏與自然資源法體系的融合,不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
《環境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本法所稱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這說明我國的環境保護應相應地包括至少以下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環境污染與其他公害的防治,其二是自然資源的保護。因此,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實際上應當是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基本法,它在內容上應集環境保護基本法與自然資源基本法的內容于一身。對這兩部分內容,《環境保護法》都應予以詳盡的規定。但在具體規定上卻著重突出了環境和其他公害的污染防治,對自然資源保護的內容則作了較大程度的保留。這與其理論上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基本法地位無疑是極不相稱的。
由于環境由環境因素組成,而環境因素是具有生態功能聯系的自然資源,因此,環境的保護與自然資源的保護息息相關。這種息息相關性不僅要求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存儲、運輸和保護滿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物質和能量需求、還要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觀的要求,考慮當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態需求;不僅要求環境保護的整體化,還要求環境保護的具體化,即要把環境保護的整體化要求整和到各自然資源的保護中去,而目前的環保與自然資源立法由于協調性不強,因此很難全面地體現著兩方面的要求,不利于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恢復開發、利用、保護、治理、與改善的可持續目標的實現。
三、以可持續發展觀來完善我國環境立法
為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國現有的環境與資源法律、法規必須進行修改和完善,以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
(一)將可持續發展的立法理念貫穿于環境資源立法的始終。
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相協調原則是當代環境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則,它不僅反映了當代環境法的實質和體現了當代環境法的價值取向,同時也符合當代環境法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國的環境資源立法應當通過對立法目的和立法指導思想的規定以及基本實施途徑的設計,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體現出來,使之定性化、具體化。我們應該把全面相關的環境系統整體作為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法的理論基礎,以生態的整體價值為價值總原則,重新考查現有立法,并根據環境整體的可持續的標準對不符合這一標準的環境法進行調整。建立以保護自然權利原則、生態權利優先原則、人類綜合責任原則的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法。這種環境法不再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不再把自然對人類的價值作為保護的目的,而是自然的整體價值為追求目標。
為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在環境政策和環境立法上具體體現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以法律規范的形式引導人類傳統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以糾正傳統的依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費來刺激和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方式,以法律手段來鼓勵社會生產采用無污染、低污染的高新技術,以“知識經濟”的理念轉變傳統的增長方式,推行清潔生產,逐步淘汰落后的生產工藝和設備,實現少投入、多產出的生產方式,推動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進一步將市場經營觀念引入環境資源立法。
1、在法律制定中應重視發揮市場作用來推動環境與資源保護。
強調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指導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配置自然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不等于也不應該減少政府的責任和作用。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關鍵在于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把職能真正轉變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也就是說,環境管理部門應從側重項目審批轉向服務與引導,從而確立和完善資源的產權制度來協調各方利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通過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來促進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節約使用等。只有這樣才能有力的推動可再生自然資源源源不斷地被人們長遠持續利用;又能推動不可再生資源在有限存量之內,最大限度地被人們長期持續利用。
2、預防原則應當在環境資源立法中得到進一步的體現。
消除污染,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就是根本不讓污染發生。⑤[葉俊榮著《環境政策與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年P90]環境資源立法應當設定環境資源影響評估機制、市場準入制度,從源頭上控制,使污染盡少的發生。預防原則的發展,首先應從只限“少排放”的基本要求擴充、延伸到“少產生或不產生”的要求,從“無害化”發展為“減量化”的基本要求,并以清潔生產為核心內容,通過功能多樣化和配套互補的途徑,對法律原則和制度進行整體改造,消除預防制度與治理制度的差別,使各項制度都可能具備防與治的功能。只有在環境立法中進一步體現預防原則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三)制定綜合性的環境管理體制立法,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完善環境管理體制立法就應使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之間相互銜接、協調和配合。國家應把規劃、政策和決策納入到戰略環境影響評價之中,并把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整合到具體的實施行動要求之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全面清理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維護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協調性與統一性;在法律、法規和規章被頒布、修改或廢除時,要及時地以適當的方式公布,保證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透明性。同時,為了完善環境管理體制的立法,應當制定一部綜合性的環境管理體制立法,確立環境管理部門的地位、機構組成、各部門承擔的管理職能以及各部門間相互協調、配合和監督的程序等。在這種綜合性立法的基礎上,再由各部門、各地方將自己的職責具體化。這樣就形成一個具有系統性和協調一致的環境管理體制立法體系。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穩固法律的權威性,加大環境執法的力度,從根本上保證了在環境資源保護過程中有法可依的可操作性,使得環境資源得到完善的法律保護。這樣的一個立法體系是保障可持續發展戰略順利實施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
(四)進一步將有關的環境立法與資源立法融合在一起。
其實,環境與資源問題是緊密聯系的,例如,我國《環境保護法》第2條規定的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可以看出,這些本身也是資源。因此建議將環境與資源融合立法,制定《環境資源基本法》。從現行的有關環境、資源立法現狀看,林林總總,非常煩瑣。如有關的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礦產資源法、海洋資源法、草原法、野生動物、植物保護法、風景名勝保護管理法、國土規劃法、節約能源和綜合利用法、自然災害防治法、國土資源和區域開發與整治法、綜合監督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控制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氣象法、種子法、防震減災法、煤炭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節約能源促進法以及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等特殊環境保護法,等等。這些法律或規定缺乏統一、可操作性差,有時還會相互抵觸。實際上,即使是民事、刑事兩大基本立法也沒有如此多的分支與不統一。因此,本著以可持續發展觀的要求為目標將環境與自然資源進行一體化保護、開發和管理的宗旨建議制定綜合性的《環境資源法》。
參考文獻:
[1]陳泉生:《可持續發展與法律變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張帆,《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金瑞林主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
[4]杜群:《環境法與自然資源法的融合》,《法學研究》,2000年第6期。
[5]金瑞林、汪勁:《中國環境與自然資源立法若干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中國21世紀議程》(1994年3月25日國務院第16次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