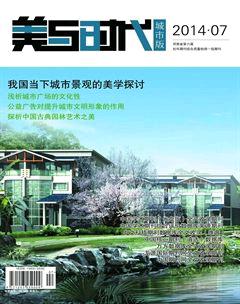族裔散居與異域視野下的“Culture Shock”
李慧研
摘要:
影片《撞車》通過多線索敘事,講述了一系列不同族裔在異域視野下發生文化沖擊的故事,通過不同人物身份對本源文化的指代,實現了多種文化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的對話。
關鍵詞:文化沖擊;身份認同;族裔散居
影片《撞車》講述了一連串由于車禍而引出的故事,影片取名為“Crash”有雙關之意的,一方面故事從一場真正的“crash”展開,另一方面,“crash”所代表的“沖撞”之意,是在指代“culture shock”。
影片中的Culture shock,從人物設計和劇情發展角度來說,有幾種不同民族的外來客和幾組不同文化背景的沖突關系。黑人混混、導演、醫生、亞洲司機和偷渡客、拉美裔的鎖匠、波斯店主、白人警察法官……這一個個角色與他們不同膚色不同職業下的身份標簽,構成了這部影片中的戲劇元素。
文化研究學者陶家俊曾在《身份認同導論》一文中將身份問題歸結為四類:個體認同、集體認同、自我認同以及社會認同[1]。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解析影片,影片中包涵的多種文化身份之間的culture shock,本質上就是社會認同的問題,放置在美國這樣一個移民國家的特殊環境中,因而帶有了明顯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傾向。
影片采取了多線索敘事的方式,不同膚色不同背景的人們天然帶有的文化沖突成為了影片推進的敘事動力。人在尋求個體認同的時候,會對于非同源文化帶有一種排他心理。同源文化的歷史積淀為這一民族賦予一種標簽化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歷史遺留的物質財富共同構成了這一民族獨有的文化身份。
這種文化身份逐漸成為一種外化的標簽,而這種標簽常常伴隨著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日常的“差異化交往”中,形成一種“思維定勢”,或者說“思維偏見”。在影片中,白人警官對黑人夫婦的盤查、白人店主與波斯人的語言沖突等等橋段都有表現,這不是個體與個體間的沖突,是一個族裔對另一族裔的思維偏見。就拿片中波斯人一家來說,因為與阿拉伯人容貌相近,讓生活在美國的他們處境艱難處處受到不公平待遇,并非是因為他們的行為不端引來的私人恩怨,而是911事件后的美國對恐怖主義人人恐慌的影響下,美國人由恐怖主義產生并向阿拉伯人拓展的仇恨情緒。美國人的這種恐懼心理,一方面來自社會緊張局勢下地暴力恐懼,另一方面來自文化融合中的未知和排他心理。集體間的文化差異與思維偏見,只能以個體的沖突來表現,影片中選擇了幾組關于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沖突,旨在表現全球化視野內的“culture shock”。
而在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上,有一個前提不能忽視,即“承認差異”。從多元文化沖擊以及文化差異角度解讀這兩個警察角色,顯然小警察的行為表明他是一個理解文化差異也尊重文化差異的人,但是在內心深處,對于他族文化還是因為未知而缺乏信任感甚至安全感,以至于他雖然邀請了黑人混混搭車,但是卻在兩人的交談中認為自己受到了侮辱,甚至由于精神過度緊張,防衛過當開槍打死了本無意傷害他的黑人混混。他身上所代表的是成長在全球化和多族裔散居背景下的新一代美國人,接受主流推崇的反歧視教育試圖從個人開始改變社會對于少數族裔的不公平待遇,而這種行為轉變的前提是他在內心中認同美國社會存在著一種社會階級,而黑人處于低于白人的下等地位,因此他在內心中,對于黑人是俯視的憐憫視角。而反觀青年警察,他是一個不能輕易用好壞界定的人,在影片中,他以一個刁難黑人夫婦的壞警察形象出場,與白人政客的妻子一樣,充當著主流社會看向少數族裔的“有色眼鏡”,他出言羞辱醫院的黑人女職員,認為他們黑人的身份為他們在“反種族歧視”的當下獲得了更多的特權,這種特權的本身就是對社會各文化族裔差異性的強調,擴大少數族裔的特權是對社會矛盾的加重。他將對政策的不滿對患病父親的擔憂統統發泄到生活中的黑人身上,以求得所謂“是白人占據美國上層社會”的心理平衡,但是當他發現車禍中被困在車內的正是前一晚被他猥褻的黑人妻子的時候,他還是盡其所能冒著生命危險將她救了出來。他的角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的美國人,種族歧視的情緒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政策面前對給予少數族裔的優待而不滿,“羞辱黑人”是對生活中不如意而且不受到主流社會保護時煩躁情緒的發泄,但是在自己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職能面前,仍然能夠做出正確的抉擇。
羅伯特·麥基在其著作《故事》中寫到,“人物真相只有當一個人在壓力之下做出選擇時才能得到揭示——壓力越大,揭示越深,該選擇便越真實地表達了人物的本性[2]”。影片中這一對警察搭檔的形象對比鮮明,危急關頭的不同選擇是對原有形象的顛覆,這種顛覆本身揭示的是他們在社會身份之下的真實“自我”。
這兩個警察在影片中都經歷的這種前后形象變化,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們都看到了兩個民族的文化差異,只不過一個在通過強化這種差異來表現自己對他族文化的尊重,而另一個卻用縮小這種差異的方式來表現自己對于沒有任何文化標簽的“生命”的尊重。
正如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一文中曾談到關于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問題,他認為社會群體的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也是“變化的”,那些隱藏在同一種族文化共同點之下的差異才構成了“真正的現在的我們”[3]。
站在美國的異域視野下對于不同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問題做歷時研究,就是影片中一環扣一環的“culture shock”的來源,其本質就是霍爾所說的那種以同源文化的差異演變形成的“真正的現實的我們”。而站在這種全球化視野的橫切面看待多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普世價值觀的真善美是任何民族文化經歷怎樣的演變無法磨滅的精神內核,這種普世價值觀可以跨越疆域、國界、膚色,獲得不同文化身份的共識。
這種普世價值觀,是影片中黑人婦女被白人青年警察救出的時候無聲的回望,是黑人母親看到兒子尸體那一刻撕心裂肺的哭喊。影片在小女孩撲向父親以小小身軀擋子彈的時刻達到情感高潮,正是因為獲得觀眾情感共鳴的,是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親情。
在影片的最后,白人警察擁抱著年老的父親,黑人警探安撫著失去小兒子的母親,父女平安,夫妻和解,雖然失手殺人的白人警察還在彷徨著不知去向何方,但是黑人混混卻在金錢利益面前選擇了釋放一車的東南亞偷渡客。在美國的異域視野下,每天都在發生著“文化沖擊”,每天也都在發生著“文化和解”,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因為文化的差異本身就無法通過任何手段去約束或改變。用人性的大愛去包容不同文化身份背后的文化差異,是導演用這樣一個復雜的沖撞故事講給世人的秘密。
【注釋】
[1]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J].外國文學,2004(03):37-38
[2]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M].周鐵東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118
[3]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群居[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影視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