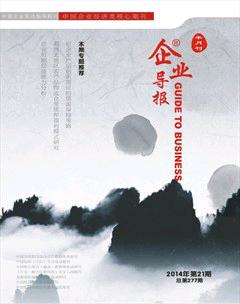關(guān)于《呼嘯山莊》中背離傳統(tǒng)的宗教意義研究
劉沖
摘? 要:本文從《呼嘯山莊》的寫作背景入手,結(jié)合寫作時(shí)代和作者本人的特征,分析了書中運(yùn)用宗教元素時(shí)背離傳統(tǒng)宗教意義的原因,并解讀了具體的運(yùn)用手法和背離內(nèi)涵。
關(guān)鍵詞:《呼嘯山莊》;傳統(tǒng)宗教意義;運(yùn)用;背離
作為維多利亞時(shí)期的代表性文學(xué)作品之一,《呼嘯山莊》雖然以獨(dú)特著稱,但在文學(xué)表現(xiàn)手法上仍體現(xiàn)出了那個(gè)時(shí)期的風(fēng)格。艾米莉在這部作品中運(yùn)用了大量的宗教元素,但這些宗教元素中有相當(dāng)一部分與其傳統(tǒng)意義產(chǎn)生了背離,在作品中營(yíng)造出了一種神性、魔性、現(xiàn)實(shí)性交錯(cuò)的獨(dú)特氛圍。這種表現(xiàn)手法與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表現(xiàn)時(shí)期有深厚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需要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呼嘯山莊》的社會(huì)宗教背景
《呼嘯山莊》成書于十九世紀(jì),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是英國(guó)人。當(dāng)時(shí)的英國(guó)正值維多利亞時(shí)代,日不落帝國(guó)的繁盛令英國(guó)的文化觀與宗教觀對(duì)全世界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原本就是英國(guó)人的艾米莉受到的影響當(dāng)然更大。
維多利亞時(shí)代的社會(huì)宗教背景可以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基督教的傳統(tǒng)思想主導(dǎo)整個(gè)歐洲超過千年,其巨大的投影始終籠罩著歐洲社會(huì),因此無論是文學(xué)還是思想,在那個(gè)時(shí)期都難免帶有濃厚的傳統(tǒng)宗教色彩。另一方面,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的工業(yè)革命已經(jīng)達(dá)到頂峰,社會(huì)的變革和發(fā)展勢(shì)在必然,新事物、新思想的巨大沖擊動(dòng)搖著人們傳統(tǒng)的宗教觀。在這種背景下,人們一方面無法完全放棄宗教思想,另一方面也要接受以科學(xué)和自然為根基的新思想,由此產(chǎn)生了用新觀點(diǎn)和新思想去詮釋舊有宗教元素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的外在體現(xiàn)就是文學(xué)作品中對(duì)傳統(tǒng)宗教寓意的背離。
社會(huì)宗教背景構(gòu)成了《呼嘯山莊》中背離傳統(tǒng)宗教意義的表現(xiàn)手法多次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艾米莉·勃朗特原本就是一位較為推崇自然主義的女性,這令她的宗教觀更容易受這種新宗教思想的影響,進(jìn)而在作品的表現(xiàn)手法上體現(xiàn)出來。另一方面,《呼嘯山莊》本身的風(fēng)格就具有較為濃厚的離奇、激進(jìn)、凄厲甚至殘酷特征,這種風(fēng)格與基督教的傳統(tǒng)宗教觀是相違背的,因此作品中對(duì)宗教元素的運(yùn)用與其傳統(tǒng)意義相背離也顯得理所當(dāng)然了。
二、《呼嘯山莊》文學(xué)表述中的宗教特征
(一) 《呼嘯山莊》對(duì)圣經(jīng)詞匯的運(yùn)用。在文學(xué)作品中運(yùn)用圣經(jīng)詞匯是西方文學(xué)非常常見的寫作手法,這一方面是因?yàn)槭ソ?jīng)的詞句在西方是耳熟能詳、家喻戶曉的,在作品中運(yùn)用這些詞匯往往能更便于讀者理解,另一方面是因?yàn)槭ソ?jīng)詞匯往往具備非常多的象征義,應(yīng)用在文學(xué)作品中往往可以作為雙關(guān)語表達(dá)出多層含義。因此,這個(gè)詞在書中的運(yùn)用非常豐富,而且每次運(yùn)用時(shí)象征的具體意象或者有一定差異,或者同時(shí)象征多種意象,這種豐富多變的運(yùn)用方式往往是普通詞匯不具備的。
(二) 《呼嘯山莊》對(duì)宗教典故的運(yùn)用。圣經(jīng)中存在著相當(dāng)多的宗教故事,這些故事往往作為典故被廣泛地應(yīng)用于各個(gè)文學(xué)作品。《呼嘯山莊》中對(duì)宗教典故的運(yùn)用往往是間接的,相比直接引用宗教故事來對(duì)主題加以渲染和展開,艾米莉·勃朗特更喜歡將小說中的故事和宗教故事隱性對(duì)比。例如,《呼嘯山莊》里,耐莉?qū)⑾K箍死蛑苯映鉃椤蔼q大”。猶大是圣經(jīng)中著名的叛徒,原本身為十二使徒之一的他出賣了耶穌,致使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在西方,將人稱作猶大可以看作一種極為惡毒和厭惡的謾罵,因此這個(gè)稱呼首先表達(dá)出了耐莉?qū)οK箍死虻膮拹骸Mㄟ^對(duì)比猶大和希斯克利夫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兩人的確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雖然這種對(duì)比來自于耐莉個(gè)人對(duì)希斯克利夫的片面主觀認(rèn)知,但對(duì)宗教典故的運(yùn)用的確深化了希斯克利夫的形象刻畫。
(三) 《呼嘯山莊》里的宗教觀體現(xiàn)。《呼嘯山莊》的故事描寫了三代人的恩怨情仇,這其中涉及多個(gè)人的出生與死亡,在那個(gè)年代的西方,無論是出生還是死亡都是與宗教分不開的。舉例來說,根據(jù)傳統(tǒng)的宗教觀念,人們?cè)诔錾鷷r(shí)需要受洗禮,死亡的葬禮、葬儀也都有嚴(yán)格的宗教規(guī)定。在維多利亞時(shí)代,雖然傳統(tǒng)宗教觀開始受到?jīng)_擊,但這些宗教方面的儀式依然有非常嚴(yán)格的社會(huì)規(guī)定,并為大多數(shù)人所遵循。《呼嘯山莊》通過對(duì)這些宗教儀式和宗教規(guī)條的描寫,隱晦地展現(xiàn)出了作者的宗教觀。
三、《呼嘯山莊》對(duì)傳統(tǒng)宗教意義的背離
(一)賦予圣經(jīng)詞匯新的象征意義。圣經(jīng)詞匯雖然具有非常多的象征意義,但在傳統(tǒng)的宗教觀念中,對(duì)這些“圣詞”的運(yùn)用比較死板,擅自為這些詞匯增添新的象征義是一種相對(duì)忌諱的行為。而在《呼嘯山莊》中,艾米莉·勃朗特不僅賦予圣經(jīng)詞匯豐富的象征意義,而且其中有多個(gè)象征意義具有異教特征,這完全背離了傳統(tǒng)的宗教觀念。以前文所述的“天堂”一詞為例,希斯克利夫在臨死前曾說過“我快到達(dá)我的天堂了,其他人的天堂毫無價(jià)值”,這里的兩個(gè)天堂具有完全不同的象征意義。后者是傳統(tǒng)宗教意義上的天堂,前者則是一種理想鄉(xiāng)的象征,從希斯克利夫的思想特征來看,他將要到達(dá)的天堂更近似于一種自由而充滿熱情的仙界,事實(shí)上,這是用英國(guó)傳統(tǒng)神話中的“仙境”來詮釋了“天堂”一詞。從這種相對(duì)離經(jīng)叛道的用法可以看出,在艾米莉·勃朗特的筆下,宗教元素已經(jīng)失去了那種必然的、不可改變的、唯一的神圣性,正如同《呼嘯山莊》本身的風(fēng)格一樣開始透露出離奇與狂野。
(二)給予宗教典故新的詮釋方法。《呼嘯山莊》中的宗教典故雖然仍保留了濃厚的傳統(tǒng)宗教寓意,但這些傳統(tǒng)的宗教意義并不再是唯一。以前文所舉的“猶大”的典故運(yùn)用來說,艾米莉·勃朗特借筆下人物之口比照了希斯克利夫和猶大,但要知道,在傳統(tǒng)宗教觀中,猶大可以說是十惡不赦之人,如果遵循這種意義,希斯克利夫在作品中理應(yīng)是個(gè)沒有任何可取之處的純粹惡人。但事實(shí)上并非如此,希斯克利夫雖然讓人恨,但也的確是個(gè)值得同情的人,艾米莉雖然讓希斯克利夫和猶大在背叛與偽善的方面重疊起來,但并沒有因此就不去抒寫他人性的光輝點(diǎn)。在希斯克利夫身上并存著愛和恨,但這愛和恨都是瘋狂的,這種混雜讓他變得偏激,成為了猶大。換言之,在艾米莉的筆下,猶大的典故不再是一種惡的象征,它更多地隱喻了人性中瘋狂、茫然、矛盾的一面,這種對(duì)宗教典故的全新闡釋令宗教元素本身也染上了人性的色彩。事實(shí)上,這與維多利亞時(shí)代人們對(duì)宗教元素的需求有很大關(guān)系,在當(dāng)時(shí)的人們看來,宗教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新時(shí)代里對(duì)人性、對(duì)自然、對(duì)科學(xué)的需求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迫切的愿望下,宗教元素開始與人性、自然、科學(xué)融合在一起。《呼嘯山莊》中背離傳統(tǒng)宗教意義,讓宗教典故染上更多的人性可以說也是這種愿望的一種體現(xiàn)。
(三)體現(xiàn)新興的宗教精神。即使是在那個(gè)新興宗教精神已經(jīng)開始傳播的時(shí)代里,艾米莉·勃朗特的宗教觀也是相當(dāng)獨(dú)特的,而這種獨(dú)特的宗教觀在書中體現(xiàn)了出來。艾米莉一方面對(duì)宗教相當(dāng)虔誠(chéng),另一方面卻歌頌不被傳統(tǒng)宗教觀認(rèn)可的自然,從《呼嘯山莊》里對(duì)角色出生與死亡的描寫來看,艾米莉反對(duì)傳統(tǒng)宗教的規(guī)條和制度。文中對(duì)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靈魂的描寫更是嚴(yán)重違背傳統(tǒng)的宗教觀,不歸于天堂,不落于地獄,而是永遠(yuǎn)在呼嘯山莊的自然與田野中游蕩,這也許就是他們的幸福,也是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種宗教渴望。
結(jié)語:《呼嘯山莊》出自一個(gè)世界正發(fā)生急劇變化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代,因此那個(gè)時(shí)代人們思想上、文化上、宗教觀上的轉(zhuǎn)變與迷茫也深深地烙印進(jìn)了書中。這不僅令小說具備了更濃郁的時(shí)代色彩,也為其增添了許多獨(dú)特的魅力,值得我們研究和深思。
參考文獻(xiàn):
[1] 艾米莉·勃朗特.呼嘯山莊[M].北京:中國(guó)畫報(bào)出版社,2012.
[2] 聯(lián)合圣經(jīng)公會(huì)(譯).圣經(jīng)[M].中國(guó)基督教協(xié)會(huì),中國(guó)基督教三自愛國(guó)運(yùn)動(dòng)委員會(huì),2009.
- 企業(yè)導(dǎo)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對(duì)德國(guó)實(shí)踐教學(xué)體系的實(shí)地考察與借鑒
- 經(jīng)濟(jì)管理(非會(huì)計(jì))類專業(yè)會(huì)計(jì)學(xué)課程教學(xué)改革探析
- 淺析高職國(guó)際貿(mào)易專業(yè)教師的頂崗實(shí)踐
- 高職高專物流管理專業(yè)校內(nèi)實(shí)訓(xùn)基地開放式教學(xué)研究
- 《基礎(chǔ)會(huì)計(jì)》課程教學(xué)改革初探
- 《會(huì)計(jì)電算化》課程實(shí)踐項(xiàng)目教學(xué)思路設(shè)計(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