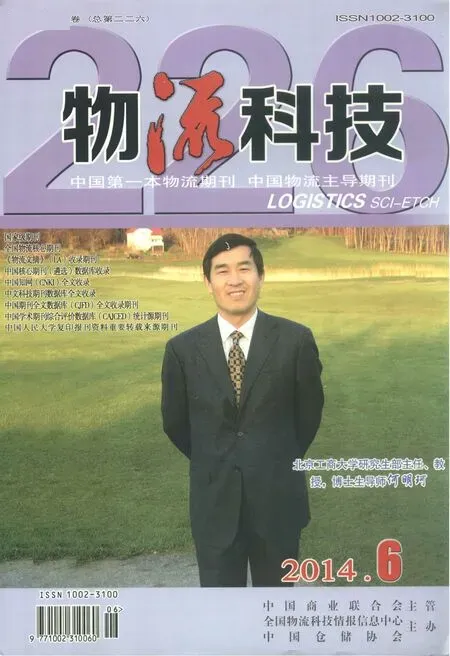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層次評估:指標(biāo)構(gòu)建與檢驗——以中山大學(xué)《區(qū)域物流規(guī)劃》課程為例
牛保莊,崔欽泉 (中山大學(xué) 嶺南學(xué)院,廣東 廣州510275)
NIU Bao-zhuang, CUI Qin-quan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0 引 言
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Breen and Krahake 1980)[1]將學(xué)生作為學(xué)習(xí)的主體,教師作為學(xué)生學(xué)習(xí)過程中的指引者,整個課程的開展以典型的教學(xué)任務(wù)為主線,注重新舊知識的銜接,通過多層次的任務(wù)設(shè)置,讓學(xué)生在一定的具體情境中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而系統(tǒng)地掌握新知識、新技能。該教學(xué)法的理論基礎(chǔ)是建構(gòu)主義[2],建構(gòu)主義認為學(xué)習(xí)者知識的建構(gòu)是通過不斷與周圍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進行交互,經(jīng)過意義建構(gòu)獲得[3]。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作為一種新的教學(xué)方法,已經(jīng)在高校的計算機與信息技術(shù)[4]、管理信息系統(tǒng)[5]、物流學(xué)[6-7]、物流管理基礎(chǔ)[8]等課程的教學(xué)中得到了廣泛的應(yīng)用。
任務(wù)驅(qū)動法的交互性、真實性和以學(xué)生為中心和建構(gòu)性的特點(Nunan 1989)[9],使之與傳統(tǒng)教學(xué)方法相比較,具有獨特的優(yōu)勢。然而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譬如,在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教學(xué)效果評價方面,目前尚無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教師實施了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后,應(yīng)該如何評價實施效果?已有的教學(xué)評估方法是否適用于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才能真正落到實處。以往文獻中,平衡記分卡(BSC)、整合績效管理(IPM) 等方法逐漸被引入高校的課程績效評估體系[10],但指標(biāo)過于寬泛,可操作性不強,并非針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因此,有必要設(shè)計一套合理的指標(biāo)體系,使得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能及時得到有效反饋和評價。
基于此,本文以中山大學(xué)《區(qū)域物流規(guī)劃》教學(xué)實踐為基礎(chǔ),構(gòu)建了一套基于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課程績效評價體系,并進行了詳細的統(tǒng)計分析檢驗。比較的對象是傳統(tǒng)教學(xué)評估體系、基于層次分析的改進教學(xué)評估體系以及融合傳統(tǒng)教學(xué)評估和任務(wù)驅(qū)動指標(biāo)的評估體系。
1 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評估方法選擇
盡管目前各高校都有自己的一套課程績效考核體系,但不同課程通用一套評價指標(biāo),忽視了每門課程自身的特色以及學(xué)科之間的可比性[11]。以中山大學(xué)教學(xué)評估表為例,指標(biāo)包括教學(xué)態(tài)度、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和教學(xué)效果四大方面,權(quán)重都是25%。而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涉及內(nèi)容較多,與學(xué)生互動較強,指標(biāo)應(yīng)有增刪,權(quán)重應(yīng)有不同。
層次分析法(AHP) 主要應(yīng)用在具有多個評估準(zhǔn)則的決策問題上,是一種定性和定量相結(jié)合的系統(tǒng)性評估方法,在處理復(fù)雜的多目標(biāo)評價方面有較好的特性。因此,本文構(gòu)建了一套針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的層次指標(biāo)體系,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進行績效評估,并對評估結(jié)果做了深入對比分析。
2 基于層次分析法的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評估體系構(gòu)建
評價體系緊跟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脈絡(luò),將各個環(huán)節(jié)包絡(luò)在內(nèi),從課程任務(wù)設(shè)計、指導(dǎo)任務(wù)開展、任務(wù)完成情況評價及反饋和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效果四個維度來構(gòu)建關(guān)鍵指標(biāo),如圖1 所示:

課程任務(wù)的設(shè)計是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開展的核心基礎(chǔ)。在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的整個環(huán)節(jié)中,興趣是推動學(xué)生不斷探索前進的動力[12],這就要求情境的設(shè)置要貼近生活,最好能直接取材于生活,使學(xué)生意識到自己的學(xué)習(xí)過程極具現(xiàn)實意義[13],在此基礎(chǔ)上,學(xué)生的成就感也就容易建立。此外,傳授知識的過程不是一種簡單地復(fù)制,時代的發(fā)展對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實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本文將“任務(wù)設(shè)置能留給學(xué)生足夠的自主發(fā)揮空間”作為評價指標(biāo)之一。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凸顯了學(xué)生自身的作用,學(xué)生由接受式的學(xué)習(xí)轉(zhuǎn)變?yōu)樘骄渴降膶W(xué)習(xí)。于是,在教學(xué)層次、難易設(shè)置上的統(tǒng)籌兼顧顯得尤為重要。此外,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特別強調(diào)知識之間的銜接性和連貫性。通過新舊知識的融會貫通,學(xué)生可以更加自然地鞏固舊知識,掌握新知識。
體系的第二個維度是指導(dǎo)任務(wù)開展。在這一個層面,其核心要素是分組的結(jié)構(gòu)與基礎(chǔ)性的把握[14]。基礎(chǔ)檢測的結(jié)果成為任務(wù)成員分組、分工的重要依據(jù)。教師要在學(xué)生大腦中建立起清晰的知識框架,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要兼顧各個層次的學(xué)生,雖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但對于基本知識點,一定要疏而不漏,有啟發(fā)性,使得學(xué)生對知識能觸類旁通。一方面,要尊重每個學(xué)生的意愿;另一方面,又要兼顧到小組成員結(jié)構(gòu)的合理性。這對任課教師而言既是一門藝術(shù),又是一種挑戰(zhàn),需要教師在課上和課下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摸底工作。
體系的第三個維度是任務(wù)完成情況及評價。這一過程的關(guān)鍵是反饋與考核。及時反饋是學(xué)生的課程任務(wù)得以順利開展的保障;考核,是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的催化劑,使學(xué)生能夠?qū)ψ约旱膱?zhí)行效果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可以借此對自身做一個較為全面的分析。此外,互相交流、答辯、質(zhì)疑的過程,也是一個集思廣益、打通思維脈絡(luò)的過程。
雖然教育工作者一直反對“一考定終身”的考核形式,但較少有教師能夠?qū)⑵涓吨T實踐。在任務(wù)驅(qū)動法的教學(xué)中,教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來跟進每一位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進程,走進每一位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甚至是生活世界。因此,過程評判成為核心評價指標(biāo)之一。
一門課程,從開展到結(jié)束,尤其是在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這一背景下,要實現(xiàn)的教學(xué)目標(biāo)更側(cè)重于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動手能力、探索問題的能力是否得到全面提高,學(xué)生是否全面而又靈活地掌握了知識,是否能學(xué)以致用,這是教學(xué)效果層面的核心指標(biāo)。
基于以上論述,本文構(gòu)建了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績效評估的核心指標(biāo)體系,如圖2 所示:
其中,令(Q1,Q2,Q3,Q4)=(課程任務(wù)設(shè)計,指導(dǎo)任務(wù)開展,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效果,任務(wù)完成情況評價及反饋),(q11,q12,q13,q14,q15)=(課程系統(tǒng)任務(wù)層次清晰,條理分明,與子任務(wù)的邏輯關(guān)系清楚;新舊知識銜接連貫,能介紹相關(guān)資料,引導(dǎo)學(xué)生查閱相關(guān)文獻;任務(wù)源于生活,情境感強,能激發(fā)學(xué)生的興趣;任務(wù)的重難點突出,難易梯度合理,能兼顧不同層次學(xué)生;任務(wù)設(shè)置能留給學(xué)生足夠的自由發(fā)揮空間),(q21,q22,q23,q24,q25)=(基礎(chǔ)檢測能體現(xiàn)課程要求,與課程任務(wù)密切相關(guān);充分尊重每位同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并能熱心幫助學(xué)生不斷完善;任務(wù)成員分組結(jié)構(gòu)合理;任務(wù)分析清楚到位,有啟發(fā)性;基礎(chǔ)知識點講解全面無遺漏,有引導(dǎo)和啟發(fā)性,使學(xué)生觸類旁通),(q31,q32,q33,q34,q35)=(對學(xué)生修改后的成果反饋準(zhǔn)確及時;課程任務(wù)考核方式形式多樣,客觀有效;學(xué)生全程參與積極性高;對學(xué)生的考核評價注重過程,任務(wù)的完成情況不是唯一標(biāo)準(zhǔn);愿意與學(xué)生交流,能及時耐心解答學(xué)生的疑惑),(q41,q42,q43,q44)=(課程任務(wù)有助于學(xué)生系統(tǒng)掌握知識,并能靈活應(yīng)用于實踐;課程任務(wù)有助于提高學(xué)生的求知欲和探索問題的能力;課程任務(wù)有助于提高學(xué)生的自主動手能力;課程任務(wù)有助于提高學(xué)生創(chuàng)新能力)。
3 樣本分析與評價比較
區(qū)域物流是中山大學(xué)嶺南學(xué)院物流工程與管理專業(yè)新近開設(shè)的一門專業(yè)必修課程。這門課口徑寬,跨度大,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要求教師和學(xué)生系統(tǒng)地掌握管理決策理論與方法、物流管理戰(zhàn)略管理、區(qū)域經(jīng)濟、管理信息系統(tǒng)等方面的知識,并具備在實踐中熟練應(yīng)用的能力。筆者以2009 級和2010 級物流管理專業(yè)學(xué)生為樣本收集評價結(jié)果,對中大評教體系、改進型中大評教體系、任務(wù)驅(qū)動體系、任務(wù)驅(qū)動與傳統(tǒng)評估融合體系四種評估體系進行對比分析,并探討了結(jié)果的差異性。文中的中大評教體系是中山大學(xué)現(xiàn)行的課程評教法,改進型中大評教體系是用層次分析打分之后的評教法(采用中大現(xiàn)行指標(biāo),但權(quán)重不同),任務(wù)驅(qū)動體系即筆者在第2 章構(gòu)建的指標(biāo)體系,任務(wù)驅(qū)動與傳統(tǒng)評估融合體系是指將中大評教指標(biāo)與任務(wù)驅(qū)動評價指標(biāo)的相同部分有機融合之后的課程績效評價體系,以下簡稱融合型。
3.1 指標(biāo)體系
3.1.1 中山大學(xué)本科評教指標(biāo)體系其中(U1,U2,U3,U4)=(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效果,教學(xué)方法,教學(xué)態(tài)度),(u11,u12,u13)=(備課充分、授課熟練;教態(tài)大方、為人師表;愿意與學(xué)生交流、能耐心解答學(xué)生疑問),(u21,u22,u23,u24)=(內(nèi)容清晰、重點突出、難點講透;講課深度和容量適合學(xué)生掌握;能介紹相關(guān)參考資料,注意新舊內(nèi)容銜接;注重反映學(xué)科發(fā)展的新動態(tài)和新成果),(u31,u32,u33)=(講課有啟發(fā)性、善于促進學(xué)生思考;聯(lián)系實際、案例講解與理論闡述結(jié)合恰當(dāng);能采用多種教學(xué)手段、運用效果好),(u41,u42,u43)=(教師授課有利于提高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教師授課有助于提高學(xué)生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授課有助于引導(dǎo)學(xué)生自學(xué))。

3.1.2 任務(wù)驅(qū)動與中大評教融合體系針對以上的評估體系,筆者請中山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教育學(xué)院的專家對各項指標(biāo)進行了權(quán)重打分,本文在加權(quán)處理專家意見的基礎(chǔ)上對各評估法做了對比分析。
3.2 權(quán)重結(jié)果
3.2.1 改進型中大評教體系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
一級指標(biāo)U1、U2、U3、U4的權(quán)重W= (0.2332,0.1277,0.5884,0.0506),C.R.=0.0138;二級指標(biāo)權(quán)重如表1 所示。
評價指標(biāo)(u11,u12,u13,u14,u21,u22,u23,u31,u32,u33,u41,u42,u43)相對于總目標(biāo)的權(quán)重:

3.2.2 任務(wù)驅(qū)動評教體系指標(biāo)權(quán)重
一級指標(biāo)Q1、Q2、Q3、Q4的權(quán)重W= (0.3464,0.4472,0.1209,0.0855),C.R.=0.035;二級指標(biāo)權(quán)重如表2 所示。

表1 中山大學(xué)本科生評教體系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值

表2 任務(wù)驅(qū)動評教體系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值
評價指標(biāo)(q11,q12,q13,q14,q15,q21,q22,q23,q24,q25,q31,q32,q33,q34,q41,q42,q43,q44,q45) 相對于總目標(biāo)的權(quán)重W=(0.0920,0.0436,0.0211,0.1717,0.0181,0.0251,0.2381,0.0318,0.0370,0.1152,0.0797,0.0215,0.0102,0.0094,0.0417,0.0091,0.0034,0.0173,0.0139)。
3.2.3 融合型評教體系指標(biāo)權(quán)重
一級指標(biāo)W1、W2、W3、W4的權(quán)重W= (0.5884,0.2332,0.0506,0.1277),C.R.=0.0138;二級指標(biāo)權(quán)重如表3 所示:

表3 融合型評教體系指標(biāo)權(quán)重值
評價指標(biāo)相對于總目標(biāo)的權(quán)重W=(0.0374,0.0257,0.0156,0.0205,0.1444,0.0468,0.2371,0.0608,0.0083,0.0083,0.0386,0.0036,0.0704,0.0092,0.0375,0.0187,0.0021,0.0096,0.0094)。
3.3 權(quán)重對比分析
中山大學(xué)本科生評教指標(biāo),雖然從等級判斷到打分量化以及評教內(nèi)容上都進行過一定調(diào)整,但從目前的評教體系來看,其對u13、u22、u23、u31、u32和u33六項指標(biāo)所賦予的權(quán)重分別為0.05,對其他七項指標(biāo)賦予的權(quán)重分別為0.1,存在人為主觀因素影響大,權(quán)重賦值形式過于簡單等問題,不能準(zhǔn)確反映每個評價要素的相對權(quán)重,導(dǎo)致最終的評教結(jié)果偏離真實值。
3.3.1 中山大學(xué)現(xiàn)行本科生評教指標(biāo)與改進型評教指標(biāo)對比
圖3 中,以偏離45 度線的程度來度量各因素權(quán)重的未改進值(中山大學(xué)本科生評教指標(biāo)權(quán)重值) 與改進值的差異性。在權(quán)重值小于0.1 時,隨權(quán)重值的增大,改進值指逐漸趨近于未改進值,但當(dāng)權(quán)重值大于0.1 時,未改進值與改進值出現(xiàn)較大幅度的分化,這說明,在中山大學(xué)評教體系中,部分指標(biāo)的實際權(quán)重值小于給定值,但變異性不明顯;而另一部分指標(biāo)的實際權(quán)重值遠高于給定值。于是,此評教體系忽視了部分指標(biāo)的重要性,其權(quán)重賦值居中化的做法掩蓋了影響課程績效的重要因素。通過未改進值與改進值的擬合優(yōu)度檢驗,得到的χ2值為29.6957,在α=0.05 的顯著水平下,得出結(jié)論:與未改進值相比較,改進值發(fā)生了明顯的變異。
3.3.2 改進型評教體系與融合型體系對比


圖4 中,以45 度線為基準(zhǔn),相較于中山大學(xué)本科生評教指標(biāo)的改進體系,在融合型課程績效評價體系中,各指標(biāo)所占權(quán)重顯著下降,所占比重均小于0.05,并且趨勢性不明顯;通過擬合優(yōu)度檢驗,χ2=152.1357,在α=0.05 的顯著水平下,得出結(jié)論:與融合值相較,改進值發(fā)生了顯著性變異。中山大學(xué)本科生評教指標(biāo)在融入任務(wù)驅(qū)動評教指標(biāo)后,其對課程績效的影響系數(shù)大幅下降,是由于在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課程績效評估中,任務(wù)驅(qū)動評價指標(biāo)占了絕對優(yōu)勢,課程績效的優(yōu)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開展過程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而缺乏針對性的原始評價指標(biāo)的重要性顯著降低,已經(jīng)成為影響課程績效的次要指標(biāo)。因此,雖然在層次分析基礎(chǔ)上對原始的評教體系進行了改進,其效度已有大幅提升,但在與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課程績效評價指標(biāo)的對比中,其地位明顯降低。
3.3.3 任務(wù)驅(qū)動體系與融合型體系對比
將任務(wù)驅(qū)動評價體系中的各項指標(biāo)在任務(wù)驅(qū)動評價體系和融合型評價體系中的權(quán)重值進行擬合優(yōu)度檢驗,得到χ2=66.4555。在α=0.05 的顯著水平下,得出的結(jié)論是:任務(wù)驅(qū)動評價體系中的各項指標(biāo)權(quán)重值發(fā)生了顯著性變化,違背了上文的結(jié)論:任務(wù)驅(qū)動評價指標(biāo)是課程績效考核的核心指標(biāo)。
為解釋上述統(tǒng)計結(jié)果,本文分別對兩套體系的第一層和第二層指標(biāo)權(quán)重做了剖析對比。筆者選取相較任務(wù)驅(qū)動評價體系而言,在融合型體系中變異最顯著的四項指標(biāo),M1(q34)、M2(q22)、M3(q32)、M4(q14)做進一步分析。

表4 權(quán)重變化最大的四項指標(biāo)比較
同樣進行擬合優(yōu)度分析,得出χ2=62.5615,十分接近66.4555,于是,這四項因素是以上做出任務(wù)驅(qū)動評價體系中的各項指標(biāo)權(quán)重值發(fā)生了顯著性變化的結(jié)論的關(guān)鍵證據(jù)。進一步將這四項指標(biāo)所屬的一級指標(biāo)和這四項指標(biāo)在一級指標(biāo)下所占的權(quán)重做了擬合優(yōu)度分析,得出的結(jié)論是:這四項指標(biāo)所屬的一級指標(biāo)權(quán)重發(fā)生顯著變異,而各指標(biāo)在一級指標(biāo)下的權(quán)重值未發(fā)生顯著變化。
以上分析使得將兩套指標(biāo)進行融合的可行性有待商榷,原因有二。其一,融合型指標(biāo)中由于引入了與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關(guān)聯(lián)度不強的評價指標(biāo),使得原有的課程任務(wù)設(shè)計、任務(wù)指導(dǎo)開展、反饋評價和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效果這四個一級指標(biāo)的結(jié)構(gòu)被打破。立足于評價體系的層次性,只能選擇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效果、教學(xué)態(tài)度和教學(xué)方法這四項一級指標(biāo),與二級指標(biāo)相對應(yīng)的一級指標(biāo)權(quán)重同任務(wù)驅(qū)動評價體系大相徑庭。雖然在融合體系中,針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而言,由于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課程績效評估指標(biāo)的核心性,在融合型中,任務(wù)驅(qū)動體系指標(biāo)的二級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沒有發(fā)生明顯變化,但一級指標(biāo)權(quán)重發(fā)生了明顯變異。其二,任務(wù)驅(qū)動評估體系只有19 個核心評價指標(biāo),而融合型體系中有30 個評價指標(biāo),繁雜的評價指標(biāo)容易使學(xué)生產(chǎn)生評教疲勞和抵觸感,難以獲得高質(zhì)量的評教結(jié)果,同時也增加了分析的難度。
3.4 各評估體系的評估結(jié)果分析
在中山大學(xué)本科生評教體系下,筆者所執(zhí)教的《區(qū)域物流規(guī)劃》課程綜合得分情況如表5 所示:

表5 各評教指標(biāo)體系下的課程績效得分
改進的中大評教體系與中大評教體系相比較,得分最高(95.2) 的u13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出現(xiàn)大幅下降,降至0.0123,而得分比較低的幾項,如u32和u21的權(quán)重分別大幅度上升至0.4271 和0.1609,因此,導(dǎo)致教師在改進的體系中得分較低。
與融合型體系相比較,任務(wù)驅(qū)動體系得分較高,是因為在q14、q22等幾項權(quán)重較大的指標(biāo)中得分較高,分別為96.4 和98.2。
當(dāng)然,在任務(wù)驅(qū)動評教體系中也有很多得分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基礎(chǔ)知識講解的全面性、基礎(chǔ)檢測的有效性等,由于學(xué)生層次差異,教師在這方面很難對學(xué)生的整體層次有一個精確的把握,這一部分需要筆者在日后的教學(xué)實踐中不斷改進。
4 總 結(jié)
本文以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具體開展為切入點,構(gòu)建了基于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課程績效評估體系,并結(jié)合實際的評價結(jié)果,對所構(gòu)建的評價體系的可行性和信度做了進一步論證,是對高校課程績效評估的一個補充。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針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構(gòu)建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績效評估體系,得出:既有的傳統(tǒng)課程績效評估體系在指標(biāo)權(quán)重上存在不合理之處;改進的傳統(tǒng)評教體系與未改進前相比,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有較大變異;在不考慮指標(biāo)融合時一級指標(biāo)分類因素影響的情況下,任務(wù)驅(qū)動評價體系指標(biāo)在各體系對比中仍是影響課程績效的主導(dǎo)因素等結(jié)論。結(jié)果基于樣本數(shù)據(jù)并通過了檢驗,相對嚴謹。
在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實踐過程中,筆者也將嘗試新的思路,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課程績效評估體系做出進一步完善。筆者還將繼續(xù)探索其他多目標(biāo)評估方法的應(yīng)用,并與層次分析的結(jié)果進行比較,以檢驗教學(xué)績效評估結(jié)果的有效性。
[1] Breen, M. P. & Candlin, C. N. The essentials of a communicative curriculum in language teaching[J]. Applied Linguistics,1980(2):89-112.
[2] Matthews M. R. Introductory comments on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ivism in science education[J]. Science & Education, 1997(6):5-14.
[3] 丁邦平. 建構(gòu)主義與面向21 世紀(jì)的科學(xué)教育改革[J]. 比較教育研究,2001(8):6-10.
[4] 郭紹青. 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內(nèi)涵[J]. 中國電化教育,2006(7):57-59.
[5] 唐文源,張珺,李頻宇. 管理信息系統(tǒng)課程中的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的探討[J]. 中國管理信息化,2006(8):80-83.
[6] 李曉超. 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模式在《物流學(xué)》本科課程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J]. 物流技術(shù),2010(2):158-160.
[7] 公雙雷. 以任務(wù)驅(qū)動的物流教學(xué)方法探究[J]. 物流科技,2009(2):126-128.
[8] 黃志寧. 基于“任務(wù)驅(qū)動”《物流管理基礎(chǔ)》的教學(xué)改革研究與實踐[J]. 物流采購與研究,2009(4):109-111.
[9] Nunan, D. Designing tasks for the communicative classroom. Cambrid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 徐銀燕,李麗芳,孫圣勇. 論高校課程績效的科學(xué)考核觀[J]. 教育視點,2009(7):21-22.
[11] 鄧璐,牛奉高,齊玉琴. 高校教師績效評價的實證研究[J]. 山西財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2011(2):171-176.
[12] 程國東. 淺談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中的任務(wù)設(shè)置問題[J]. 教學(xué)研究,2012(1):113.
[13] 安俊秀. 構(gòu)建“興趣本位、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的課程體系論[J]. 教育理論與實踐,2008(2):59-60.
[14] 丁曉倩,梁宏倩,海小娟,等. 任務(wù)驅(qū)動教學(xué)法應(yīng)用于信息技術(shù)課程教學(xué)的誤區(qū)分析[J]. 科技信息,2008(22):534-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