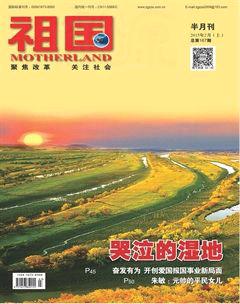透析信息化作戰指揮新特征
高東廣
軍委主席習近平要求,全軍要“深入研究現代戰爭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把現代戰爭的制勝機理搞透”。縱觀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幾場高技術局部戰爭,我們不難發現,當今世界,新軍事革命浪潮洶涌,以強大的力量推動著機械化戰爭形態向信息化戰爭形態的迅疾轉變。正如哲學家庫恩所言:人類社會的科學發展是科學范式的轉換推動的,當發生科學革命時,科學發展將被一種新的范式所規范。人類戰爭史也一再表明,戰爭形態的變革與科技革命緊密相關,當新的科技革命發生時,必將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強烈地沖擊和影響軍事領域。海灣戰爭以來的幾場高技術局部戰爭舉世矚目,信息化戰爭形態凸顯雛形,并正在使作戰方式、作戰指揮和后勤保障方式方法等發生根本性“驟變”,筆者從信息化作戰指揮新理念、新特征,對信息化作戰制勝機理進行詮釋。
時代烙印:網絡化指揮
現代信息化條件下作戰,充滿整個戰場范圍的信息將成倍增長,傳統的通信傳輸渠道已遠不能滿足作戰指揮需求,取而代之的是遍布戰場的從戰略、戰役到戰術甚至單兵的各種網絡及無數節點。這些網絡呈立體交叉、矩陣型結構,用現代語言描繪就是:縱橫貫通——縱到底、橫到邊,無縫鏈接——環環緊扣、鏈接如流,綜合集成——要素集成、系統集成。然而,從最高層到最基層指揮單元以及諸軍兵種都能在這個龐大的網絡節點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敵方即使摧毀某一節點,信息流仍能通過網絡迂回,溝通聯絡,從而實現高效、快速、安全的網絡化指揮。
從戰略層到戰術層,信息網絡系統均由大量無(有)線電通信系統、計算機通信系統、數字通信系統、衛星通信系統、衛星定位系統等緊密相連,在陸、海、空、天、電多維領域,各種通信手段綜合運用、系統集成,形成高效的網絡空間,使戰場指揮控制暢通無阻。這種戰場網絡環境,為現代作戰指揮提供了強大的網絡化平臺,而較之傳統戰場,這種平臺的物理和效能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革,使作戰指揮信息在網絡狀指揮體系中,高效、安全、不間斷地流通。海灣戰爭結束后,世界一些軍事強國都從美軍運用網絡化指揮作戰中得到啟示,競相加強以信息網絡系統為依托的網絡化指揮建設,并在各自的軍事變革與轉型中不斷地強化網絡化指揮理念。一些發達國家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甚至與國家互聯網相鏈接,構成了軍地互聯網,使戰時地方支援也實現了網絡化。
超越時空:全維化指揮
從主體意義上講,傳統戰爭主要是以陸地為主、以平面為主、以線式為主。而在現代信息化作戰條件下,軍事上的精確打擊、遠程打擊和超視距打擊能力不斷提高,作戰也不再是從前沿到縱深逐步推進,而是超越時空直接攻擊縱深戰略目標,在非接觸狀態下即可達成作戰目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戰場空間急劇拓展,由一戰、二戰時的陸、海、空三維戰場急劇拓展到太空戰場、電磁戰場等多維戰場,軍事理論界進而提出了所謂“全維戰場”。戰場范圍的空前拓展,前后方界線、攻防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要求作戰指揮要在動態中準確定位,在機動中尋求優勢,在稍縱即逝的全維空間中捕捉最佳戰機。
為此,要求作戰指揮必須在陸、海、空、天、電全維領域,組織實施立體、遠程和快速的全維化指揮。海灣戰爭中,美軍投入數百架戰略運輸機,以及大量快速海運船,組織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遠程立體化快速投送,向作戰地區運送52萬作戰部隊、610萬噸油料和400萬噸其它物資,有效地保障了作戰需求。所以國際評論認為,信息化戰爭條件下不論是作戰行動還是后勤保障,都需要有在全維空間組織實施的能力,全維化指揮已成為取得現代戰爭主動權的關鍵因素之一。
高效即時:實時化指揮
從古至今,戰爭都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然而,古戰場時間因素較之空間因素處于從屬地位。工業時代到來,恩格斯提出了:“時間就是軍隊,時間就是勝利”。可見,時間因素在作戰中的作用急升。通常,傳統戰爭是以年、月、日來計算的,而現代信息化條件下作戰則常常是用秒、分秒以至毫秒來計算。海灣戰爭時,由于充分運用了指揮自動化系統,制定作戰方案僅需幾小時,實施也在幾小時;到了伊拉克戰爭,由于數字化指揮手段和信息網絡系統的綜合運用,對作戰部隊可近乎實時掌控、即時決策,基本上接近了指揮控制的實時化。
而且從發展來看,由于太空探測、空中偵察、紅外成像偵察手段以及精確制導技術和信息化彈藥的廣泛應用,使戰場處于全方位、全時空、近乎透明狀態,這使得“發現即摧毀”愈來愈成為現實。有資料顯示,一顆偵察衛星,可以監視地球面積的30%以上;一架電子預警機,能在600至900公里的范圍識別各種目標;微光夜視系統,可使亮度增加1000倍以上。所以,面對高度透明的信息化戰場環境,對現代作戰力量的運用,必定由傳統的空間集中、力量集中轉變到快速的時間集中、效能集中上。
有機融合:人機化指揮
恩格斯有句名言:“革命將以現代的軍事手段和現代的軍事學術與現代的軍事手段和現代的軍事學術作戰。”隨著現代信息技術、模擬技術、計算機技術、衛星通信和虛擬技術等高新技術在作戰指揮領域的廣泛應用,特別是各類指揮自動化系統和輔助決策支持系統等指揮手段的應用,使作戰指揮具有了最為典型的“人—機”結合特征,人機幾乎是不能分離的。以往傳統戰爭中作戰指揮在通常情況下,主要靠人腦、靠自身指揮經驗,指揮往往采取手勢、口語、擂鼓、信鴿等駕馭指揮作戰。
而工業文明時代,隨著望遠鏡、電報機、電話機、計算尺、指揮尺等輔助指揮作戰,大大減輕了指揮人員的工作量。到了現代信息化戰爭時代,戰場變化急劇,戰機稍縱即逝,指揮員要及時定下決策,必須借助于以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為核心的高科技輔助決策支持系統。通常輔助決策支持系統包括:作戰綜合數據庫、作戰模擬庫、軍事專家知識庫、古今中外戰例庫、敵我雙方基本實力與方法庫和操作便捷的人-機交互系統等等。海灣戰爭以來的幾場局部戰爭,美軍為首的多國部隊僅在戰場范圍就配置有數千臺各型計算機和萬余個各類信息處理分系統。戰爭實踐表明,各類指揮信息處理系統已經成為現代作戰指揮的“倍增器”,其潛在的倍增作用很難用傳統的兵力加強觀念來衡量,指揮人員運用的好,將使作戰效能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大。所以有理由說,不論是現代信息條件下作戰,還是平時戰備訓練與管理,都離不開各類指揮信息系統的強力支撐,各類指揮手段的綜合運用,已成為現代軍事建設和發展的重要象征。因此,人們普遍把指揮人員與各類指揮信息系統稱為“人—機”結合或“人—機”系統。endprint
尤其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交戰雙方指揮員,一方面必須通過“人—機”系統,借助計算機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進行運籌與決策,在全維空間組織、協同、指揮各軍兵種和各個層次作戰力量,從而大大提高作戰指揮的時效性和準確性;另一方面,還必須通過“人—機”指揮系統,在高技術主導下實施謀略對抗,使謀略對抗在光、電、磁、熱、聲等無形要素環境中,定奇謀,用奇兵,施奇法,以奇制勝。
適時精確:精準化指揮
從海灣戰爭以來的幾場信息化戰爭進程看,作戰目的越來越明確,作戰目標越來越有限,作戰有限性越來越突出。與此同時,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在戰場上廣泛應用,這為作戰系統和后勤系統的精確化指揮提供了可能,同時也對作戰指揮以及后勤指揮等的精準性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
俗語說得好,“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在信息化作戰條件下,交戰雙方均把重點放在“精確化交戰”上,不再搞以往超出戰略目標的無謂消耗。作戰指揮和后勤指揮中更注重把重點放在“精確”和“有效”上。因為在高效運行的信息化戰場,任何微小的差錯都可能導致作戰行動、保障活動等嚴重失利。美軍自海灣戰爭以后,認真總結了作戰指揮中的一些教訓,對作戰系統提出了精確化交戰的理念,而對后勤則提出了“聚焦后勤”等新的概念,并在伊拉克戰爭中進行了新的試驗。美軍新近提出的21世紀要突出強調精確化指揮控制,正在于此。其重點要求:一是信息情報來源精確可靠,通過全方位、全天候的信息處理平臺,信息搜集、處理、篩選基本實現了高效、快速、準確;二是決策方法科學、智能、快速,通過決策輔助支持系統,能在多種作戰方案和后勤保障方案中選取最佳方案;三是指揮人員具有更高的綜合素質。尤其是,現代精確化指揮對指揮員的軍事素質、科技素質和綜合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對軍事指揮員思維的預見性、敏銳性、靈活性和創新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總之,精確化指揮主要是利用先進的計算機技術、信息網絡技術和自識別技術,建構信息化網絡系統平臺,實現對所有作戰力量的靜態、動態可視和作戰行動的有效精確控制。誠然,信息化手段再高,終究還是代替不了作戰指揮人員本身,因為指揮員永遠是作戰決策與指揮的主體。
(作者系軍事專家、大校、研究員、碩導、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副秘書長、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邀研究員、中國藝術家協會軍事文化委員會秘書長。出版軍事專著18部,發表文章200余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