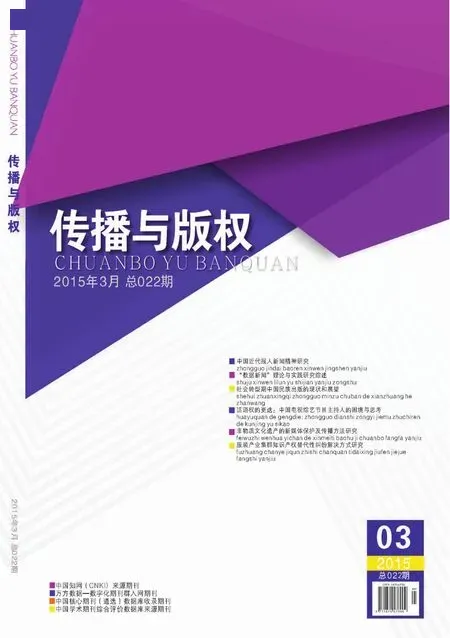話語權的更迭:中國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的困境與思考
劉金旭
話語權的更迭:中國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的困境與思考
劉金旭
[摘要]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與全民狂歡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電視節目呈現出了各種新特質。隨著消費文化、海外文化的浸染,中國電視綜藝節目呈現出各種各樣的異化態勢,節目的形式與結構發生了調整與變化,觀眾的收視習慣也被潛移默化的改變。電視綜藝節目的內部結構逐漸遭到破壞,顯示出了一種不平衡的發展傾向:電視節目主持人話語權逐漸隱匿。
[關鍵詞]話語權;中國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困境;思考
[作者]劉金旭,湖南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巴赫金曾說過:“狂歡節沒有演員和觀眾之分。就其意義來說是全民性的,無所不包的,所有人都需要加入親昵的交際。”電視綜藝節目也不例外,全民參與已成為不可遏制的態勢,沒有門檻沒有把關人。《我是歌手》《開講啦》《超級演說家》《中國好聲音》等節目播出后,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電視收視風暴。但是在節目火熱背后,有一種微妙的現場浮出水面,那就是有一個顯像群體逐漸走向隱像邊緣化,甚至可以說逐漸失去了話語權,他們就是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曾經作為節目中關鍵支撐點的主持人卻在新的傳播環境下走向隱匿,因此綜藝節目主持人在重構的電視節目中走向了困境,也引起了今后如何調整主持人自身定位的思考。
一、主持人話語權走向傾斜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之相同步的作為上層建筑的中國電視綜藝節目也有了一種突飛猛進的態勢。從《正大綜藝》到《幸運52》,從《夢想劇場》到《星光大道》,從《超級女聲》到《我是歌手》,這一系列的電視綜藝節目經歷了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黃金時期。與此同時,進入我們視野的還有一批知名的節目主持人,他們幽默的主持風格、善談的表達方式、優雅的個人氣質、敏捷的應變思維、亮麗時尚的氣質形象都給他們自身還有所主持的節目打上了個性的印記,因此主持人成為一個節目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甚至說成為這檔節目的靈魂。因此主持人的重心地位也決定了節目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隨著專業化的嘉賓與評委加入綜藝節目的陣營中之后,從一開始節目中的話語權側重于主持人,再到主持人與嘉賓評委話語權的平衡再到嘉賓的一方傾斜,慢慢地嘉賓與評委成為節目的靈魂與焦點。如果說電視節目主持人、專業嘉賓團隊、節目參與明星是代表三種不同話語權的話,那么在中國最早的電視綜藝節目中,電視節目主持人把握著電視節目的話語權,慢慢地形成三足鼎立,直到今天“一人獨大”,專業嘉賓與參與明星成為節目的焦點,他們把握了節目的話語權,主持人的話語空間變狹窄擁擠,隨之而來的是慢慢被隱藏直至消失。這一現象在近一兩年來收視率較高的幾檔綜藝節目中可探究到其蹤影。電視文化建設,就是通過電視人對文化本質與文化內涵的真正占有,繼而通過電視節目對受眾進行文化告知、文化感染、文化滲透的文化影響過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其中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難以將這個整體工程繼續進行下去。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作為一檔綜藝節目的鏈條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話語權的頻頻更迭,他們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環,同樣作為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的他們逐漸走向了傾斜,地位也出現了威脅。
二、主持人話語權被嘉賓話語所取代
作為有聲語言傳播主體的節目主持人如何在熒屏上散發出自身的影響力與話語權?一是需要具備與受眾“接觸”的第一要素:吸引力。二是具有令受眾“持續”的個性因子:感染力。三是需要有令受眾“彌漫”的力量保證:滲透力。吸引力是主持人綜合屏幕形象的直觀展示,從2013年湖南衛視推出的大型明星音樂競技類真人秀節目《我是歌手》可見一斑,湖南衛視的主持人沒有出現在舞臺上,出乎觀眾意料的是參賽選手“羽泉組合”中的胡海泉擔任比賽的主持人。在2015年的節目中古巨基與孫楠也加盟到了主持的團隊,同樣受到了觀眾的良性反饋,一種明星效應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也散發出了強大的光暈。而湖南衛視的眾多綜藝節目主持人成為參賽嘉賓的“隨從”,而且只出現在第二現場,在他們身上毫無“話語權”。在東方衛視之前熱播的《舞林大會》中,金星犀利的點評讓她成為這檔節目的焦點,她不但搶奪了參賽明星的光環,還讓觀眾似乎忘記了節目中還有一位主持人的存在。此時的節目主持人的處境談不上尷尬,但確實處于話語權的邊緣地帶。不可否認,作為嘉賓身份的他們具備了節目話語權
的支配權利,因為他們的確從身上散發出由內而外的感染力。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的主持人華少的話語權也不例外地被擠壓,他的傳播空間是與參賽選手的家人在第二現場加油助陣,而第一現場的話語權完全掌控在位導師“口中”,他們彼此的調侃互動,似乎剝奪了主持人的地位。主持人在此類電視綜藝節目中處于劣勢地位,也在內部系統中處于不平衡的狀態。“喧賓奪主”似乎成為這類節目中評委的標簽。
三、綜藝節目主持人話語體系由“個性”走向“沖突”
主持人的傳播地位受到多方面條件的制約,如社會環境、媒介環境、個體環境等。作為電視語言顯性符號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一旦進入電視,勢必超越個體本身,成為傳媒話語生產中的有聲語言傳播主體,成為在“公用空間”進行話語對話的重要中介。但是在現階段的電視綜藝節目傳播過程中,傳統的電視綜藝節目中以主持人為主的話語體系逐漸削弱,而嘉賓與選手之間的新“對話”逐漸增加,不僅話語權落到了嘉賓和評委一方,主持人的話語體系也一度被嘉賓與選手之間的“沖突”所取代。主持人不再是唯一的節目調節者和中介。通過嘉賓與選手之間的矛盾沖突,重新構建了節目中的新的話語體系:“戲劇性沖突”。當然,這必定加強節目的收視強度。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是打造個性化欄目的一種手段,但是一種新看點出現,必將會打開其他各家媒體的“新思維”,因此必然會引起個電視媒體的爭相效仿。“克隆化”“雷同化”成為一種令人焦慮的現象,電視節目的策劃與設計本身出現了偏頗,有意或無意忽略了主持人這一重要地位。比如《非誠勿擾》中嘉賓對前來擇偶的男士進行的調侃與點評,對各位女嘉賓的交流與爭論構成了嘉賓與選手、嘉賓與嘉賓的話語體系。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會隨著彼此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進行討論、爭辯甚至爭吵,這一系列的不可預知的矛盾推動了節目的進程。因為對于電視觀眾而言,在這種節目話語體系中傳遞出的信息不存在修改和二度創作,沒有方位偏差,有可靠的時效性,因此類似于這樣的“新話語體系”即戲劇性沖突都成為這類節目的新看點。但是恰恰被忽略的是電視節目主持人被隱匿,觀眾的焦點不再是主持人的引出與總結,更加期待的是一種即將爆棚的戲劇化沖突。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人的話語權似乎不再起作用,適當的調侃也無法重新構建此類節目應有的內部平衡,人為化的矛盾構建吸進著電視觀眾的眼球,盡量迎合現代電視觀眾的收視習慣也成為奪取收視率的最佳手段。可想而知,電視綜藝節目中主持人應有的語言功能逐漸失去了作用。
四、綜藝節目主持人話語權是否會消失?
隨著中國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的話語體系被邊緣化的現象出現之后,問題也隨之而來:中國電視綜藝節目是否還會有主持人的一席之地,主持人是否還需要在節目中出現?當然,這個問題沒有任何人能妄下定論。但是主持人話語權的更迭現象的出現是需要主持人自身去做決定的。是順應電視傳播的潮流甘愿處于話語權的被動方,還是重新在電視節目的傳播過程中爭奪主持人的話語權,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中國經濟仍處于社會轉型期,泛娛樂化和審美異化背景下產生的節目仍然會如雨后春筍般滋生。面對收視為王、娛樂至上的當今節目宗旨,電視節目主持人是否應該思考自身處境與身份。究竟是應該將自己看成是一名普通的節目串聯點,還是將自己視作節目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鏈條,這是對于自身文化地位與文化身份的傳播身份的認同。主持人需要一種身份自覺,也需要一種文化自覺,人文精神的缺失不得不作為他們話語權丟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人文精神是其節目主持中的“魂”之所在。當矯揉造作的副語言充斥熒屏的時候,當程式化、純技術語言代替了真情實感的時候,當貴族化、優越感的表情爬滿面部的時候,受眾被置于何地?羅丹說:“美麗的風景所以使人感動,不是由于它給多少人或多或少的舒適的感覺,而是由于它引起人的思想。……藝術的整個美,來自思想、來自意圖。”面對紛繁復雜的媒體環境,提高自身的主持語言的修養與自身的傳播能力,也許是綜藝節目主持人走出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1]胡智峰.中國電視策劃與設計[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
[2]馬方.淺析綜藝節目的發展態勢與研究思路[J].南方電視學刊,2013(1).
[3]曾志華.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文化影響力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卜晨光,趙若竹.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的功能重設與話語重構[J].電視研究,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