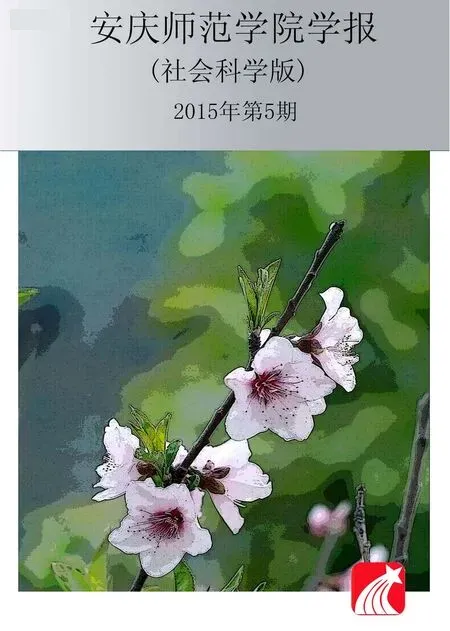《墨子虛詞用法詮釋》“而”字詞性歸類商榷
李 賽 男
(上海大學文學院, 上海 200444)
?
《墨子虛詞用法詮釋》“而”字詞性歸類商榷
李 賽 男
(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 200444)
摘要:謝德三《墨子虛詞用法詮釋》認為“而”作指示代詞猶“此”、作系詞猶“乃”、作準系詞猶“如”、作副詞猶“乃、才”,并根據(jù)譯義把“而”歸為介詞和連詞。這些“而”的語法功能都是連接前后兩個謂詞性結構,是連詞。《墨子虛詞用法詮釋》忽略了“而”的語法功能,用強賦實義、翻譯的方法,對“而”做出的詞性歸類是值得商榷的。《墨子》中的“然而”大部分都不是凝固結構,“而后”“而況”“而已”“而已矣”都是詞與詞的組合,《墨子虛詞用法詮釋》把它們都歸為熟語也是有問題的。
關鍵詞:《墨子虛詞用法詮釋》;而;詞性
謝德三的《墨子虛詞用法詮釋》[1](下簡稱《詮釋》)是第一部對《墨子》中的虛詞進行詞性歸類的研究專著,為先秦虛詞規(guī)律的總結積累了材料。由于該書在考察具體虛詞時過分注重其在句中的譯義,忽略虛詞本身的語法意義,從而強行析出一些虛詞本身沒有的詞性來。例如“而”,乃古漢語中極常見的虛詞,其基本功能就是用于連接前后兩個謂詞性成分。王力根據(jù)“而”聯(lián)結兩種行為或性質的功能,把它歸為“聯(lián)結詞”[2]391,而《詮釋》則將其分作指示代詞猶“此”、作系詞猶“乃”、作準系詞猶“如”、作副詞猶“乃、才”,作介詞猶“以”等等,這樣顯然是脫離了“而”作為連詞的基本性質,人為地根據(jù)上下文意譯添出不同的詞性來。此外,《墨子》中諸如“然而”、“而后”、“而況”等也均未凝固,不能作熟語看。
一、“而”不具有“此”的指代功能
謝氏認為“而”具有指示代詞的詞性,“意猶‘此’”。如:
(1)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墨子·天志上》)
(2)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zhàn)而死,而子慍,而猶欲糶,糶則慍也,豈不費哉?”(《墨子·魯問》)
(3)今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并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奸也。(《墨子·號令》)
三例中“而”的語義難解,前人多從疏通文字出發(fā),認為有“此”意。《詮釋》蓋受其影響,從而忽略了句中“而”的語法功能。
例(1) “焉而晏日”的釋義歷來備受爭議。“焉而晏日”本作“焉而晏曰”,畢沅根據(jù)上下文改為“焉而晏日”[3]91。孫詒讓依畢沅改。“晏日”即晴明之日。俞樾認為:“‘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為衍文。”孫氏認為:“上‘焉’與‘于’同義,‘焉而’猶言‘于而’,言于此晴晏之日,焉而得罪也。”[4]192吳毓江認為“而”字為“天”字之誤,因其二者古字相近而混淆。[5]291謝氏根據(jù)孫詒讓的觀點,認為此“而”猶“此”,遂認為“而”具有指示代詞性。孫氏從疏通文字的角度,認為“焉”同“于”,“而”同“此”,實則是以意改句。
考查《墨子》全文,位于句首的“焉”,其后大多接動詞,少數(shù)接名詞,“焉”為疑問代詞,用于修飾這些名詞和動詞。檢先秦文獻,無“焉”居句首而后接“而”的例子。“晏日”已為晴明之意,若再贅一“天”反而句意難通。查先秦古籍亦無“天晏日”之說。句首“焉而”很可能是承下衍,原句為“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正好印證了下文“明必見之”的結論。“得罪”做句子謂語動詞,“晏日”為“得罪”的條件,“而”在此處用于連接狀語和中心語。
例(2)中之“而”,畢沅認為乃“是”之誤,將“而”改為“是”[3]186,孫詒讓依據(jù)畢沅將其改正[4]473。如此,則這個“而”本應作“是”,并非“而”具有“是”的語法語義功能。《詮釋》不辨,誤將“而”等同于“是”,并進行歸類處理,顯然依據(jù)不足。雖然作為指示代詞的“是”用于回指前文,這本身就是聯(lián)系上下文,與“而”聯(lián)系前后的作用十分相似,但不能據(jù)此就認為“而”與“是”的功能相同。如:
(4)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筑則慍也,豈不悖哉!”(《墨子·貴義》)
本句與例(2)句法結構基本相同,基本上屬于同構。例中的“是”和“而”都用于聯(lián)系前后文,但不能據(jù)此就認為兩者是一樣的。
例(3)之“而”,謝氏根據(jù)孫詒讓意譯析為指示代詞,意猶“此”。孫氏云:“‘而’乃‘此’字之誤。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是其證。”[4]591其實,孫氏在此是從疏通文字出發(fā)來解釋虛詞的。我們知道,指示代詞用于回指前文,本身具有連接前后的功能,這一點同連詞“而”功能相似。但連詞幾近語法化過程的末端,語義完全丟失,語法功能虛化到了極點,變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指示代詞雖為虛詞,但具有較強的實義,可以做句子主語,它連接前后的功能只是在回指前文時附帶體現(xiàn)出來的功能。而且,指示代詞在句中具有樞紐作用,去掉之后句子就散架了。因此,連詞“而”與指示代詞 “是”等不可以混為一談。例(3)之“而”用于承接上文。孫氏以前句冗長,遂以“此”來回指前文,這種平衡前后的做法,于小學釋義方面無可厚非,但并非作為詞類劃分的依據(jù)。
二、判斷句中“而”不具有系詞功能
1. “而”不是系詞
在指示代詞分類之后,謝氏認為“而”具有系詞性,并對此進行了舉例論證。《詮釋》把判斷句中的“乃”歸為系詞與口語中的“是”等同,并進一步認為“而”與“乃”同。認為“乃”具有聯(lián)系前后的作用,并用“而”與之比擬。其實,“而”在聯(lián)系前后句時,其語法作用與系詞雖然很像,但二者卻有本質的不同,“而”不具有系詞功能。
“而”可用于連接句中謂詞性結構、描寫句或判斷句前后謂詞性小句、狀語從句和謂語句等。系詞則只用于判斷句中,對名詞性主語和謂語的內涵和外延關系表示判斷,語義上則是話題和述題切分的記號。它連接前后的作用只在判斷前后成分時附帶體現(xiàn)的。《詮釋》忽略系詞的主要功能,僅根據(jù)其聯(lián)系主謂,便強行將“而”歸為系詞。如:
(5)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墨子·尚同下》)
這里謝氏誤把“故當尚同之說”當作主語,余下部分歸作謂語,將前一“而”判定為系詞。其實,句中主語已經省略,“故當尚同之說”乃是作狀語,以界定“不可不察”的對象。“不可不察尚同為政之本”并非名詞謂語,而是一個復合結構。主句的動詞謂語為“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之要”作“察”的賓語。
(6)古者王今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zhàn),而不可不非。(《墨子·非攻中》)
“而不可不非”中“而”同樣不是處于判斷句中,而是位于假設關系中,述說一種必要性。句子主干為“古者王今大人不可不非(攻戰(zhàn))”,《詮釋》誤將“故當攻戰(zhàn)”看作主語,把“不可不非”當成謂語,把“而”視作系詞。其實,此處“故當攻戰(zhàn)”是“不可不非”的狀語,用來補充說明“非”的對象,“而”的作用只是用于連接狀語和中心語。
2.“而”與準系詞“如”不同
《詮釋》不僅將“而”誤作系詞,而且還認為“而”有準系詞性,其意猶“如”。
這種歸類其實也是忽略了“而”“如”在語法語義功能上的差別,僅憑句子的語境義做出的臆斷。謝氏在此條目下只舉了一例:
(7)若以尊卑為歲月數(shù),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墨子·非儒下》)
本句之“而卑子也”,王引之認為:“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6]俞樾亦認可王氏之說[7]。馬建忠《馬氏文通》(下簡稱《文通》)則認為“‘而’字之解‘若’‘如’等字者,非其本字,乃上下截之辭氣使然耳”[8]295。誠如《文通》所言,由于“而”位置靈活多變,加之其語法功能虛化至極,因此可譯為多種語境義。而《詮釋》機械地引用王氏觀點,將“而”等同于“如”了。
句中“親伯父宗兄而卑子”和“尊其妻子與父母同”作句子謂語;“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作為句中謂語的一部分獨立存在,是一個主謂結構,“親伯父宗兄”作主語,“卑子”作謂語,“而”用于連接主謂結構,與“子產而死”結構相同,意為“對待伯父和同族的兄弟就如對待庶子一樣”。把“而”作“如”解,是句子翻譯的結果。“親伯父宗兄而卑子”是假設復句結果句中的一個部分,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判斷句。既不能作為判斷句進行分析,就更談不上準系詞了。“如”作為準系詞,本身具有聯(lián)系前后的作用,這同“而”的功能吻合,于是《詮釋》遂將“而”解為“如”,再根據(jù)“如”的語法作用錯誤地將“而”歸為了準系詞。
三、“而”不具有副詞功能
在對“而”作系詞、準系詞的錯誤歸類后,《詮釋》還將“而”分析為副詞,一種情況相當于“能”,另一種情況相當于“乃”,意譯為“才、方才”。這種根據(jù)“而”的語境義對“而”進行分類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虛詞本身實義性不強,只根據(jù)其語境義對其功能進行分類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這本質上仍是延續(xù)了訓詁學以解經為目的的釋詞方法,于現(xiàn)代語言學研究虛詞功能,對其分布規(guī)律和條件進行總結的目的毫無裨益。
1.“而”不為副詞“能”
《詮釋》認為“而”作副詞如“能”,乃是從意譯的角度做出的分析。它根據(jù)《墨子》中同類句型,通過異文比較,于是將“而”與“能”作了類比。如:
(8)故古者圣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墨子·尚同中》)
謝氏認為例(8)中“而”“意與'能'相當,如口語之'能夠'”。《墨子》中還有一例語法結構與此類似,如:
(9)故古者圣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賢中》)
《詮釋》根據(jù)例(9)中“唯能審”認為例(8)中“唯而審”與此同,進而認為“而”與“能”通。郭錫良先生早就反對過用古注、互文來分析這類問題[9]110,同一篇文章中,作者經常會通過改換句中某些虛詞,來避免句子重復。虛詞的改換會直接影響句子結構的變化,因此僅根據(jù)前后文結構迥異的同義句來分析虛詞是不可取的。例(9)中“故古者圣王唯能審”雖與例(8)表意類似,但從整個句子結構來看,二者大相徑庭。
例(8)中“以”后接名詞,“以尚同”若作為介詞詞組處理則句子缺少賓語,所以此處“以”只能作為動詞看,意為“用”,是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唯而審”作狀語修飾“以”,意為“古者圣王只有明白地使用尚同學說”。例(9)中“以”是介詞,句中動詞謂語中心為“審”,“唯”用來修飾“審”的必要性,“以尚賢使能為政”是“審”的賓語,也是“審”的對象。例(8)(9)句子結構完全不同,不能做相同的分析,將“而”釋為“能”是意譯的結果。
例(8)中“而”是用來連接兩個平行形容詞性狀語。“唯”和“審”都作狀語修飾“以”,“唯”用來限定“以”的必要性,“審”用來修飾“以”的情態(tài),二者語義作用稍有不同,但都指向動詞“以”。“而”則用來連接二者,使其形成聯(lián)合狀語來修飾“以”,這個“而”只能根據(jù)其連接兩個謂詞性狀語“唯、審”的語法功能,將其歸為連詞。
2.“而”不為副詞“乃”
“乃”做副詞,有時用來強調時間上的先后或事情發(fā)展的因果關系,譯為“才、方才”。有時候,“而”連接的前后兩個謂詞性成分之間有時間上、情理上的關系,《詮釋》將這樣的“而”分析為同“乃”一樣的副詞,如:
(10)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公輸》)
謝氏認為上句中“而”“意與‘乃’相當,如口語之‘才’、‘方才’、‘方’”。郭錫良先生說過,“而”根本沒有副詞義[9],不能用串講、互訓的方式進行解釋。此處“而”若作“才”看,“公輸盤詘”是“曰”的充分必要條件,強調前者,“而”語義指向“曰”,用來修飾“曰”。但這里“詘”并不是“曰”的充分必要條件,這兩者只是時間上的前后相序而已。因此,這里“而”的功能只是聯(lián)系相繼的兩個動作,并沒有語義指向性,不能歸為副詞。
四、與“而”連用之“熟語”不具有凝固性
在對“而”的詞性進行歸類之后,《詮釋》將“然而”、“而后”、“而況”、“而已”、“而已矣”判定為“與‘而’連用之熟語”。熟語具有結構上的凝固性、語義上的整體性。“然而”、“而后”、“而況”、“而已”雖然在現(xiàn)代漢語中成詞,但在《墨子》中具有各自的語法功能,可以單獨使用,只是詞與詞的組合,不具備熟語的本質特征,不能歸為熟語。它這樣劃分,顯然是從現(xiàn)代漢語出發(fā),僅根據(jù)其共現(xiàn)頻率進行的歸類的,它沒有注意虛詞發(fā)展的歷史性和社會性。
1.然而
《詮釋》認為“然而”與口語的“但是”、“可是”相當,用來表示轉折關系,這實則是承認“然而”已經像“但是”、“可是”一樣,變成了轉折連詞。《經傳釋詞》認為“然而”同“然”,是“詞之轉也”[10],楊樹達《詞詮》[11]256、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12]、楊伯峻《古漢語虛詞》[13]124等都沿襲了《經傳釋詞》的說法,謝氏受其影響,也這樣認為。《文通》認為“然而”當拆讀,如“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孟子·公孫丑下》)中“然”用于承接上文,“而”用于連接下文,表轉折[8]292。
《文通》的看法是非常正確的,“然而”最初為兩個單音詞連用,到了戰(zhàn)國末開始變成一個凝固結構。《荀子》中的“然而”有42例為單音詞連用,有60例已變成表轉折語義的凝固結構[14]。“然而”凝固成詞開始于《墨子》,《墨子》24例“然而”中有4例已凝固成詞[15],如:
(11)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墨子·明鬼下》)
“雖……然而……”連用,“雖”后陳述的條件“使然”消解了“然而”中“然”的回指作用。“然”在前后句之間連用,一定程度上也加強了“然而”的成詞性。“使然”中“然”已經回指了一種情況,“然而”中的然若再用于回指,會影響整個句子的句意理解,在這種情況下,“然而”只能作為轉折連詞分析。
但是,這種情況較少見,“然而”在《墨子》中大多數(shù)情況下仍為兩個詞,如:
(12)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墨子·七患》)
此例中“然”用于回指前文“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用于逆接,表轉折。若把“然而”作轉折詞看,則“皆滅亡于百里之君”缺少主語,導致句法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然而”析為純粹表轉折,就會改變句子層次結構,影響句義理解。
因此,不能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把“然而”作為凝固結構看待,而應根據(jù)其語法功能仍將其視為詞與詞的組合。其中“然”具有很強的實義,用于回指前文,“而”用于聯(lián)系前后文,仍為連詞。兩者在長期共同使用過程中,由于語法功能的相合,遂變?yōu)橐粋€詞。現(xiàn)代漢語中“然而”只用于轉折,“然”的回指作用已經完全消失了。這種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才產生的,《詮釋》忽略了漢語史的時間概念。
2.而后
《詮釋》認為“而后”用于時間關系復句中,用以承接上下二事,相當于口語“才”“方才”,這與呂叔湘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16]。楊伯峻認為“而后”是連詞[13]31,這都是從現(xiàn)代漢語出發(fā)做出的解釋。《文通》則云“凡上下節(jié)有言時者,則以‘而’字連之,以記其時之同異”,“‘而后’不惟計時也,凡言因果言次第者,胥用焉”[8]296-297;也就是說,“而后”中“而”為連詞,“后”作時間狀語,用以說明前后句之間的時間、因果和主次關系,馬氏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
(13)昔荊靈王好小要,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jù)而后興,扶垣而后行。(《墨子·兼愛下》)
陳寶勤認為上句“固據(jù)而后興”“扶垣而后行”中的“而后”都為詞和詞的組合,“而”為連詞,“后”為時間名詞[14],“而”用于連接狀語“固據(jù)”、“扶垣”和謂語“后興”、“后行”,“后”是時間名詞,用于修飾動詞“興”和“行”,其層次結構如下:
固據(jù)而后興,扶垣而后行
┕┙┕┙┕┙┕┙┕┙┕┙
┕───┙ ┕───┙
“而”和“后”位于不同結構中,“而”連接的兩個謂詞結構之間有內在的時間和因果關系,不能將“而后”強行析出進行分析。
“而后”在《荀子》中有24例凝固為表示承接語義的固定結構[14],這說明“而后”在戰(zhàn)國末期才開始成為熟語。作為單純表承接語義的“而后”必須滿足:“而后”連接的前后句之間,沒有時間上的“先后”語義關系;“而后”連接的后句中,沒有“后”存在的空間;“而后”中“后”失去實義,受“而”影響,與“而”共同連接前后文,如:
(14)節(jié)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后誅之。(《荀子·強國篇》)
上例中“不順者”和“誅之”之間沒有語義上的先后關系。“而后”相當于“而”,用于主謂之間的連接,去掉不影響句子語義和結構完整。《詮釋》所舉例證中的“后”都具有實義性,與例(19)中的情況不同。這些“而后”都只能歸為詞與詞的組合,不能歸為熟語。
3.而況
《詮釋》把“而況”分析為逼近關系復句第二小句上,具有表示“以深證淺”的功能,與口語“何況”相當。馬氏認為“‘而’若有‘又’字之意”,“而況”相當于“又況”[8]291-292,楊樹達云:“‘而況’中‘而’相當于‘猶、且’。”[12]461《詮釋》認為“而況”中的“而”為疑問代詞;《詞詮》則把“而況”中的“而”分析為副詞。這是由于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據(jù)意譯將“而況”解釋為“何況、且況”,沒有考慮詞的語法功能。馬氏一方面堅持“而”的連詞性,一方面又認為“而況”中的“而”相當于“又”,若有“又”字之意,表達模棱兩可。其實“而況”仍然是詞與詞的組合,“而”用來連接前后文,“況”表示遞進,用于引起下文。
根據(jù)漢語史規(guī)律,漢以前的“而況”都為連詞的連用[15],由于“而”和“況”都具有連接作用,其功能相互疊加;“而”的語法功能比“況”的更虛化,這迫使“而”丟失了其連接前后的語法功能,在魏晉南北朝時期[15]與“況”形成凝固結構,在連接前后文的基礎上,表示前后句之間的遞進關系;在唐朝又進一步變成標志遞進語義關系的合成連詞[16]。
(15)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于人之墻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墨子·天志下》)
上句中“而”用于連接“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和“況有踰于人之墻垣,抯格人之子女者”兩個小句;很明顯,“有踰于人之墻垣,抯格人之子女者”比“不與其勞,獲其實”這種情況更可惡,“況”位于第二個小句句首,用以表示這種遞進關系。由于“而”和“況”都是連詞,語義不實,又都用于連系前后句,所以《詮釋》把“而況”看作一個詞。但“而”和“況”語義功能不同:“而”單純表連接,去掉不影響語法語義理解;“況”除表連接外,表示后句與前句的遞進關系,用于強調后句,去掉后前后句關系不明顯,雖不影響語法結構,但影響句意理解。“而”雖然語義很虛,但它不依附于“況”而存在。“而”和“況”具有各自獨立的語法作用,不具備凝固結構的本質特征。
4.而已
謝氏將“而已”分析為“聯(lián)合式合義復詞”,做句末語氣詞,相當于口語“罷了”;有時在“而已”下加“矣”字,成“而已矣”,其意亦同。認為“而已”為“聯(lián)合式”,則本質上認為“已”同“而”一樣為虛詞。認為“而已”為“合義復詞”,則認為“而”已經不能獨立存在,與“已”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結合體,依附“已”而存在,這是不正確的。這里的“已”都為動詞,“停止”義,“而”有獨立的語法作用,用于連接前句和“已”,如:
(16)饉,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墨子·七患》)
(17)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墨子·兼愛上》)
例(21)“稟食而已矣”中,“而”用于連接狀語“稟食”和謂語動詞“已”。這里的“已”雖可翻譯為“罷了”,但從句法上分析,“已”在句中為動詞,充當句子謂語,不能分析為語氣詞。“而已”去掉之后,句子結構不完整。例(22)“具此而已矣”中,“而”用于連接“具此”和“已”兩個謂詞性結構,句中的“已”已經開始虛化,意義沒有例(21)中的意義實在,但仍為動詞,“而”為連詞。“而”和“已”具有獨立的語法功能,不能歸為語氣詞。與“然而”相反,“而已”是由于“而”前面的謂語結構漸漸變得復雜,前后不平衡;“已”用以表示“而”前謂語停止的狀態(tài),“已”的語義不斷虛化,最終迫使“而”丟失了聯(lián)系前后的功能,與“已”一起成為句末的語氣詞。
“而已”在戰(zhàn)國末期開始凝固,漢代進一步凝固,魏晉南北朝時期完全凝固,直到唐以后才變成表示限制語氣的合成詞[14]。《詮釋》認為《墨子》中“而已”已成詞,將“而已”的成詞時間提前了1000多年。
“而已矣”為凝固結構的前提是“而已”為凝固結構。經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而已”在《墨子》中只是詞與詞的連用,不是凝固結構,“矣”則為句末語氣詞,在“而已”變成語氣詞之后才與其后的“矣”“也”“耳”等形成了語氣詞連用。
結語
《詮釋》作為至今唯一一本對《墨子》中的虛詞進行系統(tǒng)分析的重要虛詞專書著作,為古漢語虛詞用法的規(guī)律總結做出了貢獻。由于我們現(xiàn)在的古漢語虛詞研究的理論體系尚不成熟,加之古漢語本身的靈活性強,同一虛詞、虛詞的同一用法可以有不同的表現(xiàn),稍不注意就會失誤,在所難免。“而”作為古漢語中一個出現(xiàn)頻率極大的虛詞,對其理解只能根據(jù)其本身的語法功能,而不能根據(jù)其前后實詞結構的語義關系、整個句型對其進行強賦實義,這必將會導致詞性分類駁雜多端,擾亂規(guī)律的總結。
通過對《詮釋》中的例證分析,“而”并不等同于“此、乃、如、才、能、以”等,它主要功能是連接前后兩個謂詞性結構,是連詞。這些謂詞性結構之間形成的語義關系紛繁復雜,不能據(jù)此改變“而”本身的語法功能和詞性歸類。謝氏根據(jù)“而”連接的謂詞性結構之間的不同關系,按照句型對其連詞功能進行了細密的分類,這是不必要的。通過“而”和典型介詞“以”的對比,我們認為“而”不具備介詞的語法功能,不能根據(jù)意譯將其解釋為介詞。
《詮釋》把與“而”共現(xiàn)頻率較高的“然而”“而后”“而況”“而已”“而已矣”歸為熟語,這忽略了語言發(fā)展的歷時性。《墨子》中大部分“然而”仍是兩個詞,與現(xiàn)代漢語中的“然而”大相徑庭;“而后”“而況”“而已”都是戰(zhàn)國末期才趨于凝固的,《墨子》中都只是詞與詞的組合。“而已矣”則是在“而已”成詞之后的語氣詞連用現(xiàn)象,并不能歸為熟語。
參考文獻:
[1]謝德三.墨子虛詞用法詮釋[M].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
[2]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畢沅.墨子[M].日本:靈巖山館影印經訓堂本,1835.
[4]孫詒讓.墨子閑詁[M].孫啟治,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
[5]吳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6]王念孫.讀書雜志·墨子第三[M].清道光十二年刻本.673.
[7]俞樾.諸子平議·卷十[M].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
[8]馬建忠.馬氏文通[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9]郭錫良.漢語史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0]王引之.經傳釋詞[M].長沙:岳麓書社,1984:157.
[11]楊樹達.詞詮[M].北京:中華書局,1954.
[12]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54:569.
[13]楊伯峻.古漢語虛詞[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4]陳寶勤.試論“而后”“而已”“而況”“而且”“既而”“俄而”“然而”[J].古漢語研究,1994(24).
[15]劉利.上古漢語的雙音節(jié)連詞[J].中國語文,2005(305).
[16]呂叔湘.文言虛字[M].北京:開明書店,1944:90.
責任編校:汪長林
A Discussion on the Word Classification of “Er (而)” inAnnotationsofFunctionalWords’UsagesinMozi
LI Sai-n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AnnotationsofFunctionalWords’UsagesinMoziby XIE De-san, “er (而)”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tial word like “ci (此)”, a copula like “nai (乃)”, a quasi like “ru (如)” and as an adverb like “nai (乃)” and “cai (才)”. “Er (而)” is also categorized as a preposition and a conjunction.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the word is to connect the two predicate structures, hence a conjunction. The book ignores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its categorization of “er (而)” is worth discussion. Most of the related structures inMoziare not fixed, and “erhou (而后)”, “erkuang (而況)”, “eryi (而已)” and “eryiyi (而已矣)” are word combinations. It is questionable to categorize them as idioms.
Key words:AnnotationsofFunctionalWords’UsagesinMozi; er (而); part of speech
中圖分類號:H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5-0079-06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5.019
作者簡介:李賽男,女,山東青島人,上海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4-15
網絡出版時間:2015-11-11 10:42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1111.1042.0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