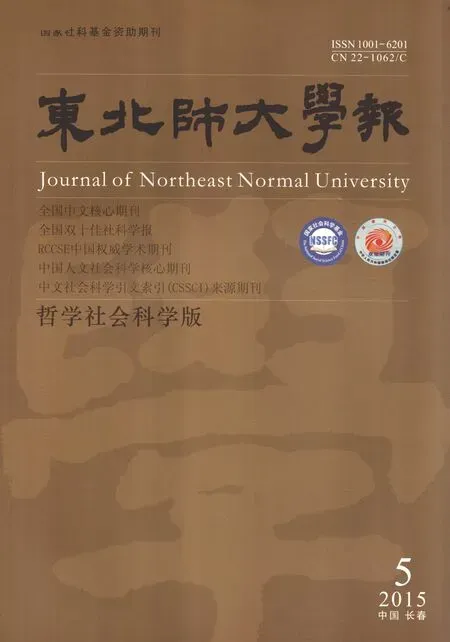穿越物化的“幻相”——盧卡奇辯證法的真實意蘊
雪 婷
(陜西師范大學 政治經濟學院,陜西 西安710119)
被譽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圣經”[1]的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正如它的副標題所言,是一部“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著作。眾所周知,盧卡奇的辯證法經常被人們冠以“歷史辯證法”、“總體辯證法”、“歷史實踐辯證法”、“歷史過程中的主客體辯證法”等名號,這些名號僅僅是為了突出盧卡奇辯證法的某個局部,還是對同一個內容的不同“稱謂”?如果是前者,這就遮蔽了盧卡奇辯證法的真實意蘊,重又陷入我們所批判的“細枝末節”中;如果是后者,這些不同的“稱謂”之間是什么關系?這是我們理解盧卡奇辯證法的癥結所在。事實上,這些不同的“稱謂”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突破與自然科學方法相契合的資產階級物化意識結構,穿越物化“幻相”重建被物化消滅的人。
一、物化意識結構:物化“幻相”產生的內在邏輯
面對實證主義“抹殺”辯證法的“挑戰”和庸俗馬克思主義“歪曲”辯證法的“危險”,馬克思辯證法面臨空前的危機。為什么馬克思的辯證法面臨如此大的“災難”?因為資本主義發展本身傾向于產生一種非常迎合自然科學方法的物化意識結構。正是這種物化意識結構,使人們喪失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把握,從而把持續生成的現實割裂為孤立僵硬的事實,并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獲得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這種對象性不僅切斷了勞動主體之間的有機聯系,而且掩蓋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所有痕跡,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幻相”。盧卡奇的辯證法就是針對這種物化“幻相”提出的。那么,這種物化“幻相”產生的內在邏輯是什么?
盧卡奇對物化現象的描述是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入手的,他把商品拜物教看作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問題。首先,盧卡奇從主客觀方面考察這種“物化”現象:“人自己的活動,人自己的勞動,作為某種客觀的東西,某種不依賴于人的東西,某種通過異于人的自律性來控制人的東西,同人相對立。更確切地說,這種情況既發生在客觀方面,也發生在主觀方面。”[2]152-153這種“物化”,不僅客觀上切斷人與勞動對象的自然關聯使物與物的現成世界與人相對立,而且主觀上使主體與自身相分離從而把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聯系都變成可計算的偶然聯系。由于這種“物化”根源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后者在主客觀方面都制約著商品中的抽象人類勞動,因而物化對應著“抽象的暴力”[3]292。
其次,受韋伯合理化思想的影響,盧卡奇不僅從主客觀方面闡述“物化”現象,而且深入剖析合理化原則對人靈魂的“侵蝕”——物化意識。在合理化原則的支配下,人們的勞動過程逐漸被分解為一些抽象的局部操作,工人由此變成機器的零部件,“隨著對勞動過程的現代‘心理’分析(泰羅制),這種合理的機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靈魂’里”[2]154。當這種合理性原則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時,處于機器鏈條上的工人就會失去對整個勞動過程的總體性把握只能對其采取一種直觀態度,這種態度侵入工人的心理結構并使其成為束縛人的“精神枷鎖”,“這種物化意識的出現將消解人的主體性,使人全方位地接受物的統治”[4]。
再次,合理化、規律化使資產階級的物化意識永久化為根深蒂固的物化意識結構。隨著勞動過程的日益合理化,人無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主觀上都喪失作為勞動主人的身份,因而對生產只能采取直觀態度,這種態度把時間降到空間的水平,即“時間空間化”。這樣,時間就凝固成一個精確的、可量化的“物”的連續統一體即空間,同時處于這種“物性”時間下的勞動主體也被分割為僵化的孤立原子,“在物化的意識看來,這種可計算性形式必然成為這種商品性質真正直接性的表現形式,這種商品性質——作為物化的意識——也根本不力求超出這種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過‘科學地加強’這里可理解的規律性來堅持這種表現形式,并使之永久化。”[2]161這種由可計算性形式不斷加強地物化意識結構不自覺地浸入人的意識,并使得人的肉體和心靈越來越屈從于這種物化。
最后,這種物化意識結構在哲學上的體現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兩難困境”。由于近代理性主義愈來愈發現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相互聯系,當理性主義要求成為認識整個存在的方法時,非理性問題就會起到瓦解整個“理性大廈”的作用,康德的“自在之物”就是這一非理性界限的典型。因此,對康德“自在之物”的克服就構成整個德國古典哲學的“主旋律”。康德從主體實踐出發試圖克服理論理性的內在局限,但普遍必然性的知識須以先驗的物質基礎為前提,這必然導致自然的必然性與個體的自由性之間相矛盾。費希特試圖把康德的“認識主體”轉化為“行為主體”并通過“正、反、合”的主體設定活動為康德的先驗辯證法注入活力,但最終陷入自我的“怪圈”。為解決這一問題,黑格爾從“實體即主體”出發把思維的主客對立納入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中,既把一成不變的概念溶入理性的自我運動中,又把所有的邏輯問題都建立在內容的物質特性上,這使得辯證法成為一種有內容的總體辯證法。但由于黑格爾的行為主體是先驗的世界精神,所以這種總體注定是抽象的。由此可見,從康德到黑格爾的整個德國古典哲學雖然已經把握到資產階級物化意識結構并試圖通過向內發展的道路加以克服,但由于它只是在思想上把這一矛盾推向極點,因而最終只能陷入“兩難困境”,“古典哲學本來要在思想上打碎形式理性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物化的)思想的局限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滅了的人,但在這種表面現象中,它的全部嘗試都化為烏有。思維重又落入主體和客體的直觀二元論的窠臼之中。”[2]235在盧卡奇看來,雖然德國古典哲學在試圖克服資產階級物化意識結構時陷入“兩難困境”,但它最大的理論貢獻是為我們穿越物化“幻相”奠定了堅實的辯證法基礎。
二、辯證的總體:如何從事實上升到現實?
盧卡奇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寶貴遺產”,從辯證的總體出發試圖把孤立的事實不斷提升為持續生成的現實。但是,“如何從事實上升到現實”直接關涉到盧卡奇辯證法的本質問題。實質上,盧卡奇的辯證法是辯證法的歷史與歷史的辯證法的統一、總體性的歷史與歷史的總體性的統一以及歷史的實踐與實踐的歷史相統一的“內在一致”,這是從“事實”上升到“現實”的根本路徑。
(一)歷史根基:辯證法的歷史與歷史的辯證法的統一
盧卡奇把歷史作為整個哲學的理論基石。在他看來,面對形式與內容的分裂,庸俗馬克思主義者不但沒有提出解決方案反而回避問題本身,其原因在于他們忽略了這些孤立事實的歷史性質。因此,我們要突破資產階級物化結構,就必須把辯證法奠定在堅實的歷史根基之上,“幾乎在每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后面,都隱藏著通向歷史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也就是通向解決問題的道路”[2]228,黑格爾哲學在這一點上邁開了決定性的一步,因為他發現了形式和內容統一的辯證中介即絕對精神的歷史運動。在這個意義上,辯證法的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主體與客體、自由與必然、內容與形式等所有僵硬的對立都溶解到歷史的長河中去了。
盧卡奇把黑格爾哲學的歷史傾向發揮到極致,既把社會生活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歷史問題,又揭示歷史發展的真正基礎是資本主義的內在對抗,與此同時他也識破黑格爾絕對精神表面上創造歷史的“概念神話”。在盧卡奇看來,真正的辯證法就是要剝離黑格爾的“絕對主體”,把形式與內容的對立置于總體性的現實歷史之中,這樣才能真正把握到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因此,盧卡奇的“歷史”是從孤立的“事實”上升為持續生成的“現實”的一把“金鑰匙”。
但是,盧卡奇的“歷史”,既不是黑格爾抽象的“理性運動”,也不是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辯證法的歷史,“如果擯棄或者抹殺辯證法,歷史就變得無法了解。”[2]62這種“歷史”是人一連串的活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所有關涉形式與內容等二元對立的問題都將得以解決。同時,盧卡奇的辯證法既不是脫離歷史的自然辯證法,也不是超越歷史的“絕對精神”運動,而是歷史本身的辯證法,因為“辯證法來自歷史本身,是在歷史的這個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的表現形式,并被人們所認識。”[2]273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奇把辯證法與歷史看作同一個過程。因此,盧卡奇辯證法的歷史根基是辯證法的歷史與歷史的辯證法的統一。
(二)具體的總體性:總體性的歷史與歷史的總體性的統一
在盧卡奇看來,以歷史為根基的辯證法的本質是“具體的總體性”。實證主義者運用自然科學方法把整個社會看作永恒不變的自然規律,這使得人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呈現出一種支離破碎的物化狀態從而遮蔽了活生生的社會現實。盧卡奇辯證的總體則是在思維中把握活生生現實的唯一手段,因為“辯證法不顧所有這些孤立的和導致孤立的事實以及局部的體系,堅持整體的具體統一性。”[2]55雖然我們對現實的一切認識均從事實出發,但是我們并不停留于這些孤立事實,而是把它們置于一個歷史的總體中并使其成為現實的一個環節,這樣我們的認識才能從孤立的“事實”不斷上升為持續生成的“現實”。
黑格爾雖然最早運用具體的總體,但由于他的“總體實際上就是一種絕對”[5],因而它的內容仍帶有“永恒價值”的傳奇性殘余。與黑格爾超驗的總體不同,盧卡奇“具體的總體”是對活生生的歷史統一性的理解,是“歷史地(因而在現實中)帶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6],因而是歷史的總體性。面對同樣的社會現實,當資產階級運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社會矛盾棄之不顧時,盧卡奇的辯證法卻以此為出發點并將其揚棄于歷史的總體性中以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趨勢,“資本主義的最后繁榮由于其基本問題放進了整個歷史過程中,而具有了一種可怕的‘死亡之舞’。”[2]86這是盧卡奇具體的總體性最具革命性的一面。
盧卡奇辯證法的本質不僅是歷史的總體性,而且是總體性的歷史,因為“總體的觀點,把所有局部現象都看作是整體——被理解為思想和歷史的統一的辯證過程——的因素”[2]80。與資產階級把社會發展的各環節都變成同等數量的“事實群”不同,盧卡奇“具體的總體性”,既不把歷史發展的各環節歸結為無差別的社會同一性,也不是這些歷史環節的外在“堆砌”,而是把這些環節置于歷史發展的辯證運動中,從而使各個環節的具體可能性不斷上升為社會發展的現實性。由此可見,盧卡奇辯證法的本質是總體性的歷史與歷史的總體性的內在統一。
(三)改變現實:歷史的實踐與實踐的歷史的統一
盧卡奇以歷史為載體、以“具體的總體性”為內容的辯證法,其目的在于通過實踐突破資產階級的物化意識結構,因為實踐按其本質,“是對現實的沖破,是對現實的改變”[2]94。與恩格斯規避各種干擾因素的工業實踐不同,盧卡奇的辯證法不僅使無產階級從總體上把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對抗,而且使其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和自身存在的非人性,這促使無產階級摒棄直觀態度轉而采取一種革命實踐態度,“在一切形而上學中,客體,即思考的對象,必須保持未被觸動和改變,因而思考本身始終只是直觀的,不能成為實踐的;而對辯證方法說來,中心問題乃是改變現實”[2]51。
盧卡奇的實踐不僅是歷史的實踐,而且是實踐的歷史。與德國古典哲學家極力推崇的倫理實踐不同,盧卡奇“改變現實”的實踐活動,不僅認識到德國古典哲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對抗,而且將其看作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動力。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奇的實踐與辯證法的歷史息息相關。因為這種實踐,既不是超歷史的理想環境中的“抽象實踐”,也不是康德、費希特意義上的倫理實踐,而是活生生的歷史實踐活動;這種歷史,既不是個別歷史事實的疊加,也不是脫離實踐的精神運動,而是實踐活動的最終產物。因此,盧卡奇“改變現實”的辯證法是歷史的實踐與實踐的歷史的內在統一。
由此可見,盧卡奇以歷史為根基,以具體的總體為本質、以改變現實為己任的辯證的總體,真正把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運動,這是一個比任何物化的經驗世界更高的過程。這一過程不是一個超驗的過程,而是現實世界中“我們”創造的結果,“如果我們可以把全部現實看作為歷史(即看作為我們的歷史,因為別的歷史是沒有的),那么我們實際上使自己提高到這樣一種立場,在這種立場上,現實可以被把握為我們的‘行為’。”[2]231這個創世的“我們”就是無產階級。由于盧卡奇的辯證法始終圍繞無產階級的現實命運而展開,而工人只有經歷無產階級意識這一環節才能成為歷史的主客體,因此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是盧卡奇辯證法的必由之路。
三、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盧卡奇辯證法的必由之路
為什么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處于同一種物化現實,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卻獨具革命性?這是由兩個階級在生產過程中的特殊地位決定的。資產階級一方面作為物化的客體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作為表面的主體而存在,這種雙重存在使他們對生產只能采取一種純直觀的態度,這種從量上把握對象的方式只能形成一種虛幻意識。相反,無產階級自它產生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一種“物化意識”,這既加速了工人與其個性的分離使其淪為一種商品,又迫使其成為被量化的純粹客體。由于它的“靈魂”并沒有變為商品,這表明無產階級身上還存在尚未被資本主義克服的力量,這構成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生成的起點。數量化是蒙在客體上的物化外衣,而作為歷史主客體的無產階級自身蘊含著一種質的變遷,這是無產階級作為商品的自我意識存在的根源。盧卡奇的辯證法就是要使無產階級自覺地意識到:只有消除這種直接存在的虛假形式,才能作為真正的階級而存在。
直接性和中介作為辯證過程的兩個因素是內在統一的。存在的每一個既定客體都具有現象學意義上的直接性,而超越這種直接性就意味著創造。中介范疇是從直接現實性通達客觀現實性的“橋梁”,每一種中介必然產生一種立場。資產階級運用自然科學方法把現實分解為一大堆孤立的事實并將其置于抽象的規律之下,這必然導致歷史與起源相分離。相反,無產階級卻能超越這種直接性,因為它通過中介范疇不僅能從總體上把握到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而且能意識到自己存在的辯證本性,這對于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至關重要,“對無產階級來說,自我意識到自己存在的辯證本質乃是一個生命攸關的問題。”[2]256
只有當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從資本主義的現實矛盾發展而來時,無產階級意識才能成為過程本身的意識,無產階級改造現實的實踐才能發揮它的威力。但無產階級即使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也不可能一下子從實踐上消除所有的物化形式。因為無產階級意識作為“主體”過程的真理本身是辯證過程本身的意識,“只有當歷史的過程迫切需要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發生作用,嚴重的經濟危機使這種階級意識上升為行動時,這種階級意識的實踐的、積極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質才能顯示出它的真實形態。”[2]96因此,無產階級意識的實踐本質在于它不斷生成的歷史性,這種歷史性通過中介范疇超越物化意識從而把握到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力量。由于盧卡奇正是發現了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革命性,所以才反復強調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把自身的命運作為整個人類的命運來對待,只有無產階級意識才能自覺到革命實踐。
四、思想“悖論”:盧卡奇辯證法的歷史限度
毫無疑問,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在辯證法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無論對于恢復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本質,還是對于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熱情,都有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當時,一場重大的、世界歷史性的轉變正在努力尋找一種理論表述”[2]21。但是,由于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自身存在“悖論”[3]360:它把勞動對于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看作物化的根源,但是卻把“克服”這一根源的辯證法置于形式上的從屬層面,這決定了盧卡奇的辯證法具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盧卡奇辯證法的黑格爾色彩過于濃重。雖然盧卡奇試圖通過恢復黑格爾傳統狠狠地打擊機會主義者,但是在尋求突破資產階級物化意識結構的歷史主體時卻把無產階級作為歷史的主客體,這是一種“比黑格爾更加黑格爾的嘗試”。具體而言,盧卡奇在闡述馬克思辯證法的過程中雖然力圖超越黑格爾的“概念神話”并試圖與其劃清界限,但在涉及階級立場與無產階級意識的關系問題時,卻又不自覺地運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這是他無法擺脫黑格爾的根本原因。
二是盧卡奇對實踐的理解過于抽象。盧卡奇對于辯證法的強調不是一種理論抽象,而是始終與工人實踐密切相關,但是由于他的辯證法難以擺脫黑格爾的“陰霾”,這決定了他改變現實的歷史實踐注定是抽象的,因為這里的實踐主體是“無產階級及其意識”。這種把主體的階級意識等同于主體自身的做法,不可能完成“沖破”現實的實踐任務。
三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與階級意識之間缺乏現實中介。無產階級立場的根本內涵是突破“被賦予的意識”把人與人之間的真實聯系從物與物的關系中解放出來,而這以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實踐為前提。如何彌合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與階級意識之間的鴻溝就成為盧卡奇辯證法的理論“難題”。盡管他在后期試圖通過勞動及再生產彌合這一鴻溝,但由于缺乏一系列可操作的現實中介環節,因而只能不自覺地通過黑格爾的“反光鏡”來理解馬克思,從而使馬克思的辯證法退回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巔峰”。
由于這些理論局限,盧卡奇的辯證法遭到來自法蘭克福學派和當代激進左翼思想家的廣泛質疑,但無論是法蘭克福學派對盧卡奇無產階級意識所可能導致的極權主義的批判,還是當代激進左翼思想家(齊澤克)對盧卡奇革命道路的推崇,都從不同角度詮釋了盧卡奇辯證法的魅力至今猶存。
[1] Maurice Merleau-Ponty.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M].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7.
[2] [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 衣俊卿,周凡.新馬克思主義評論(超越物化的狂歡)盧卡奇專輯[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4] [德]弗洛姆.在幻想鎖鏈世界的彼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61.
[5] 張一兵.文本的深度耕黎——西方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解讀:第1 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4.
[6] [匈]盧卡奇.盧卡奇自傳[M].杜章智,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