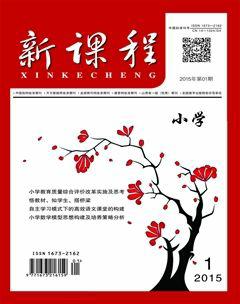從學(xué)生那里出發(fā)
陸小靜
對(duì)于教學(xué)設(shè)計(jì),新老師總是容易犯這樣一些錯(cuò)誤:沒(méi)有目標(biāo)意識(shí);在知識(shí)點(diǎn)中游離,抓不住重點(diǎn);有了目標(biāo)卻沒(méi)有方法等。對(duì)于這樣的情況,我做了一些思考:
一、站在學(xué)生的那邊,讓學(xué)生走到最近的發(fā)展區(qū)
我們常說(shuō),三種知識(shí)不需要在課堂上教給學(xué)生:一是學(xué)生已經(jīng)會(huì)的;二是教給學(xué)生仍不會(huì)的;三是學(xué)生通過(guò)自學(xué)能夠掌握的。這與前蘇聯(lián)著名心理學(xué)家維果斯基提出的“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的理念不謀而合。我們的課堂教學(xué)應(yīng)著眼于學(xué)生的最近發(fā)展區(qū),設(shè)計(jì)一些有難度、但在教師的引導(dǎo)下又能被解決的問(wèn)題,使學(xué)生潛能得到最大化的發(fā)揮。明白了這一點(diǎn),那么我們便會(huì)從學(xué)生的已有經(jīng)驗(yàn)出發(fā),從學(xué)生的角度來(lái)思考,這對(duì)于教學(xué)過(guò)程中知識(shí)點(diǎn)的取舍、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的設(shè)計(jì)會(huì)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新課標(biāo)指出,語(yǔ)文課程是一門學(xué)習(xí)語(yǔ)言文字運(yùn)用的綜合性、實(shí)踐性課程。因此在設(shè)計(jì)教案時(shí),我們會(huì)有意識(shí)地找到語(yǔ)言訓(xùn)練點(diǎn),幫助學(xué)生學(xué)會(huì)語(yǔ)言、語(yǔ)用。但是,我們要時(shí)刻謹(jǐn)記,我們所設(shè)計(jì)的語(yǔ)言訓(xùn)練點(diǎn)應(yīng)是貼近語(yǔ)言文字的訓(xùn)練點(diǎn),應(yīng)是切實(shí)貼合學(xué)生的學(xué)情,而不是為了讓課堂顯得有設(shè)計(jì)感而去設(shè)計(jì)。教學(xué)設(shè)計(jì)要從學(xué)生的角度去思考,貼近他們的最近發(fā)展區(qū),跳一跳能夠獲得的“果子”才是我們應(yīng)該要教給學(xué)生的知識(shí)點(diǎn)。
二、把課文當(dāng)作例子,用教材教
大學(xué)時(shí)上《教學(xué)論》,教師總說(shuō):“我們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確實(shí)如此,在很多時(shí)候,我們都針對(duì)課文,也就是教材來(lái)設(shè)計(jì)教案,然后循規(guī)蹈矩地傳授學(xué)生這一課的知識(shí)。然而過(guò)段時(shí)間我們卻發(fā)現(xiàn),當(dāng)學(xué)生遇到同一類型的文章,他們?nèi)匀皇譄o(wú)策。就這樣,我們的教學(xué)設(shè)計(jì)仿佛一直在被教材牽著鼻子走。我想應(yīng)該是我們把教材的角色定位錯(cuò)了,我們要交給學(xué)生許多的知識(shí)與技能、過(guò)程與方法、情感態(tài)度與價(jià)值感,而教材只不過(guò)是一種媒介、只不過(guò)是一個(gè)載體。我們要做的是要站在教材的制高點(diǎn),學(xué)著去運(yùn)用它。
我們常說(shuō)“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作為一名教師,我一直認(rèn)為傳授方法比傳授知識(shí)更為重要。就拿小學(xué)語(yǔ)文階段的文章體裁來(lái)說(shuō),基本上可以分為寫景、狀物、敘事。而教師則要總結(jié)歸納出每一類型的文章不同的特點(diǎn),就拿講授故事這一類的體裁來(lái)說(shuō),我們可以告訴學(xué)生故事一般都可以分為三個(gè)部分:起因、經(jīng)過(guò)、結(jié)果。在讀一個(gè)故事的時(shí)候,我們可以從這三個(gè)方面去理清文章脈絡(luò),這也有利于學(xué)生的理解、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