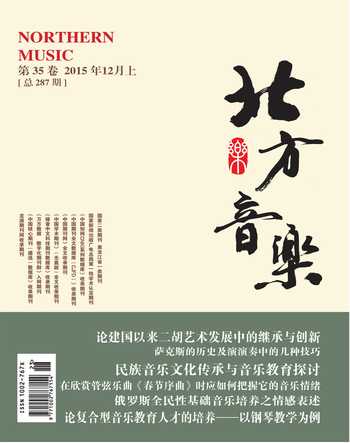中國多聲部民歌中的線性思維
陶文青


【摘要】民歌創作、表演的口頭性、即興性,決定了其傳承的變異性,而這與音樂理論的相對穩定性、科學性、系統性有所不同。因此,植根于單聲部民歌,或說變異于單聲部民歌基礎上的我國多聲部民歌,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單聲部民歌的變體,是多聲部音樂的非自覺狀態,是中國多聲音樂的雛形與重要基礎。
【關鍵詞】線性思維;民歌;傳承;自覺
我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民族眾多,產生了由單純民族音樂及多民族雜居的音樂文化共存的獨特與繁榮局面,這其中產生了大量民歌(包括單聲部與多聲部民歌),收集、整理、研究我國多聲部民歌音樂形態成為發展我國多聲音樂文化的重要前提。
就總的發展規律來看,音樂總是遵循單聲部在前、雙聲部及多聲部在后的發展規律。民歌產生于民間,多為勞動人民集體創作,口頭性、即興性成為其重要特征,民歌成為我國民族民間音樂文化傳承、發展、繁榮的重要載體。民歌創作、表演的口頭性、即興性,決定了其傳承的變異性,而這與音樂理論的相對穩定性、科學化、系統化有所不同。因此,植根于單聲部民歌,或說變異于單聲部民歌基礎上的我國多聲部民歌,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單聲部民歌的變體,是多聲部音樂的非自覺狀態,是中國多聲音樂的雛形與重要基礎。就音樂的多聲理論而言,它并非是一種非真正意義上的自覺行為,大多是一種對音樂的直覺,對音樂的整體把握能力。因此,就中國多聲部民歌的創作而言,它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偶然行為,但它是我國多聲部音樂創作的重要源泉與依據。
中國多聲部民歌的出現總是與單聲部民歌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因此,從多聲部民歌的構成形式看,總會顯露出一些單聲的因素在其中,其實這也就是中國多聲部民歌織體構成中的線性思維的具體表現所在。
我國多聲部民歌的線性思維主要體現在各聲部的構成關系、節拍節奏形式、調式與調性、織體形式、和聲特點等方面。
在調式調性方面,我國多聲部民歌各聲部可能有時運用的調式會不同,如不同調式的縱向結合、不同音階類型的縱向結合、不同調性的結合等,大多是單聲部民歌的變異。換句話說,這也是我國多聲音樂由偶然走向必然的一個必經過程。在調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各聲部之間縱向調式滲透問題。各聲部由于運用不同的調式骨干音,出現了使調式色彩豐富、變化的現象,如廣西環江毛南族民歌《毛南人民見新天》即屬同宮系統不同調式的縱向結合,是宮、羽兩個調式縱向相互滲透的結果。(見譜例1)平行性的宮商大二度關系的調式重疊、局部性的調的重疊(大致屬同宮結束主音同系統內)、平行式調式重疊如平行五度(如流行于福建東部寧德縣與霞浦縣部分山區畬族中的“雙條落”)。其中經常自然出現的不同起同收的模仿復調,其實就是單聲部旋律的變異。實際上,它體現的主要是一種旋律的橫向進行,是同一條旋律在兩聲部中不同時間先后出現的結果。因此,這其間兩聲部的結合必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畬族的平行式調式重疊如平行五度這已經不是單單的各行其是了,上下兩聲部間有了相互的照應,已經向聲部間有規律的結合方向邁進,但它依然經歷由各聲部各行其是這樣一個過程。)從同宮系統各聲部的結合由不同調式的重疊到相同調式但不同主音的調式重疊的過程,是人們對僅僅由線性思維方式產生的多聲音樂已不能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的結果,也是經由偶然、直覺之后的必然行為。
由某一問題會引發與其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由于我國多聲部民歌各聲部之間存在縱向調式滲透現象(如上文提到的平行性的宮商大二度關系的調式重疊、局部性的調的重疊、平行式調式重疊等),相應地,在織體構成方面也顯現出線形思維特征。線性思維在我國多聲部民歌中織體形式方面的表現,其實與其在調式調性中的表現大同小異。以產生于我國湖南江華縣的“蝴蝶歌”為例,其織體形式便采用了我國民間多聲部音樂中一種常見的織體形式——支聲體。支聲體中每個聲部曲調基本來源于同一曲調,曲調大體相似或略有變化,從《不唱條歌難過日》中“齊唱”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這一特征。(見譜例2)
但從其間存在很多二度和聲音程關系這一現象,也可窺見我國民族和聲、多聲音樂的發展方向及線索。另外,我國多聲部民歌中的線性思維在部分復調型織體中也有體現,如屬整體性模仿類型、大多由同度模仿構成的畬族的“雙條落”; 以領、和或先、后方式演唱的漢族勞動號子。這里的模仿基于單聲旋律,但也存在了縱向的對比因素,只是相對于對比模仿等織體對比度弱些。⑴由于模仿式織體的存在,導致了節拍重音的錯位現象,這給記譜帶來一定難度。實際上這種節奏節拍上的復合實質也是線性思維的結果。
中國的多聲部民歌的土壤源自民間,中國多聲部音樂有深厚的民間基礎。線形思維是我國多聲部民歌的重要特征,這也是中國多聲部音樂不及西方發達的重要原因。究其具體原因,其一主要體現為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方面。不同的思維方式產生、孕育不同的音樂形態。各國人的思維方式由各國哲學基礎決定。西方人思維方式主要建立在對立面的基礎上,而我國人的思維方式則建立在對自身的思考與完善方面,前者帶來了西方高度發達的自然科學、科技的高度發達、繁榮,促進了西方文明,但同時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我國人的思維方式大大提升了中國人的整體觀與直覺力;同時,又顯現出對事物的縱向研究缺乏深度的弊端。
此外,我國早期民歌記譜法的繁瑣、非科學化也是制約民歌傳播乃至多聲部民歌發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民間音樂的口頭傳承及變異性特點,我國民歌樂譜的記寫方式多采用非書面記號譜及書面記號譜中的文字譜(如律呂譜、工尺譜),這給民歌的完整傳播帶來一定難度,傳承的范圍自然也會相對縮小。用于記錄苗族民歌的結帶譜即為一種非書面記號譜,其記譜方式是以六種不同顏色的布條表示六種音高,用打結布條長短表示音符實值,以金色細紋的布條打結表示任意休止。⑵這種記譜法雖然已經包含了對音的高低,長短、休止的記錄,但是對于不了解苗族音樂文化及記譜規律的人讀此譜會產生無從下手,根本無法讀懂其間真正記寫內容的困惑。再如我國最早記錄《詩經》的樂譜——律呂譜曾對《風雅十二詩譜》中“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過如下記譜:“黃南林南,黃姑太黃,林南黃姑,黃林南黃” ⑶這一由律呂譜所作《風雅十二詩譜》,對我國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十五國民歌的傳承提供了珍貴音樂資料,但由于律呂譜記譜法的繁瑣,也為民間音樂進一步流傳帶來一定困難。以上所講僅僅就單聲部民歌的記錄而言,多聲部民歌的記寫、讀寫難度可想而知了。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記譜法的不完備或多樣性給音樂的傳播帶來了難度。相對于我國記譜法而言,歐洲最早的記譜法——拜占庭圣歌記譜法,記錄旋律的方式是音程記號,發展到格利高里圣歌記譜法、圣母院派記譜法、定量記譜法、到現代的五線譜記譜法,基本遵循了一條主線、一個體系——音符譜的逐步完善、系統化與科學化,這無疑對西方多聲音樂的發展、發達與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國有著豐富的民間音樂資源,作為民族民間音樂基礎的民歌更為多姿多彩,發現、整理、傳承、發展我國民歌文化,成為我國音樂文化發展的重要前提。在這方面,我國著名音樂家樊祖蔭先生已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卓絕的努力。民間音樂文化是每一個國家音樂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是世界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珍視民間音樂是一個國家音樂文化發展的重要標志。要克服我國多聲民歌中由線性思維帶來的各種偶然性弊端,只有注重理解其中的單聲因素,研究偶然背后的必然,才能大力弘揚我國民族民間音樂文化,推動我國多聲音樂的發展,更好地推動我國音樂理論、創作的科學化、系統化。這需要更多的專業音樂工作者及社會各界的介入、大力支持與協助,這行為本身是人們珍重本國文化、本土文化的重要表現。
參考文獻
[1]樊祖蔭,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論 [M].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
[2][3] 王耀華等,中國傳統樂譜學[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