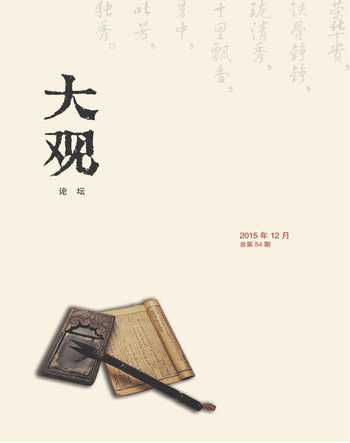從趙五娘形象塑造看越劇《琵琶記》對南戲《琵琶記》的改編
陳苗苗
摘要:趙五娘是南戲《琵琶記》中主要的女性形象。越劇《琵琶記》與南戲《琵琶記》在這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存在較大差別。越劇《琵琶記》將南戲《琵琶記》中趙五娘“孝婦”和“怨婦”共時共存的形象分時期表現。從女性形象塑造來看,越劇《琵琶記》對南戲《琵琶記》的改編有得有失。
關鍵詞:趙五娘;形象;改編
一、引言
越劇《琵琶記》是浙江小百花越劇團于1999年演出的一出戲,由郭漢成與譚志湘合作改編自南戲《琵琶記》而來。高明所作的《琵琶記》被譽為傳奇之祖,是我國古代戲曲中的經典。
趙五娘是劇中主要的女性人物,對比越劇《琵琶記》與南戲《琵琶記》,筆者認為在這位女性的形象塑造上,越劇《琵琶記》與南戲《琵琶記》存在較大差別。在趙五娘的形象塑造上,南戲《琵琶記》將“孝婦”和“怨婦”同時呈現在觀眾面前,而越劇《琵琶記》則將“孝婦”和“怨婦”分時期表現出來。
二、趙五娘的形象改編
趙五娘是我國古代戲曲中塑造的孝婦賢妻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南戲《琵琶記》的順序是五娘勸解公婆爭吵;蔡婆埋冤五娘;五娘吃糠,采用雙線結構,與以蔡伯喈在京為線索的故事穿插表現。越劇《琵琶記》在場景的順序上對南戲《琵琶記》做了調整,將五娘吃糠;蔡婆冤枉五娘;勸解公婆爭吵這幾個場景按順序集中起來重點表現趙五娘孝婦賢妻的形象,而后對取孝帕和五娘伯喈相會這兩個場景做了濃墨重彩的表現,主要表現趙五娘“怨婦”的形象。
在越劇《琵琶記》中,趙五娘的形象有明確的時期變化。在進京尋夫之前,趙五娘是一個“孝婦”的形象。陳留饑荒,趙五娘為了讓公婆多吃幾餐薄粥,自己用糠充饑。蔡婆誤以為五娘獨自在吃米,冤枉了五娘,誤會化解之后,五娘非但沒有覺得冤屈反而還勸解公婆爭吵。而當婆婆被糠給噎死表明糠難以下咽,為五娘吃糠這個舉動表現出來的孝心更添重色。當公婆相繼去世后,五娘也只是呼喊著“伯喈,你回來,你回來呀。”至此,趙五娘呈現給觀眾的是一位孝順、賢德的婦女形象。進京之后,趙五娘“怨婦”的形象逐漸表現出來在“取孝帕”場景中,五娘道:“取孝帕,取孝帕,千悲萬恨心痛煞。這孝帕是公公至死不閉的一雙眼,這孝帕是婆婆聲聲喚兒早歸家。這孝帕浸透蔡門血和淚,這孝帕沾著陳留風和沙。這孝帕如何取得下?”照鏡子準備取下孝帕時,五娘不忍看自己的容顏,“鏡中的人兒叫人怕,猶如枯枝萎地花。饑荒歲月催人老,苦難無情刻面頰。如今是紅顏喪盡人憔悴,怎及她金屋供養富貴花”,她怨牛小姐“既嫁蔡郎為蔡婦,緣何不認他爹娘;既嫁蔡郎為蔡婦,緣何不允他回家;既嫁蔡郎為蔡婦,卻緣何害蔡郎。生不養,死不葬,麻布披,孝不戴,天倫有虧,情理有差,手捧孝帕要問問她”,這是五娘有對自己容顏變化的幽怨,也有對公婆沒有兒子盡孝送終的幽怨,她怨恨牛小姐,她認為是牛小姐耽誤了蔡伯喈回家。在書館里,五娘與蔡伯喈相見,心中的幽怨又起:“說什么滿面羞愧對賢妻,分明是榮華富貴難舍棄。琵琶已是無情物,落得個千里尋夫奉還你。物是人非徒悔恨,倒不如等你盼你滿頭白發老死在故里”,繼而怒摔琵琶,這時五娘心中的怨恨達到極致。
南戲《琵琶記》中的趙五娘幾乎是“孝婦”和“怨婦”形象相伴而行的。在蔡伯喈赴試之前,趙五娘就有幽怨之情。在第五出“伯喈夫妻分別”中趙五娘多次向蔡伯喈表達自己心中的“怨”:“你爹行見得你好偏,只一子不留在身畔。我和你去說咱。休休,他只道我不賢,要將你迷戀。苦!這其間怎不悲怨?”[1]“妾的衷腸事,萬萬千,說來又怕添縈絆。六十日夫妻恩情斷,八十歲父母如何展?教我如何不怨?”[2]在蔡伯喈走后,在趙五娘在家侍奉公婆這條線中更是每一出戲里都有五娘的“怨”:在第十出“五娘勸解公婆爭吵”中,開頭趙五娘就道:“長吁氣,自憐薄命相遭際。相遭際,晚年舅姑,薄情夫婿”[3],但縱使自己心中有千般怨恨,見公婆爭吵,五娘還是要去勸慰。在第十六出“五娘請糧被搶”中,五娘被人騙萌生“我終久是個死,這里有口井,不如投入井中死”[4]的想法,想要投井自盡但又想到二老會因此招致速死,遂強忍住內心的苦。在第十九出“蔡婆埋冤五娘”,第二十出“五娘吃糠”,第二十四出“五娘剪發買發”中,五娘同樣表現出自己內心的幽怨:“高堂父母老難保,上國兒郎去不還。力盡計窮淚亦竭,淹淹氣盡知何日?空原黃土謾成堆,誰把一抔掩奴骨?”[5]“縱然不死也難捱,教人只恨蔡伯喈······我千辛萬苦有甚情懷?可不道我臉兒黃瘦古如柴。”[6]“思量我生無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饑為怨鬼。公婆年紀老,靠著奴家相依倚,只得茍活片時。片時茍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謾把糠米來相比,這糠尚兀自有人吃,奴家骨頭,知他埋在何處?”[7]在五娘的哀怨里,我們看到是走過一個苦難之后是另一個苦難,在她的哀嘆里看不到希望,表現出五娘在外部生存環境和內部心理的雙重壓力下生存,舉步維艱。就在這樣舉步維艱的境地里,趙五娘還要克制住內心的幽怨,護公婆周全,“孝婦”的形象也自然突顯出來。
三、人物形象改編的思考
筆者認為越劇《琵琶記》對趙五娘形象的改編沒有原作南戲《琵琶記》所塑造的趙五娘形象帶給觀眾的震撼強大。首先越劇《琵琶記》將趙五娘“孝婦”形象用了幾個典型的情節集中展示出來,而“怨婦”的形象只用了兩個場景展示出來,相對的怨婦的形象被弱化了。其次在南戲《琵琶記》中趙五娘的“怨”是沒有傾訴的對象的,她處在心中的幽怨無法擺脫卻又要強忍著苦和淚去盡心盡力侍奉公婆這樣的狀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見其心理壓力之大,而她又能強忍著怨恨去勸解公婆、吃糠、剪發賣發可見其隱忍的性格。“孝婦”與“怨婦”形象的共時共存使得趙五娘身上隱忍性格得以表現,使得趙五娘所受的苦難在觀眾看來愈加沉重,其形象亦愈深入人心。而在越劇《琵琶記》中“怨婦”的形象塑造被安排在進入牛府之后,她可以對著蔡伯喈、牛小姐怨,她的幽怨有傾訴的對象。又由于情節的安排實際上在觀眾心里早就對趙五娘的遭遇產生了同情之心,也被她的孝道感動,因此在此時趙五娘的“怨”在觀眾看來是一種長久以來積壓在內心的苦痛的正常發泄,并不能完全表現其性格之隱忍。相比較南戲《琵琶記》所塑造的趙五娘的形象性格更加豐富,更能打動人。
【注釋】
[1][2][3][4][5][6][7]高明:琵琶記[M].錢南揚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7頁,39頁,72頁,104頁,117頁,118頁,121頁
【參考文獻】
[1][元]高明:琵琶記[M].錢南揚.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中國戲劇家協會,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影視部:越劇電視藝術片·琵琶記·中國古典南戲[CD].杭州:浙江文藝音像出版社.1999.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