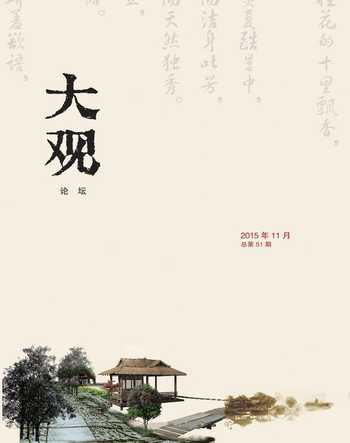淺談簡?愛與子君形象的異同
摘要:夏洛蒂·勃朗特《簡·愛》中的女主人公簡·愛和魯迅《傷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分別是中西文學史上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她們都為了愛情不惜反抗社會,二者卻最終結局不同。文章從簡·愛和子君的形象出發,對簡·愛和子君形象的異同進行了綜合探討,以窺其不同結局的原因。
關鍵詞:簡·愛;子君;形象;異同
簡·愛一直被認為是西方女性解放的典型代表,是一個敢于在男權社會中爭取男女平等、追求自由愛情的獨立女性形象,最終她成就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佳話。子君為了追求自由的愛情敢于與親情決裂,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大膽地與涓生過起未婚同居的生活,然而卻是以悲劇收場。這讓人不禁感嘆:同樣是女子對戀愛自由的大膽追求,為何卻是不同的結局?文章從文本出發,對簡·愛與子君形象的異同進行分析,試圖以此找出答案。
一、性格上的叛逆和抗爭
簡·愛的性格具有叛逆性和抗爭性。這種叛逆和抗爭,在她小時候便已表現出來。書中描述到:“簡·愛感覺有血從頭發上掉下來,順著脖子流了下來,痛楚立刻刺激了簡·愛的叛逆和抗爭,壓制了簡·愛的恐懼,簡·愛瘋狂的反擊。”由此可知,簡·愛的叛逆和抗爭是骨子里散發出來的,是天生就有的。而簡·愛和羅切斯特的愛情,是她叛逆和抗爭性格的爆發點。簡·愛貧窮、低微、矮小,長相平平,在她身上似乎沒有任何閃光點,與高富帥的羅切斯特似乎也并不匹配,但她并沒有自慚形穢。在她看來,每個人的靈魂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在愛情面前也應當是平等的,不應該將其和地位、金錢、長相等捆綁。文中她這樣說到:“難道就因為我一貧如洗,默默無聞、長相平庸、個子瘦小,就沒有靈魂,沒有心腸了?——你不是想錯了嗎?——我的心靈跟你一樣豐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樣充實!要是上帝賜予我一點姿色和充足的財富,我會使你同我現在一樣難分難舍,我不是根據習俗、常規,甚至不是血肉之軀同你說話,而是我的靈魂同你的靈魂在對話,就像我們兩個人穿過墳墓,站在上帝腳下,彼此平等——本來就如此!”
子君亦是如此。為了愛情她不顧家人的勸阻,甚至與家人決裂,毅然決然地跟涓生同居,而同居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民國時期,許多家長們還有著濃厚的封建主義傳統思想,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婚姻之事,依舊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然而子君敢于同幾千年來的封建禮教和權威進行挑戰,“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豪言壯語,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縛與涓生相愛,毅然決然地和涓生未婚同居,這是她的叛逆和反抗。在與涓生同居過程中,對于別人不壞好意的窺探,她毫無懼色,“目不斜視地驕傲地走了”。為了自由的愛情,她以一種決絕的態度來對待世俗的排斥和非議。
但子君的反抗卻是暫時的、軟弱的。為了愛情,她堅持和涓生在一起,但也僅僅是為了愛情,再多也就是當時思潮對于人的一種鼓動和影響,可以說她是一個面對愛情和新思潮產生反抗叛逆情緒的人,她的叛逆和反抗是一時的。而簡·愛則是一個骨子里就有叛逆和抗爭性格的人,她的叛逆和反抗是終其一生的。正是這種不同的叛逆和抗爭,成為了兩位女主人公不同結局的原因之一。
二、內心的堅強與脆弱
人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簡·愛和子君的人生也無可幸免,但兩位女主人公在面對生活中的挫折時,卻表現出不一樣的人生態度。當簡·愛發現自己愛上了羅切斯特時,物質、地位的懸殊并不能阻礙她的愛。當確定了彼此心意時,她果斷地愛了下去。而當她知道羅切斯特還有妻子時,她主動選擇了離開,并積極地另謀新生活。簡·愛的離開不是愛情的結束,而是給愛自由。離開后她并沒有頹廢,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沒有停止追求愛情的腳步,她與羅切斯特的圓滿結局就是最好的證據。子君在碰到愛情挫折后也選擇了離開,但子君的離開卻是對困苦生活的失望,對自己通過抗爭獲得的自由愛情的失望,也是對于人生這段刻苦銘心旅程的失望。面對同居中的挫折,她碎心了,不再有愛,她放棄了愛情,放棄了人生,最終也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面對愛情中的挫折,子君是脆弱的,她選擇了放棄,沒有和涓生一起面對,共度難關,她的愛情難免悲劇。而簡·愛卻是堅強的,她沒有喪失自我,選擇了執著追求,即使最后羅切斯特的眼睛受傷,一無所有,也沒有因此拋棄他,反而認為兩人終于能在一起了,她以她的堅強抓住幸福的每個機遇。
三、經濟上的獨立與依賴
獨立性是魯迅先生所特意批判的,魯迅先生認為中國女性在當時雖然懂得了自由愛情的理念,但是并不明白什么是獨立女性,什么是女性權利,她們還無法沖破中國傳統女性觀念的束縛,在魯迅筆下的子君,完整的表述了這一思想。同居后的子君,完全喪失了自我,開始同中國傳統婦女一樣,糾結于家庭瑣事,完全成為男性的附庸,在經濟上完全依靠涓生。面對生活的壓力,她開始“有怨色”,而不是尋找謀生的出路,涓生丟了工作后,她對涓生失去工作的困窘生活失去了耐心,物質生活的困窘夾雜對于愛情的懷疑,成為她離開的最后一根稻草,子君從心底把涓生當做依賴,尤其是同居后在物質上,從而失去了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氣。
簡·愛的獨立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經濟上的。一開始她就通過廣告獲得了一份家庭教師的工作,自力更生。她從不認為自己是男性的附庸,即便是與羅切斯特相愛,她也認為彼此之間應該平等地對話,平等地戀愛。而發現羅切斯特有妻子時,簡·愛離開莊園后依舊能夠獨立生活、自食其力。顯然,簡·愛的獨立既是精神上的,同時也是經濟上的,這成為她幸福結局的又一原因。
簡·愛和子君都是所處社會歷史背景下女性主義覺醒的典型代表。簡·愛和子君最終命運的不同走向,從本質上反映了她們處在女性意識覺醒的不同階段:簡·愛對男權社會的認識更加清楚,對女性愛情和自由的追求更加強烈和徹底;而子君身上只是剛冒出了女性覺醒意識的幼芽,沒有從根本上擺脫男權社會對她精神的禁錮。以這兩個著名的女性人物為鏡,映射的是她們身處時代的暗涌和慣性,而她們的命運也啟示著當下的女性追求自由和解放是一個修遠而漫長的路程,需要付出更多的智慧、勇氣與耐心。
參考文獻:
[1]夏洛蒂·勃朗特.《簡·愛》[M].黃源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2]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瑪格麗特·奧方利特:《現代大大小小的小說家》[A].勃朗特姐妹研究[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作者簡介:鄭春玉,文學碩士,武警警官學院人文社科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