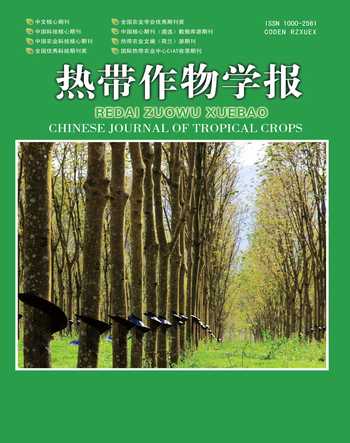云南地區烘焙咖啡豆的風味指紋圖譜研究
董文江 張豐 趙建平 谷風林 陸敏泉



摘 ?要 ?為研究云南4個地區(普洱、保山、臨滄、德宏)的烘焙咖啡豆(淺度、中度、深度烘焙)的揮發性物質種類及成分、滋味化合物的差異,采用頂空固相微萃取-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HS-SPME-GC/MS)和電子舌技術聯合使用檢測不同地區咖啡中氣味和滋味化合物。HS-SPME-GC/MS的檢測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地區烘焙豆的淺度、中度和深度樣品分別鑒定出60、65和67種揮發性成分,隨著烘焙度的增加,呋喃類、吡啶類和硫化物逐漸增加,酸類和呋喃酮物質逐漸減少,主成分分析(PCA)對不同烘焙度樣品鑒別能力較好,而不同地區的同一烘焙度樣品聚集較為緊密。電子舌檢測結果顯示,不同地區樣品中滋味化合物差異明顯,在PCA的二維投影圖上能夠按各自特性聚為一類,與HS-SPME-GC/MS檢測數據的分析結果相一致。
關鍵詞 ?烘焙咖啡豆;電子舌技術;頂空固相微萃取-氣相色譜-質譜聯用;風味指紋圖譜
中圖分類號 ?S571.2 ? ? ? ? ?文獻標識碼 ?A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Nose System Coupled with HS-SPME-GC/MS for Characterization of Aroma Fingerprint of Roasted Coffee Beans from Different Cultivation Regions in Yunnan Province
DONG Wenjiang1,3,4, ZHANG Feng1,2, ZHAO Jianping1,3,4*,
GU Fenglin1,3,4, LU Minquan1,3,4
1 ?Spice and Beverage Research Institute, CATAS, Wanning, Hainan 571533, China
2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Wubei ?430070,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Genetic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Spice and Beverage Crop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anning, Hainan 571533, China
4 ?National Center of Important Tropical Crop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Wanning, Hainan 571533, China
Abstract ?The volatile flavor components of roasted ground coffee with different roasting degree from different cultivation regions (Puer, Baoshan, Lincang, Dehong) of Yunnan were evaluated to identify the flavor difference. Headspac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gas 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 (HS-SPME-GC/MS) and electronic tongue technology were utiliz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HS-SPME-GC/MS performance indicated that the number of volatile compounds identified were 60, 65 and 67 for light, medium and dark roasted coffee sampl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oasting degree, the content of furans, pyridines and sulfides increased gradually, acids and furanones decreased accordingl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could effectively discriminate coffee samples of different roasting degree, while the samples with the roasting degree from different origins clustered closely. The performance of electronic tongue showed that the taste components were different obviously, and the samples could b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in the PCA score plot, which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 of HS-SPME-GC/MS.
Key ?words ?Roasted coffee beans;Electronic tongue;HS-SPME-GC/MS;Flavor fingerprint
doi ?10.3969/j.issn.1000-2561.2015.10.028
咖啡是世界貿易中最重要的農產品之一,除具有提神效果外,咖啡的香氣使其成為較受歡迎的飲料[1-2]。生咖啡豆是沒有香味的,其化學組分經過烘焙發生一系列反應如美拉德和焦糖化反應等才能形成咖啡特有的風味[3]。咖啡中包含超過800多種不同的揮發性成分,即使每一成分的含量是微量的,也能對咖啡的風味發揮作用[4]。因此,咖啡風味研究和質量控制可利用快速、高效、靈敏的現代儀器分析檢測技術。
國云南省的德宏、保山、臨滄、普洱為國內小粒種咖啡的主要種植區,種植面積達10萬hm2以上,總產量達12萬t,種植面積和產量占全國的98%以上[5]。國外對咖啡中的揮發性物質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Lee等[6]采用多固相-單點-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技術檢測商業咖啡中的香氣成分輪廓,總峰面積強度的增加與SPME纖維數量的增加呈現良好的線性關系(R2=0.999 2),四重SPME纖維提取的精密度為RSD值=9.9%;Petisca等[7]利用HS-SPME-GC/MS技術研究不同的烘焙速度對意式咖啡中呋喃類和其它揮發性化合物的影響結果表明:高烘焙速度有利于2-呋喃和5-甲基-呋喃的形成;Pissinatti等[8]采用同位素稀釋-氣相色譜質譜技術同時檢測烘焙咖啡的10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在最優的分析條件下,重現性范圍為3.3%~24%,精密度范圍為3.3%~33%。國內對咖啡風味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遺傳育種、豐產栽培、病蟲害防控等方面[9-11],張豐等[12]采用HS-SPME-GC/MS對云南3個地區(普洱、保山、臨滄)的中度烘焙豆進行檢測結果表明,呋喃類物質含量最高,且不同地區樣品能夠進行區分。
咖啡已成為云南地區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產業之一,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熱帶飲料作物,前期工作已對3個地區的中度烘焙豆進行分析,不同烘焙度的咖啡樣品其揮發性成分組成是不同的,導致其風味不同。本研究采用HS-SPME-GC/MS結合電子舌技術對云南咖啡的揮發性成分和滋味化合物進行分析,明確不同地區咖啡樣品的風味特點,以期為我國云南咖啡加工產業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1.1.1 ?材料與試劑 ? 阿拉比卡生咖啡豆,品種為卡蒂姆7963(水分含量為11%~12%左右):德宏地區(簡稱:DH,德宏熱帶農業科學研究所),保山地區(簡稱:BS,保山佐園咖啡莊園基地),普洱地區(簡稱:PE,普洱曼老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臨滄地區(簡稱:LC,臨滄凌豐咖啡產業有限公司鎮康分公司);C7-C30正構烷烴(純度為99.5%,美國Sigma公司);實驗用水全部為超純水,其它檢測試劑均為分析純。
1.1.2 ?儀器與設備 ? AL204型電子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儀器有限公司;Master-s-plus UVF型全自動超純水系統,上海和泰儀器有限公司;Agilent 7890A-5975C型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美國安捷倫公司;Alpha M.O.S電子舌分析系統,Alpha M.O.S電子鼻分析系統,法國Alpha M.O.S公司;SPME手動進樣器,75 μm CAR/PDMS固相微萃取頭,美國Supelco公司;MB45型快速水分測定儀,瑞士奧豪斯儀器有限公司;Xrite-SP62型色差分析儀,美國Xrite測色公司;PRE 1 Z型咖啡豆烘焙機,德國probat儀器公司;VTA 6S3型咖啡粉碎機,德國MAHLKONING儀器公司。
1.2 ?方法
1.2.1 ?烘焙豆的制備 ? 準確稱量100.00 g生咖啡豆于滾筒式咖啡烘焙機中,初始入鍋溫度為150 ℃,保持恒定火力為6.5,分別烘焙8、12、15 min得到淺度、中度、深度烘焙豆,快速冷卻至室溫。粉碎,過40目篩,色差儀測定色度值L分別為46.00、42.00、38.00。將烘焙咖啡豆置-40 ℃冰箱中保存,備用。
1.2.2 ?頂空固相微萃取法 ? 萃取頭老化:在初次使用萃取頭時,必須進行老化。將75 μm CAR/PDMS萃取頭插入氣相色譜儀中在300 ℃老化1 h。
準確稱取1.0 g咖啡樣品,加入15 mL螺口樣品瓶中,加蓋擰緊,置60 ℃集成式水浴恒溫磁力攪拌器中,平衡時間為20 min,將已活化好的SPME萃取頭插入樣品瓶,推下纖維頭,頂空吸附30 min后,插入氣相色譜進樣口解吸3 min。
1.2.3 ?氣相色譜-質譜分析 ? 色譜條件:分析柱使用Agilent公司的DB-Wax石英毛細管柱(30 m× ? 0.25 mm×0.25 ?m),進樣口溫度為250 ℃,不分流進樣,載氣為氦氣,流量為1.0 mL/min;程序升溫條件:起始溫度為40 ℃,保持2 min,以1.5 ℃ /min的速率升溫至130 ℃,然后再以4 ℃/min的速率升溫至200 ℃,保持5 min。
質譜條件:電離方式為電子轟擊(EI)源,離子源溫度為230 ℃,四級桿溫度為150 ℃,電子能量為70 eV;質量掃描范圍:35~350 amu。
保留指數的確定:將正構烷烴標準品(C7-C30)混合物在上述GC-MS條件下進行測定,得到各正構烷烴(C7-C30)的保留時間,用于下一步樣品中揮發性成分保留指數的計算。
化合物定性和定量:經過計算機檢索,與NIST Library和Wiley Library進行匹配,計算各揮發性化合物的保留指數,并與相關文獻報道對比,確定最后的定性結果;化合物的相對含量以各揮發性成分的峰面積占總峰面積和的百分比表示。
1.2.4 ?咖啡提取液的制備 ? 準確稱量8.25 g咖啡樣品加入250 mL圓底燒瓶中,置于恒溫加熱磁力攪拌器上,精密移取150 mL溫度為95 ℃的去離子水,加入圓底燒瓶中,在沸騰狀態下持續加熱5 min并攪拌,以充分浸提咖啡中的有效成分,晾至室溫、過濾;精密移取80 mL濾液至電子舌反應燒杯中,備用。
1.2.5 ?電子舌分析 ? 電子舌系統用于采集滋味指紋圖譜數據,儀器包括7個化學傳感器(ZZ、JE、BB、CA、GA、HA、JB),因ZZ傳感器響應值偏高,可能已損壞,因此采用除ZZ外的剩余6個傳感器用于實驗。精確移取80 mL咖啡液于反應杯中,數據采集時間為120 s,樣品間去離子水清洗時間為10 s。每個樣品平行測定5次,結果以平均值(x)±標準偏差(s)形式表示。
1.3 ?數據分析與處理
所有的數據分析均在軟件MATLAB R2010a平臺上運行。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地區烘焙咖啡豆揮發性成分組成分析
以臨滄地區樣品為例,不同烘焙度樣品的GC-MS總離子流色譜見圖1,藍色、綠色和紅色分別代表淺度、中度、深度烘焙樣品,在色譜峰數量和強度上存在差異。對云南4個地區(普洱、保山、臨滄、德宏)不同烘焙度咖啡的GC/MS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看出,4個地區同一烘焙度下咖啡中的揮發性物質在種類和數量上相差不大,淺度、中度和深度烘焙樣品中鑒定出的揮發性物質總數分別為60種、65種和67種(表1)。
咖啡樣品中每類物質的含量以各自峰面積之和占總峰面積的百分比表示,對咖啡中揮發性物質進行歸類分析發現,在淺度烘焙中,糠醛是普洱、臨滄、德宏樣品中含量最高的揮發性物質,分別為(17.39±0.35)%、 (14.93±0.13)%、(12.30±0.22)%,而保山咖啡中含量最高的是甲基吡嗪,為(10.75± 0.16)%; 在中度烘焙樣品中, 糠醇在保山、 臨滄和德宏中含量最高,分別為(13.54±0.42)%、 (12.28±0.25)%和(11.89±0.10)%, 而在普洱中度咖啡中5-甲基呋喃醛含量最高, 為(14.01±0.28)%; 在普洱深度烘焙咖啡中最高含量的揮發性物質是糠醇,為(15.22±0.96)%,而保山、臨滄、德宏深度烘焙咖啡中含量最高的揮發性物質是吡啶,分別為(20.28±0.46)%、 (17.85±0.20)%、 (19.26±0.40)%。說明咖啡中揮發性物質隨烘焙度增加變化較大,如普洱樣品中吡啶類物質含量從0.53%(淺度)增加至16.34%(深度);而呋喃類從43.28%(淺度)減少至33.25%(深度)。
由表1可以看出,深度烘焙咖啡中呋喃類物質數量比淺度烘焙樣品多,與中度烘焙樣品相當,如普洱咖啡中的糠醛含量由(10.44±0.08)%(中度)減少至(3.53±0.10)%(深度), 5-甲基糠醛含量由(14.01±0.28)%(中度)減少至(2.77±0.06)%(深度)。
由表1可以看出,隨著烘焙度增加,吡嗪類物質在數量和種類上變化不大,如圖2所示,隨著烘焙度的增加,吡嗪類物質的含量減少,尤其是保山和德宏咖啡由淺度烘焙到中度烘焙時變化明顯,這主要是由于這2個地區淺度咖啡中的甲基-吡嗪、2,5-二甲基吡嗪和2,6-二甲基吡嗪的含量比普洱和臨滄咖啡高。
由表1可以看出,吡啶類物質隨烘焙度增加其數量增加,而吡咯類物質基本沒有變化;在化合物含量上,4個地區咖啡中吡啶類化合物均隨烘焙度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吡啶的增加最為明顯,如普洱樣品含量從(0.53±0.05)%(淺度烘焙)增加到(13.69±1.22)%(深度烘焙);如圖2中所示,4個地區咖啡中的吡咯類化合物含量相當,且隨烘焙度增加其變化不大。
由表1可以看出,4個地區咖啡中的醛類和酮類在種類上變化不大,在同一烘焙度條件下,酮類物質含量基本相當,并且隨著烘焙度的增加,含量在逐漸減少;而醛類物質隨烘焙度的增加其含量并沒減少,在深度烘焙樣品中反而最大,主要是由于4-甲基苯甲醛在深度烘焙咖啡中的含量較高。
如圖2所示,4個地區的深度烘焙咖啡中酚類物質含量明顯增加,相比于淺度和中度咖啡,酚類物質對深度烘焙咖啡的香氣影響較大。除德宏地區咖啡外,其它地區咖啡均隨烘焙度的增加,酸類物質含量減少。
從GC-MS結果來看,并沒有檢測出2-糠基硫醇,而且4個地區硫化物的含量相差不大。
2.2 ?不同地區烘焙咖啡豆各類揮發性物質組成的主成分分析
4個地區不同烘焙度咖啡中的各類揮發性成分主成分分析見圖3。由圖3可知,前2個主成分(PC)的方差貢獻率為95.9%,基本包含了揮發性物質的主要信息,其中PC1和PC2的貢獻率分別為65.0%和30.9%。在PC1方向上除4個地區深度烘焙咖啡得分為正,其余均為負,PC1方向上投影深度烘焙(圓形)和中度烘焙(方形)、淺度烘焙(三角形)分界明顯,而中度烘焙樣品和淺度烘焙樣品有部分重疊;在PC2方向上,4個地區的淺度烘焙咖啡區分明顯,深度烘焙中普洱同另外3個地區區分明顯,而4個地區中度烘焙區分不明顯。
2.3 ?不同地區咖啡中特征香氣物質的主成分分析
國外對咖啡中關鍵香氣物質進行了較多的研究,根據GC-MS檢測到的揮發性物質選擇其中的21種作為判斷指標。
為了更進一步明晰香氣物質對不同地區烘焙咖啡的影響,以表2中的21香氣成分進行主成分分析,從圖4可知,前2個PC的方差貢獻率為86.90%,其中PC1為74.80%,PC2為12.10%。在PC1方向上,4個地區不同烘焙度咖啡得分均為正,其中深度烘焙和淺度、中度分界明顯,而中度和淺度有部分重疊;在PC2方向上,除淺度烘焙咖啡得分為負,其余均為正,3種不同烘焙度咖啡區分明顯,尤其是深度烘焙和淺度、中度咖啡。說明4個地區同一烘焙度咖啡基本能保持較好的相關性,而不同烘焙度咖啡區分程度較為明顯,較深度烘焙咖啡而言,淺度烘焙咖啡和中度烘焙咖啡相關性較好,此結果與圖3結果一致。
2.4 ?電子舌分析
電子舌的6個傳感器(JE、BB、CA、GA、HA和JB)的特征響應值對比見圖5。由圖5可知,所有咖啡樣品的傳感器CA響應值最大,對于3種烘焙度咖啡,順序均為:德宏>臨滄>保山>普洱,同一地區的3種烘焙度咖啡的CA傳感器響應值差異不大;響應值處于中間水平的傳感器為:HA、JE、JB,其中HA響應值最大,對于淺度和中度烘焙咖啡響應值JB>JE,而深度烘焙咖啡JE>JB。3種烘焙度咖啡中,普洱咖啡的HA響應值較小,臨滄咖啡響應值最大;JE傳感器,3種烘焙度咖啡的響應值依然是普洱咖啡最小,而且普洱中度咖啡的響應值要小于淺度烘焙咖啡,JB傳感器對于4個地區3種烘焙度咖啡的響應值差異較小;傳感器BB和GA響應值最小,對于GA傳感器,3種烘焙咖啡的響應值差異較小,而BB傳感器變化較大,淺度和中度烘焙咖啡響應值較大的為普洱咖啡,深度烘焙為德宏咖啡。
咖啡樣品的電子舌指紋數據的主成分分析投影見圖6。由圖6可知,PC1和PC2的總方差貢獻率為98.99%,其中PC1占96.82%,PC2占2.17%,總和大于85%表明前2個PC能夠解釋數據集的總方差。由圖6-A可看出,在PC1方向上,普洱、保山以及臨滄淺度樣品得分全部為負,而德宏和臨滄中度和深度咖啡得分為正;PC2方向上,4個地區同一烘焙度樣品相互重疊;在PC1-PC2二維投影上,4個地區咖啡基本能夠區分開,尤其是普洱咖啡和德宏咖啡,而保山咖啡和臨滄咖啡相距較近。4個地區深度烘焙咖啡均和淺度、中度咖啡區分明顯,而淺度和中度咖啡相距較近,其中德宏淺度和中度咖啡相距最近,保山淺度、中度樣品和臨滄淺度、中度樣品基本處于原點附近,區分度不大。由圖6-B可看出,在PC1負方向上與載荷BB和JB相關,正方向上與剩余4個傳感器相關;在PC2負方向上與JB和CA傳感器相關,正方向上剩余4個傳感器相關,傳感器BB、GA、JE和HA均與4個地區深度烘焙咖啡相關性較好,尤其是JE傳感器與德宏、臨滄深度咖啡相關性較大,而JB傳感器與普洱和保山淺度咖啡相關性較好。通過電子舌系統結合PCA分析,可從定性角度對不同地區烘焙咖啡豆進行區分。
3 ?討論與結論
咖啡的特征香氣是由不同種類、濃度的揮發性物質決定,對阿拉比卡烘焙咖啡的香氣起主要貢獻的化合物為極性物質[13]。隨著烘焙度的增加,咖啡中的化學組分由于烘焙發生一系列反應如美拉德和焦糖化反應等[3],導致咖啡中揮發性物質在種類和含量上發生變化。
呋喃類化合物是咖啡揮發性物質中含量相對較高的一類物質,主要表現為燒焦味和焦糖化味[14],其產生主要是由于糖類和氨基酸在高溫下發生反應[15],由于生咖啡豆中含有較高的糖類和氨基酸,所以產生的呋喃類物質含量較高。本研究結果發現,深度烘焙咖啡中呋喃類物質數量比淺度烘焙樣品多,與中度烘焙樣品相當,與Shibamoto等[16]報道一致,咖啡中糠醛含量隨烘焙度的增加而降低,可能是由于發生了分解反應或聚合反應[17-18]。
吡嗪類作為烘焙咖啡中第二大類的揮發性物質,主要表現為燒烤味和泥土味[19]。本研究結果發現,隨著烘焙度增加,吡嗪類物質在數量和種類上變化不大。吡啶類和吡咯類化合物主要表現為煙熏味和燒焦味,但是由于這些化合物閾值較高,因而其對咖啡的香氣貢獻較小[20]。本研究結果發現,4個地區咖啡中吡啶類化合物均隨烘焙度的增加而增加,與Shibamoto等[16]報道一致。醛類和酮類化合物通常在中度烘焙時具有較高的含量,而在深度烘焙由于發生降解反應含量會出現略微減少[21],其中醛類和2,3-戊二酮是貢獻咖啡奶油風味的關鍵香氣物質。本研究結果發現,4個地區咖啡中的醛類和酮類在種類上變化不大。
酚類作為咖啡中一類揮發性物質,主要是由于奎尼酸部分基團降解形成的[19]。本研究結果發現,4個地區的深度烘焙咖啡中酚類物質含量明顯增加,主要是由于愈創木酚、苯酚和4-乙基-2-甲氧基苯酚含量增幅較大,其中愈創木酚和4-乙基-2-甲氧基苯酚對香氣貢獻較大,尤其是愈創木酚被視為咖啡中的一種關鍵香氣物質[22]。羧酸類物質如乙酸、丙酸和3-甲基丁酸主要影響咖啡的酸味[19],本研究發現,酸類物質對淺度烘焙樣品影響較大。
含硫揮發物作為咖啡中一種重要的香氣物質主要影響咖啡的烘焙味[23],由于這類化合物具有較低的閃點和易氧化等特性,所以通常以微量形式存在于咖啡中(不足總揮發性物質的0.01%),但是在新鮮烘焙咖啡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3],其中,2-糠基硫醇由于其較低的閾值,為0.05 ppb(空氣),因而對咖啡香氣貢獻較大。4個地區硫化物的含量相差不大,未檢測出2-糠基硫醇。呋喃酮類也對咖啡香氣貢獻較大,而2,5-二甲基-4-羥基-3(2H)-呋喃酮是最為常見的關鍵香氣化合物[24]。
依據載荷圖可尋找對4個地區不同烘焙度咖啡香氣貢獻較大的各類揮發性物質,吡嗪類可以作為區分保山淺度和德宏淺度的判斷指標,酸類和呋喃酮類和臨滄淺度咖啡相關性較高,可以作為其判斷指標,而普洱淺度烘焙咖啡和酮類以及呋喃類相關性較高;4個地區中度烘焙咖啡基本保持一致,其相關性揮發性物質為呋喃類;深度烘焙咖啡中,保山、臨滄、德宏相接近,其相關性較高的揮發性物質主要是酚類、吡啶類以及硫化物,而同普洱深度烘焙咖啡相關性較高的揮發性物質是吡咯類,上述幾類揮發性物質基本上可作為區分不同地區、不同烘焙度咖啡豆的鑒別依據。
目前,咖啡中被檢測出的揮發性成分已超過800種,然而揮發性只是一種物質對咖啡香氣有貢獻最基本的要求[25],并不是所有的揮發性成分都是香氣物質,作為咖啡中的香氣物質必須在空氣中超過一定濃度,同時與鼻腔內的受體發生反應才能被感受到,如具有青草燒焦味的高含量甲基吡嗪由于具有較高的閾值,因此其對咖啡整體香氣貢獻相當有限[26]。另外,糠醇以及吡啶等高百分比的揮發性物質也檢測出其對咖啡的香氣有較小的影響,而一些百分含量較低的揮發性物質如4-乙基-甲氧基酚和2,5-二甲基-4-羥基-3(2H)呋喃酮卻對咖啡的香氣有較大的影響[27]。本研究根據GC-MS檢測到的揮發性物質選擇其中的21種作為判斷指標。通過對歸類揮發性物質進行PCA分析發現,揮發性物質可以作為區分4個地區不同烘焙咖啡的判斷指標,吡嗪類同保山和德宏淺度樣品相關性較好,酸類、呋喃酮類和臨滄淺度樣品相關性較高,而普洱淺度樣品與酮類以及呋喃類相關性較高;4個地區中度烘焙咖啡基本保持一致,同呋喃類相關性較好;保山、臨滄、德宏深度咖啡較接近,相關性較高的主要是酚類、吡啶類以及硫化物,普洱深度咖啡相關性較高的是吡咯類。而對主要香氣物質的PCA分析結果與以上結果存在差異,主要是由于咖啡特征香氣的產生是由少數致香物質導致的,并且隨著烘焙度的增加,4個地區同一烘焙度咖啡的香氣差異也在增加。
電子舌是模仿人體味覺機理的一種現代分析儀器,由味覺傳感器陣列獲取待測樣品液的信息,通過多元數據分析方法對傳感器輸出信號進行處理,實現對樣品的分析。電子舌并不能從微觀上對樣品的微觀組分進行分析,而是反映了樣品的整體風味特征,具有客觀、快速、準確、重復性好等優點[28],通過電子舌實驗,能夠進一步明晰4個地區烘焙咖啡間的差異。根據電子舌實驗的PCA結果可以看出,4個地區的烘焙咖啡區分度較好,尤其是普洱和德宏咖啡區分度明顯,而保山和臨滄咖啡相距較近;對于同一烘焙度咖啡而言,4個地區深度咖啡均與淺度和中度咖啡區分明顯,而中度和淺度相距較近,其中德宏淺度和中度咖啡差異最小,而保山淺度、中度咖啡和臨滄淺度、中度咖啡差異也較小。
參考文獻
[1] Illy A, Viani R. Espresso Coffee: The Science of Quality[M]. 2nd ed dLondon: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2005.
[2] Thomas C, Jana H. Volatile compounds in food authenticity and traceability testing[M]//Jelen H. Food Flavor Florida:CRC Press, 2011: 355-412.
[3] Vignoli J A, Viegas M C, Bassoli D G, et al. Roasting process affects differently the bioactive compounds and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Arabica and Robusta coffee[J]. Food Res. Int., 2014, 61: 279-285.
[4] Belitz H D, Grosch W, Schieberle P. Food chemistry[M]. Berlin: Springer, 2004: 939-969.
[5] 祝運海. 云南普洱咖啡產業發展綜述[J]. 飲料工藝, 2012, 15: 3-7.
[6] Lee C, Lee Y, Lee J G, et al. Development of a simultaneous multipl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single shot-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to aroma profile analysis of commercial coffee[J]. J Chromatogr, A, 2013, 1 295: 24-41.
[7] Petisca C, Perez-Palacios T, Farah A, et al. Furans and other volatile compounds in ground roasted and espresso coffee using headspac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Effect of roasting speed[J]. Food Bioprod Process., 2013, 91: 233-241.
[8] Pissinatti R, Nunes C M, de Souza A G, et al. 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10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roasted coffee by isotope dilution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Optimization, in-house method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an exploratory study[J]. Food Control, 2015, 51: 140-148.
[9] 何紅艷, 文志華, 李國鵬. 咖啡采后處理及初加工技術[J]. 廣東農業科學, 2008, 12: 119-120.
[10] 李國鵬, 何紅艷, 羅心平,等. 咖啡應用特性及營養診斷研究進展[J]. 中國農學通報, 2009, 25: 248-250.
[11]黃家雄,李貴平. 咖啡遺傳育種研究進展[J]. 西南農業學報,2008, 21: 1 178-1 181.
[12] 張 ?豐, 董文江, 王凱麗,等. 云南不同地區烘焙咖啡豆揮發性成分的HS-SPME/GC-MS分析[J]. 食品工業科技, 2015(11):273-280.
[13] Moon J W, Shibamoto T. Role of roasting conditions in the profile of volatile flavor chemicals formed from coffee beans[J]. J Agric Food Chem, 2009, 57: 5 823-5 831.
[14] Lopez-Galilea I, Fournier N, Cid C, et al. Changes in headspace volatile concentrations of coffee brews caused by the roasting process and the brewing procedure[J]. J Agric Food Chem, 2006, 54: 8 560-8 566.
[15] Akihiko N, Eun-Ho K, Kazuki S, et al. Formation of furfural derivatives in amino-carbonyl reaction[J]. Biosci Biotech Bioch, 1993, 57: 1 757-1 759.
[16] Shibamoto T, Harada K, Mihara S, et al. Application of HPLC for evaluation of coffee flavor quality[M]//The Quality of Food and Beverag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312-334.
[17] Silwar R, Lullmann C. Investigation of aroma formation in Robusta coffee during roasting[J]. Cafe Cacao The, 1993, 37:145-152.
[18] Zilbergleit M A, Glushko T V. Polymerization products of furfural and hydroxymethylfurfural in acetic acid[J]. Koksnes Kimija, 1991, 1: 66-68.
[19] Buffo R A, Cardelli-Freire C. Coffee flavour: an overview[J]. Flavour Frag J, 2004, 19: 99-104.
[20] Rocha S, Maeztu L, Barros A, et al. Screening and distinction of coffee brews based on headspace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gas chromatography/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J]. J Sci Food Agr., 2003, 84: 43-51.
[21] Schenker S, Heinemann C, Huber M, et al. Impact of roasting condi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aroma compounds in coffee beans[J]. J Food Sci, 2002, 67: 60-66.
[22] Sanz C, Czerny M, Cid C, et al. Comparison of potent odorants in a filtered coffee brew and in an instant coffee beverage by aroma extract dilution analysis(AEDA)[J]. Eur Food Res Technol, 2002, 214: 299-302.
[23] Cannon R J, Trinnaman L, Grainger B, et al. The key odorants of coffee from vari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s. Flavors in noncarbonated beverages[M].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0, 1 036: 77-90.
[24] Blank I, Sen A, Grosch W. Potent odorants of the roasted powder and brew of Arabica coffee[J]. Zeischrift fur Lebensmittel-Untersuchung und-Forschung, 1992, 195: 239-245.
[25] Schieberle P. New developments in methods for analysis of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and their precursors. In Characterization of Food-Emerging Methods[M]. Elsevi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1995: 403-431.
[26] Ewa N, Grazyna B, Teresa M, et al. The effect of roasting method on headspace composition of robusta coffee bean aroma[J]. Eur Food Res Technol, 2007, 225: 9-19.
[27] Akiyama M, Murakami K, Ikida M,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flavor compounds released during grinding of roasted Robusta coffee beans[J]. Food Sci Technol Res, 2005, 11: 298-307.
[28] Haddi Z, Mabrouk S, Bougrini M, et al. E-Nose and e-Tongue combination for improved recognition of fruit juice samples[J]. Food Chem, 2014, 150: 246-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