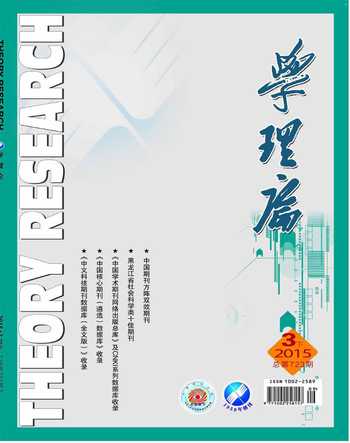西方“社會”觀念概要追溯
王金朋
摘 要:西方傳統社會思想認為,“社會”一詞的使用常是概括性、含蓄的;那么,在西方歷史中“社會”的觀念意味著如何理解歷史中“社會”概念及其繼承。在西方社會思想史的基礎上對西方“社會”的概念和使用做出回溯性觀察,通過對核心哲學思想家的論述從中分析“社會”觀念變化的脈絡。
關鍵詞:社會;社會觀;理性
中圖分類號:G91-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58-02
一、古希臘以來的社會觀
古希臘的社會是從傳統沿襲而來,當智者學派面臨“異鄉人”而對是否存在普遍規范和原則陷入懷疑,蘇格拉底無比堅定選擇相信善和美德是人類天性時,從此西方社會思想史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內在地具有了對善和美德追求的任務。除了“認識你自己”之外,古希臘的民主制社會并不能給我們更多啟發,在沒有確定知識的年代他們所做出的決斷并不意味著他們篤信,而只是依照傳統或某些神的指示罷了。
這種局面下,社會是什么并不是他們的關注重點。就像智者派許多人宣稱正當和正義只是一種獨斷傳統的表達或被強迫接受一樣,他們更關注的是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怎樣做最有意義。按照古希臘和諧精神的內涵,我們可以稱社會對于他們所具有的意義是“社會”是人類實現自己的工具。
雖然柏拉圖的設計比較理想化,對理念追求的目的也并不一定是去城邦中生活,但柏拉圖確實把“善的生活”當成其社會建制的目標,社會也就意味著一個體系化的設計,人人從屬于按其能力安排的職業,每個人與同伴穩定和諧地相處,目的是過“善的生活”。也許新柏拉圖主義對其繼承更多集中在對“太一”的追求,人的目的是去尋求靈魂的神秘合一,以至于“善”作為一種社會價值的意義被削弱。但柏的這種體系化的設計卻一直延續著,我們甚至可以有理由被認為按照理性化設計的官僚制體系就是在延續著這樣一個古老的傳統:按能力獲得職位,追求某種社會目標。
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共同體、社會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能去實現他們最好能力的必要條件。他似乎依然理所當然地把共同體或社會當成自然而然的東西,而并未對它們應該是怎樣的做更多分析。更何況,當柏拉圖的追求是某種理念時,亞里士多德的“實在”也只是一個過程,社會似乎并不具有特殊的力量。
總的來說,柏拉圖所主張的社會價值實質是他認定的人類價值的模仿,并且我們也可以稱這種價值式的社會觀也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現代社會,比如對正義、平等的追求。但社會仍然不是被分析的主體,“社會”可以是很多意義,但沒有一種是它的本意,它的存在在于它是工具而已。
二、中世紀的社會觀
如果蘇格拉底的“美德即幸福”的擴展義是幸福是人類的終極追求,而美德則是人類追求的目標。那么我們可以擴展的認為柏拉圖和斯多亞主義一樣宣揚一種普遍性、規范性的人類價值,不同于柏拉圖的是,斯多亞主義追求的現實意義在于人類開始創造一個基于自然原則但屬于自己現實生活的社會,此時社會從一個工具具有了生活的意義。
如此,社會不再是為實現某種價值或目的的工具物,而是實實在在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們享受某種意義的生活本身,就像希臘化時期斯多亞主義倡導的責任和以堅強、負責的品格培育為基礎的國家道德一樣,社會實質的具有了維護人類生活幸福、培育生活理念的任務。這種對“集體責任”的強調使得社會作為一個理想成為一個信仰。
如果說因為柏拉圖的無限追求使得人本身成為精神的工具,那么斯多亞主義的有限追求使得人本身成為目的。相應地,其結果也是社會是追求、實現善的工具和社會是維護和培育善的目的。當社會是善的目的本身時,如果按照嚴格意義上的羅馬法建立起來的社會未嘗不應稱作具有現代特征的民主社會:平等、理性、民主。
但是同樣值得思考的是“無限”帶來的是永恒追求,帶來的是向往一個終極目標的確定性,在有限意義上的追求,則往往意味著不確定性,這似乎是一個危機:對社會的信仰并不能提供給我們以未來。我們越相信確定性的現實,我們就越不確定未來。按照皮浪的話:我們從根本上就“無法知道任何東西”,以至于社會充其量只是一個“滿載貨物的手推車”,即使能夠使用一部分貨物,但我們仍然不是這個手推車的主人。
只是當阿奎那將社會“自然存在”的與教會平等起來時,社會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雖然他和亞里士多德一樣認為人是社會性的造物,生活在社會中是他們有能力實現自身的一個條件,而且他承認“人類可以在沒有啟示情況下過一種有德性的幸福生活”,他們之間的差別只是斯多亞主義意義上的差別,社會在阿處自然的具有了善和理性等特征。不過在此提及阿的特殊之處在于,阿奎那認為“天上之城”并不是人類此世的僅有的追求,人類同樣可以造自己的“地上之城”,這樣“地上之城”也不再是奧古斯丁筆下必要的惡,而是借以實現人的德性的工具。這樣社會潛在的具有了一個重要的使命:對抗教會。
雖然我們可以無限的稱當人成為“上帝寵兒”、是“最高的造物”時人類從未如此的卑躬屈膝;但教會確實的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存在,為生活在中世紀的基督徒帶來心靈的慰藉和信念的鼓舞。對于教會作為一個社會組織結構和精神信仰存在時,教會不只是上帝遴選眾人的工具,它同樣現實的承擔著對人類的生活指導和精神照拂。那么教會在“社會”層面上具有什么意義?
如果我們拓寬視野看待這個主題,我們發現人類將是如此孤獨、危險和茫然,人類在其成長路上除了自己,無可依靠;除了自我拯救,想不出別的辦法活著;除了給自己想象以外,沒有第二個法子給自己意義。也就是說,我們還可以稱中世紀與其說是人類歷史上曾經“黑暗”的世紀,不如說中世紀是人類開始認清自己本質和處境的時代。而教會所帶來的社會啟示即是信仰是我們最后的依仗。
三、近代啟蒙運動時期社會觀
從以上帝為目標的社會觀念中走出,仍然回到某種原則式的自然觀念來似乎并不困難,雖然我們仍無法排除這種原則式的觀念可能是上帝的化身;而且思想家們也主張將信仰私人化,避免了宗教機構對社會生活的控制。我們似乎可以放心地使用某些原則作為我們的生活目標和社會標準,正式開始理性生活。
伴隨著馬基雅維利的君主理論改變這個想法的進程,馬基雅維利事實上否定了普遍標準的存在,或者說在他的學說中,存在的只有君主一個人的聲音,沒有普世價值、沒有道德標準。盡管馬基雅維利所處的意大利彼時四分五裂成彼此間一直沖突的諸多小國,為創立一個穩定國家而實行絕對君主制似乎無可厚非;但如果從思想史角度來看,我們發現馬基雅維利實質上掃除了過往的一切規范、傳統和約定,他在開啟的是一個完全由自由人創造的時代。沒有自然法則,也沒有教士上帝,有的只是基于現實的自私自利的人如何建立和維持秩序。這是一個確實的人屬社會。
這樣看來,似乎在馬基雅維利處,存在著的是為尋求自保的人類在混亂或有秩序的生活,社會所代表的就是一個能夠保障人們穩定生活的君主的設計方案。也許我們可以在此處總結道:人類正開始掙脫一切形式的“神話幻覺”,正在從現實的人出發一步步的構建著新社會。
如果說馬基雅維利的君主意志有可能因其專制和變化而不斷的帶來混亂的話,德國約翰·阿爾圖修斯以社會群體為基礎的“契約論”則為如何創造一個人屬社會奠定了理論基礎。人類自然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先天的不從屬于任何人或任何別的物,不用因任何物而向任何物屈服,他們擁有對他們自己絕對的控制權力,他們可以自行結約達成某些協議,他們是他們自己的主人。假如極端地說,自古希臘以來的社會都因被賦予各種不知名的意義而使人自身淪為因某種目的奔勞的工具的話,那么也許自此始,社會即為人類本身,而社會的意義也由人類的契約所確定。
人是自然人,但僅僅如此而已,人類并不因此而從屬于自然或自然規則,他只服從于他自己和他簽約的契約。所以格勞秀斯在討論一種適用于所有條件的法律時認定:上帝給了人類以伙伴相處的自然需要,如此而已;至于如果要實現在格勞秀斯認為根本性的和平相處的話,那么每個人必須遵守某些法律,也僅此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霍布斯實際在嘗試做的是在沒有上帝的日子里為人類找到社會生活的合理性理由,這樣我們又回到理性上來了,而社會也被看作一個“利己主義的人們之間的協議的表現”。
參考文獻:
[1]G·希爾貝克,N·伊耶.西方哲學史[M].童世駿,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11.
[2]保羅·埃爾默·摩爾.柏拉圖十講[M].蘇隆,譯.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3:8.
[3]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結構[M].李康,李猛,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