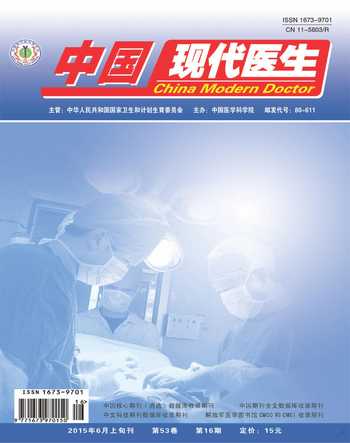家屬同步認知干預對宮頸癌患者心理、行為特征的影響
戴斌 陳文兵



[摘要] 目的 探討家屬同步認知干預對宮頸癌患者心理、行為特征的影響。 方法 選擇宮頸癌患者60例,隨機分為3組,每組20例。第1組給予常規護理,第2組對患者進行認知干預,第3組患者及家屬同時進行認知干預。干預前后采用焦慮自評量表、抑郁自評量表、行為量表對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以及行為特征進行調查分析。結果 干預后,第3組患者焦慮、抑郁評分顯著低于第2組,第2組顯著低于第1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干預后,第2組患者焦慮維度、抑郁維度得分顯著低于第1組,第3組顯著低于第2組(P<0.01);第2組樂觀維度、社會支持維度得分顯著高于第1組,第3組顯著高于第2組(P<0.01或P<0.05)。 結論 家屬同步認知干預能夠顯著改善宮頸癌手術治療患者焦慮、抑郁情緒,改善患者的行為特征。
[關鍵詞] 家屬;同步;認知干預;宮頸癌;心理;行為特征
[中圖分類號] R737.3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5)16-005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effect of synchronous families cognitive intervention on mental,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n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Selected 60 cases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hree groups, each of 20 cases. Group 1 was nursed by routine care, group 2 was nursed by cognitive intervention only for patients, and group 3 was nursed by cognitive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and familie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urveyed by SAS, SDS and C type behaviors scale.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SAS and SDS of group 3 were lower than group 2, and group 2 was lower than group 1,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or P<0.01). After intervention, anxiety dimensions, depression dimension of group 2 were lower than group 1, and group 3 were lower than group 2(P<0.01); optimism dimensions, social support dimensions of group 2 were higher than group 1, and group 3 were higher than group 2 (P<0.01 or P<0.05). Conclusion Synchronous families cognitive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can improv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behaviors.
[Key words] Families; Synchronous; Cognitive intervention; Cervical cancer; Mental;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宮頸癌發病率在女性惡性腫瘤中僅次于乳腺癌及直腸癌,居第三位。隨著篩查技術的發展,宮頸癌早期診斷率逐漸提高,也為臨床上的根治提供了可能。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患者的心理情緒影響其對治療的依從性及預后,而癌癥患者的心理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關注[1]。癌癥本身及其治療對患者來說均為負性生活事件,導致患者出現不良的心理應激,影響患者的預后。患者家屬在患者的治療、康復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作用,其本身也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心理應激問題,這也會進一步加重患者的負性情緒[2]。因此在對患者進行認知干預的同時也應注意對家屬的認知干預。本研究分別比較患者及家屬同步認知干預、僅對患者進行認識干預以及常規護理對宮頸癌圍手術期患者心理、行為特征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2年1月~2014年6月在我院手術治療的宮頸癌患者60例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臨床確診為宮頸癌Ⅰ期、Ⅱ期的患者;②無藥物依賴史及酒精依賴史;③小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理解能力正常;④意識清晰,能夠表達自己的意愿;⑤患者及家屬均知情同意并簽訂知情同意書;⑥納入的家屬干預對象年齡>18歲,小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理解能力正常,意識清晰,能夠表達自己意愿。排除標準:患者合并其他嚴重疾病,精神病史,嚴重認知障礙,視聽障礙;家屬有精神病史、認知障礙者。另外,排除在研究過程中因各種原因未能完成研究的患者及家屬。60例患者隨機分為3組各20例。第1組采用常規護理,第2組僅對患者進行認知干預,第3組同時對患者及家屬進行認知干預。三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1.2 干預方法
1.2.1 各組干預方法 第1組入院后至出院均僅給予宮頸癌手術的常規護理。第2組患者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發放《宮頸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冊》,給予認知干預。第3組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給患者發放《宮頸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冊》,同時給家屬發放《宮頸癌家屬健康教育手冊》,進行同步認知干預。宮頸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冊根據宮頸癌相關知識、高危因素、患者自我護理、自我心理調整、治療方法、預后等情況采用簡潔易懂的語言編寫。宮頸癌家屬健康教育手冊根據宮頸癌相關知識、治療方法、預后、如何護理患者、如何協助患者配合治療、如何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如何自我心理調整等采用簡潔易懂的語言進行編寫。
1.2.2 認知干預內容 認知干預模式主要是重建認知、應付心理、解決問題。重建認知的方法是通過識別、分析,從而改變患者的錯誤認知及信念,重建積極的認知模式。通常是先通過交流了解患者情況,然后評估、識別、檢驗患者存在的不良認知以及消極的思維和信念,幫助患者重建積極的認知,改變患者的情緒及行為。患者入院后,與患者進行面對面交流,了解患者的病情,評估患者存在的負性情緒和不良認知,檢驗患者的負性情緒以及不良認知,并幫助患者建立新的認知,樹立積極的心態。患者入院后每天采用一對一的方式,床邊交流。內容主要是了解患者和家屬出現的不良情緒問題,針對可能的原因給予相應的心理疏導和支持,幫助患者建立正確的認知。鼓勵患者傾訴內心的不安和痛苦,幫助患者尋找合適的宣泄途徑,并積極應對。鼓勵患者之間、患者與家屬之間進行交流,并為這些交流提供條件,進行團體干預。第2組和第3組每周組織患者學習《宮頸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冊》內容,第3組每周組織患者家屬學習《宮頸癌家屬健康教育手冊》。讓患者及家屬了解宮頸癌相關知識、手術基本情況、術后護理配合及出院后的指導等,幫助患者及家屬獲得正確的認知,指導患者及家屬積極應對負性情緒,培養患者及家屬樹立樂觀的心態。
1.3評價方法
患者入院時采用自制的一般資料問卷對患者的人口學資料進行調查,包括年齡、家庭住址、文化程度、婚姻、家庭收入等,并搜集疾病治療的相關資料,包括病理類型、分期、手術方法。入院時及出院時采用焦慮自評量表[3]、抑郁自評量表[4]、C型行為量表[5]對患者的焦慮、抑郁以及行為特征進行調查。焦慮自評量表共20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分數越高則患者焦慮情況越嚴重,正常:<50分,輕度焦慮:50~59分,中度:60~69分,重度:≥70分。抑郁自評量表共20個項目,采用4級評分法,每個項目的得分相加乘以系數1.25,取整數為標準分。抑郁嚴重程度采用總分/80評價,無抑郁為<0.5,輕度為0.50~0.59,中度為0.60~0.69,重度≥0.7。C型行為量表共有9個項目97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得分越高則患者C型行為特征越明顯。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及方差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干預前后三組焦慮情況比較
干預后,第3組患者焦慮評分顯著低于第2組,第2組顯著低于第1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 干預前后三組抑郁情況比較
干預后,第3組患者抑郁評分顯著低于第2組,第2組顯著低于第1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3 干預前后患者C型行為各維度評價比較
干預后,第2組患者焦慮維度、抑郁維度得分顯著低于第1組,第3組顯著低于第2組(P<0.01);第2組樂觀維度、社會支持維度得分顯著高于第1組,第3組顯著高于第2組(P<0.01或P<0.05)。見表4。
3討論
宮頸癌是女性高發惡性腫瘤,死亡率位第三位。目前宮頸癌的發病具有年輕化的趨勢,隨著篩查技術的發展,早期確診的患者也逐漸增加,為手術治療提供了可能,因此手術比例增加。宮頸癌以及手術對女性患者均為嚴重的負性生活事件。癌癥威脅到患者的生命,而手術治療影響女性的性特征及性生活,對于未生育的女性,甚至喪失生育能力,患者容易產生負性情緒,影響患者的治療。目前社會對宮頸癌的認知不全面,來自社會、家庭的壓力更容易使患者產生悲觀的情緒。圍手術期患者的焦慮和抑郁情緒是突出的心理問題,尤其是術前。研究顯示,術前的心理疏導能夠提高患者的治療依從性,緩解患者的不良情緒[6,7]。術后患者疼痛、并發癥的發生也會增加患者的心理負擔,并且手術使患者失去女性生殖器官,容易產生自卑、悲觀的情緒,患者還會提前導致絕經,均會增加患者的焦慮等情緒[8]。家庭成員罹患癌癥對家屬來說也是嚴重的不良生活事件,加上經濟壓力,同時還要照顧患者,均增加家屬的精神壓力[9,10]。而家屬的負性情緒并不能表露,長期壓抑,甚至會將情緒發泄在患者身上,也會影響患者情緒,不利于順利治療。
C型行為模式是癌癥易感性行為特征,主要特征為童年時形成壓抑、內心痛苦不向外表達、克制的性格,行為特征表現為不自信、過分忍耐、過分合作、害怕面對矛盾、憤怒不向外發泄、屈服于外界的權勢壓抑自己等焦慮、抑郁情緒。C型行為容易焦慮、壓抑、憤怒,這些情緒通過刺激下丘腦激活交感神經,抑制副交感神經,兒茶酚胺釋放增加,作用于免疫細胞,降低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吞噬細胞、NK細胞等數量以及功能;這些情緒還會增加患者腎上腺皮質急速分泌,引起中樞及外周相應的反應,降低患者免疫力,收縮內臟血管,影響代謝功能[11,12]。
認知干預是6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其理論基礎是認為認知過程影響到人的情緒以及行為,是一種定式的、短期的、有結構性的、針對目前心理的治療方法。認知是認識過程、認識活動,包括思維、想象、信念以及信念體系[13,14]。不同的認知產生的情緒不同,對人的行為也具有不同的影響。認知理論認為錯誤的認知和想法會影響到患者的情緒以及行為,通過評價及矯正患者的錯誤認知,改變其認知過程,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緒以及行為。在認知干預過程中,常見的干預技術及心理輔導是重建認知、應付心理、解決問題[15-17]。重建認知的方法是通過識別、分析,從而改變患者的錯誤認知及信念,重建積極的認知模式。通常是先通過交流了解患者情況,然后評估、識別、檢驗患者存在的不良認知以及消極的思維和信念,幫助患者重建積極的認知,改變患者的情緒及行為。
本次研究將認知干預方法應用于宮頸癌癥患者及家屬的干預過程中。給第2組和第3組患者發放《宮頸癌患者健康教育手冊》,給第3組家屬發放《宮頸癌家屬健康教育手冊》。研究者每周組織患者、家屬對健康教育手冊內容進行詳解、分析、答疑,使患者及家屬對宮頸癌以及宮頸癌的治療、預后等有一個全面的認識,為重建患者認知提供理論基礎。入院后通過一對一的面談,了解患者、家屬存在的心理問題,評估患者、家屬的不良認知,幫助家屬、患者建立正確的認知,緩解患者的不良情緒,改善患者的行為特征,分別對患者焦慮、抑郁、C型行為特征進行評價。干預后,第3組患者焦慮、抑郁評分顯著低于第2組,第2組顯著低于第1組,說明干預后,有效緩解了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尤其是家屬同步認知干預的第3組,改善更顯著。研究顯示C型行為特征是癌癥的易患因素。干預后,第3組患者C型行為有了顯著的改善,患者焦慮、抑郁維度得分顯著下降,樂觀維度、社會支持維度均有顯著的改善。
綜上所述,家屬同步認知干預能夠顯著改善宮頸癌手術治療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改善患者的行為特征,有利于患者的預后。
[參考文獻]
[1] 王曉梅. 癌癥患者的心理護理及其健康教育[J]. 中國醫藥指南,2014,12(26):328-329.
[2] 賴銀清. 患者家屬健康教育對晚期癌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J]. 健康導報:醫學版,2014,19(7): 220.
[3] Zung WWK. A rating instru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J]. Psychosomatics,1971,12(6): 371-379.
[4] Zung WWK.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 Arch Gen Psychiatry,1965,12:63-70.
[5] 岳文浩. C型行為模式[J]. 醫學與哲學,1990,11(11):13-15.
[6] 朱伯琴. 心理護理對宮頸癌手術患者配偶焦慮抑郁情緒的影響[J]. 臨床合理用藥雜志,2014,7(28):120-121.
[7] 張意玲,夏曉清,張常樂. 宮頸癌手術患者不同時期心理狀態的調查分析[J]. 護理與康復,2012,11(12):1118-1120.
[8] 馬迪,侯愛和,瞿舒培. 心靈關懷對宮頸癌患者配偶心理應激的影響[J]. 中華現代護理雜志,2013,19(12):1390-1392.
[9] 徐文. 健康宣教對癌癥患者家屬心理壓力和行為的影響[J]. 當代護士:學術版(中旬刊),2014,21(10):132-133.
[10] 賈艷玲,黃俊波,謝靈英. 晚期癌癥患者家屬的病情告知態度探究[J]. 醫學與哲學:臨床決策論壇版,2014, 35(5):47-48.
[11] 汪濤,亓小改,劉孜,等. 宮頸癌患者及家屬C型行為研究[J]. 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4,23(29):3245-3247.
[12] 張波,趙陽,郭丹. 婦科惡性腫瘤住院患者的C型行為模式特征分析[J]. 中國誤診學雜志,2011,11(3):558.
[13] 張穎. 認知行為干預對恢復期住院流浪精神病患者服藥依從性的影響[J]. 中國民康醫學,2014,26(22):117-118.
[14] 肖體友,張秀瓊,馮詠梅. 認知行為干預對初產婦產后負面情緒及社會支持的影響[J]. 海南醫學,2014,25(19):2954-2956.
[15] 吳濤,劉蕾,吳波. 認知心理干預對改善垂體瘤患者內鏡術后生存質量的應用效果評價[J]. 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14,30(15):18-19.
[16] 陸月娥,黎小慧,何韻儀,等. 心理護理對宮頸癌患者焦慮與抑郁狀態的影響[J]. 中國醫藥科學,2013,3(24):143-144.
[17] 卜桂蘭,程媛,曾海芳,等. 心理干預對根治性放療宮頸癌患者的療效影響分析[J]. 當代醫學,2012,18(13):154-155.
(收稿日期:2015-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