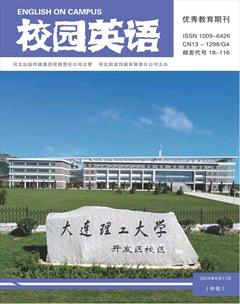從意識形態角度看白睿文的文學翻譯觀
王志敏 閆文軍 劉華
【摘要】意識形態對翻譯有很大的影響。本文借助安德烈·勒菲弗爾的意識形態理論,討論意識形態對白睿文《活著》英譯本的影響,并從社會意識形態和譯者個人意識形態的角度探討白睿文的文學翻譯觀及其形成的原因。
【關鍵詞】意識形態 文學翻譯 文化相對主義
意識形態對翻譯過程有深遠的影響。譯本的成功,不僅僅取決于原作在原文化里的影響,更要取決于譯入語文化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接納程度。翻譯的文化派認為,翻譯活動充斥了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矛盾沖突,而譯作是譯者權衡了各種意識形態和矛盾沖突的結果。他們認為,翻譯活動中,譯者的翻譯策略和選擇都可以從意識形態中找到根源。因此,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探討翻譯,能翻譯研究跳出過去“對等”概念的局限,幫助翻譯研究者更好地認識翻譯現象,解釋翻譯過程和翻譯結果。
一、意識形態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翻譯研究出現重大范式變革,歐洲低地國家和以色列的一批學者從文學接受和文化傳播的角度,以譯文描寫替代原文分析,將翻譯產生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進行系統考察,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翻譯觀和翻譯研究的模式。
在翻譯研究范式的轉變過程中,比利時裔美籍比較文學學者和翻譯理論家Andre Lefevere提出,翻譯是一種改寫,翻譯文學作品要樹立何種形象,主要是由兩種因素決定,這兩種因素是譯者的意識形態(不管是譯者本身認同的還是贊助人強加給他的)和當時在譯語環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詩學觀。從宏觀層面上,意識形態會影響翻譯的目的,翻譯題材,翻譯標準,翻譯策略;從微觀層面上會影響到具體詞語的翻譯。而在論及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時,原文語言和“文化萬象”(universe of discourse) 帶來的各種難題,譯者也會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依據自己的意識形態尋找解決辦法。根據勒菲維爾的這一理論,從莊柔玉對翻譯意識形態的提法,置白睿文于美國21世紀跨文化交際的語境中,來分析他的文學翻譯觀。
二、《活著》及其譯文
《活著》是余華20世紀90年代推出的力作,一出現便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該作品的英文譯本由加洲大學芭芭拉分校東亞系副教授Michael Berry (白睿文)翻譯,于2003年8月由蘭登書屋(Random House)首次出版發行。
《活著》講述了人承受生活的故事。余華在《活著》中,已不聚焦于人們的生存環境現實變遷、以及政治話語所輻射的權威意識形態,而只關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撐人的存在的所有支點,這些支點不只是頹廢的、無望的、帶著世紀末情調絕望的吶喊與顫栗,還擁有濃郁的人文關懷,閃耀著人類引以為豪的生命力。正如詹姆斯·喬伊斯基金會頌獎詞中對余華所作的評價:“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說反映了現代主義的多個側面,它們體現了深刻的人文關懷,并把這種有關人類生存狀態的關懷回歸到最基本最樸實的自然界,……而你,一位中國作家賦予21世紀的生活以道學的精神,由此帶來一種全新的視野。”
在《活著》英譯文中,譯者Michael Berry (白睿文) 在忠實體現原文作者初衷的基礎上折射出原作中的人文關懷。白睿文對《活著》的再現主要體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上他成功的再現了原作中的語言形式,即完整保留了原作的情節,在文本結構上與原作保持一致,并在人物刻畫上與原作相契合。在微觀層面上,白睿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傳達了原作中的中國文化特色。余華說:“這部作品的題目叫《活著》,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佛教也宣揚“苦海無邊”,叫人忍受一切。顯然,《活著》所表現出來的“忍受”精神留下了佛教影響的烙印,但它排斥了宗佛教對世界、對人生的消極態度,剔除了佛教對人精神上的麻醉,張揚了積極樂觀向上的人生觀。從這個意義上說,《活著》具有民族文化象征的功能。在譯文中,白睿文成功的傳譯了中國人的人生觀和生命哲學。而且對于文中特定的文化詞匯的翻譯,白睿文用了直譯加注的方法,沒有加上自己任何的主觀感情色彩。另外原文中的修辭手法,譬如明喻和重復在《活著》英譯本中也得到了忠實的再現。照勒菲弗爾的理論來看,白睿文的這些處理主要是由他所處的社會意識形態和他本身的意識形態兩個因素決定的。
三、意識形態對白睿文文學翻譯的影響
1.文化相對主義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西方學者懷著對種族主義、文化殖民主義的厭惡和對落后國家文化的理解與尊重,建立了“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其中以美國人類學之父弗朗茲·博厄斯為個中翹楚。
繼博厄斯之后,許多文化人類學家都從文化和個性發展的角度闡發了文化相對主義觀點。該理論的核心人物梅爾赫爾斯科維茨認為“文化相對主義的核心是尊重差別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種社會訓練,它強調多種生活方式的價值,這種強調以尋求理解與和諧共處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毀那些與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東西。”簡單點說就是承認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根據這一說法,跨文化研究 (或譯交往)(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就成了文化相對主義的重要內容。
二十一世紀,由于全球信息社會的來臨,各種文化體系的接觸日益頻繁,東西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進行成功的跨文化傳通中不僅要對各種文化差異有較深人的掌握,更重要的是不能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場上,用本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念去評價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判斷或解釋他人的行為就因該依照他群的文化邏輯或文化模式,并以此為標準。在跨文化交流的新世紀,美國人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異域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能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文化相對主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推崇。而且,余華最終所達到的思考深度仍不過是宿命式的東方神秘主義,與西方宗教精神有所不同。但在表現人類共同生命體驗上還是非常到位的。因此余華的作品便具有了足夠的世界性,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讀者。
因此,白睿文在翻譯時,不但要考慮自身所處的時代、所屬的民族、階級的文化背景和作品受眾的需要,還要考慮原作體現的文化、思想、風格和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作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創作意圖,以及譯文可能產生的藝術效果和社會作用等。
2.白睿文個人意識形態的影響。翻譯過程中的多數決定最終由譯者做出。譯者在整個過程中,自始至終受到各種因素,主要是譯語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這并不說明譯者在這個過程中是被動的。恰恰相反,譯者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處于中心能動的地位,譯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對于他對文本處理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活著》的譯者白睿文1974年出生于美國芝加哥,是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也是臺灣留美漢學家哈佛教授王德威的學生,中文造詣極佳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中國(包括港臺海外)文學、華語電影、中國通俗文化和翻譯學。
白睿文的翻譯策略是跨國界的,他的翻譯作品向西方讀者顯示了中國文化的豐富多樣。在翻譯作品的選擇上,白睿文主要基于自己的愛好:“總體來說,我喜歡用開闊的心理來面對翻譯。對作品的選擇最重要的一個標準就是作品是否寫得好,自己是否喜歡。”
1996年,白睿文翻譯了著名作家余華的小說《活著》。中文國際報章星島日報評論白睿文先生不僅中文造詣極深,更難得的是他能準確地抓住并傳遞原作的精神。白睿文在2014年的一次訪談中談到了自己的翻譯主張:“身為譯者,我希望讀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風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個透明人的角色。通過我,原作可以在英語環境中開口說話,來表達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譯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譯得好。如果在譯本中我帶有個人的風格,那我就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成功的譯者。”
翻譯完成后,他聯系了十幾家出版社,都被拒絕。2002年左右,當年拒絕白睿文的世界最大英語商業圖書出版集團蘭登書屋的一位主編卻主動聯系他,想要出版《活著》的英譯本。出版社為了照顧到英美讀者的閱讀習慣,常常要求譯者對譯作進行一定的刪減和改動,舍棄作者某些文學特質,使作品更為美國化,而白睿文對這種要求選擇了說不:“那時編輯寄回給我的譯稿,滿版都是密密麻麻的改動,我覺得他改得有點過了,離原作的意思有點遠,于是我就把那些改動都還原,再寄給他。”
以上對白睿文翻譯《活著》過程的追溯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譯者對原作處理的成因。白睿文的翻譯主張體現了他是個文化相對主義者,他不僅對原作尊重,對中國文化尊重,而且對翻譯工作極為鄭重,這些都能解釋他在譯文中對原作的把握。總而言之,在文化相對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白睿文文化相對主義的個人意識形態決定了其翻譯的行為和結果。在白睿文這里,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操控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是譯者與社會的相互交融產生出了這一翻譯成果。
白睿文的文學翻譯中,他對文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使用體現了意識形態的操控。在當今世界一體化和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中國小說在美國開始有點吃香,但整體來說中美之間的文化失衡還是相當嚴重。白睿文力挽中英翻譯的意譯風尚,以直譯的方式向西方讀者輸入了原質的中國文化,使中外文化交流躍入一個全新的層次,有利于中國文化在西方社會的傳播和了解。同時,白睿文的文學翻譯觀也驗證了意識形態對翻譯行為的操控,譯者既是意識形態的受控者也是意識形態的操控者,在社會意識形態和自身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操控下,譯者還能通過翻譯活動對社會和讀者產生重大影響。從意識形態角度探討翻譯活動,無疑是對翻譯研究的深化和擴充,使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走向了文化的大語境中。
參考文獻:
[1]Berry,Michael.To Live:A Novel[M].New York:Anchor-Random House,2003.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C].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b.
[3]吳赟.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傳播與接受——白睿文訪談錄[J].南方文壇,2014(6):48-53.
[4]蔣曉華.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闡發與新思考[J].中國翻譯, 2003(5).
[5]王友貴.意識形態與2 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1899-1979)[J].中國翻譯,2003(5).
[6]余華.活著(中文版前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