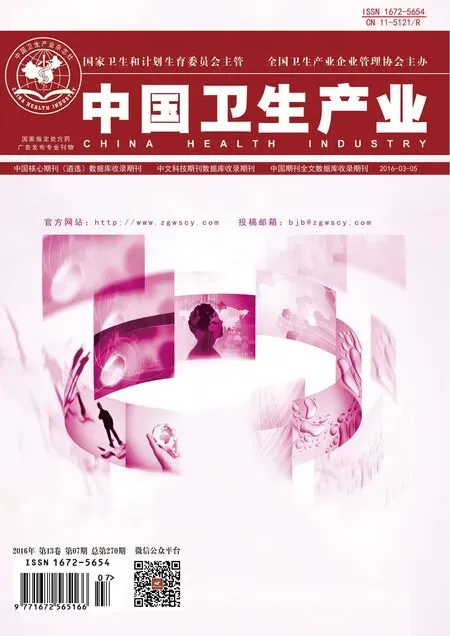護理衛生管理對醫院感染控制的影響
嚴莉湘,章萍廣水市第二人民醫院,湖北隨州 432721
?
護理衛生管理對醫院感染控制的影響
嚴莉湘,章萍
廣水市第二人民醫院,湖北隨州432721
[摘要]目的對護理管理在醫院感染控制方面的作用。方法從該院選擇110名護理人員對其進行護理衛生管理,實行醫院感染控制策略,執行手部衛生控制。結果在進行護理衛生管理之前,醫院的感染率為9.09%;在實行護理衛生管理之后,醫院的感染率為1.81%,前后對比,P=0.00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結論實行護理衛生管理,能夠有效控制醫院感染情況的發生幾率。
[關鍵詞]護理衛生管理;醫院感染控制;作用
醫院感染指的是患者在醫院治療期間獲得的一種內部感染[1]。由于醫院環境的復雜性,在世界范圍內,每年約有200萬人會獲得各種與健康照顧相關的感染并發癥,對患者的預后造成不良影響,而每年因感染死亡的人數也超過了30萬。在醫院感染的種種誘發因素中,護理人員的衛生管理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因素之一。該研究通過研究發現,護理衛生管理能夠有效的控制醫院感染的發生幾率,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從2014年5月—2015年7月,從該院選擇110名護理人員,其中男性10例,女性100例,年齡18~34歲,平均年齡(23.6±2.21)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4.89± 2.12)年。職稱為護士90例,護師10例,主管護師10例。納入標準:直接為患者提供服務的注冊在崗護師;休假人員、實習生、手術室護士和感染科護士排除在外。
1.2方法
①成立感控小組,制定相關管理制度,明確小組人員的各自分工;②加強對護理人員的感染知識培訓,定期組織講座和培訓,主要內容為:消毒隔離、無菌技術、職業安全防護、手衛生規范、醫療廢物分類等,對此110名護理人員進行護理衛生教育和指導,15 min/次,2次/周,以月為周期對其學習效果進行考核,可采取獎懲制度,以調動護理人員的積極性;③加強消毒滅菌的質量控制,確保消毒液的正確、合理使用,嚴格區分清潔區、污染區和無菌區,并做好污染物品的規范放置。完善科室的消毒設備,控制好消毒質量,搶救室和監護室安裝紫外線消毒燈定期消毒,普通病房安裝移動紫外線燈不定時消毒;開窗通風,時間40 min/次,2次/d;物體消毒,對物體表面、墻壁、門窗、桌椅等使用有效氯消毒液進行消毒,其濃度為0.5%。對于床上用品,比如枕套、床單、被單等要使用濃度為0.5%的有效氯溶液進行浸泡消毒,浸泡時間為30 min。保持檢查室內的空氣流通,定期做空氣培養,監測消毒質量;④手消毒:加強手衛生的管理,提高護理人員洗手的依從性,使用流動水對手進行沖洗,在充分浸濕之后,使用肥皂嚴格按照7步洗手法對手進行清洗消毒。科室配備質量合格的洗手液和快速手消毒設備、干手設備;⑤如果在護理的過程中,確認患者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具有傳染性,與其接觸的護理人員必須做好預防消毒措施;⑥合理使用抗感染藥物,包括抗菌藥物、抗真菌藥物、抗麻風病藥物、抗病毒藥物等;⑦護理品消毒。在臨床治療中盡量使用一次性用品,防止交叉感染,對于非一次性用品,例如氧氣濕化瓶、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等物品要嚴格消毒。其中,濕化瓶消毒要使用濃度為0.5%的有效氯消毒液進行浸泡消毒,其時間為30 min/d,之后使用清水進行沖洗,晾干。對于聽診器和血壓計在一次使用之后要使用乙醇進行擦拭消毒,在對表面抗陽性患者使用之后,要使用濃度為0.5%的有效氯消毒液進行擦拭消毒;體溫計要盡量專人專用,在使用之后要使用濃度為0.5%的有效氯消毒液進行浸泡消毒,浸泡時間為30 min,浸泡之后要擦干備用;⑧嚴格實行監測制度。以感染控制條例為基礎,各科室完善消毒監測制度,感染科將環境化分為三個等級,以月為單位進行空氣細菌培養,對室內的空氣細菌落數進行檢測;同時要以月為單位對護理人員的手部細菌和物體表面細菌進行監測;以季度為單位對紫外線消毒燈進行檢測,更換不合格的燈具;⑨加強對醫療廢物的規范化處理,可根據》醫療廢物分類目錄》和》醫療廢物管理條例》為依據,組號醫療廢物的收集和處理、記錄工作,由專人負責處理、管理。
1.3觀察指標
對護理衛生管理之前的醫院感染率進行檢測,對護理衛生管理之后的醫院感感染率進行檢測。
1.4統計方法
使用SPSS18.0對統計數據進行分析,使用t檢驗對計數資料進行檢測,對計量資料進行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在護理管理之前,醫院的感染率為9.09%,在護理管理之后,醫院的感染率為1.81%,P=0.00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具體數據見表1。

表1 護理管理前后醫院感染情況分析[n(%)]
3 討論
醫院感染又叫做院內感染,其含義是在醫療活動中任一人員因受到病原體的侵害而誘發的感染疾病[2]。其表現形式有三種:其一,交叉感染,從醫院其他人員處獲得的感染,比如:兒科收治水痘患者,就可能導致病房中出現水痘傳播。其二,環境感染,指的是環境被感染,進而延伸到人的身上,比如,化膿菌在手術室中存在,接受手術的患者就有可能感染此種細菌進行發病。其三,自身感染,指的是人被自身的感染源感染。比如,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患者,在手術的過程中要與自身腸腔進行接觸,很有可能帶入細菌[3]。當患者的免疫力下降,或者長期使用抗生素就會誘發感染。由此可見,病原微生物的來源有以下幾種:①感染病菌的主要來源是攜帶這種病菌的患者,少數來源是被病菌污染的空氣或者物品,其感染機制是醫護人員與患者間、患者之間的交叉感染;②人體正常的定植菌,在正常的條件下不會誘發感染,但是在被侵犯者身體機能下降的情況下就會誘發感染[4];③宿主體外的微生物儲存,比如被感染的食物或者水等。因此,其特點表現為耐藥性、毒性強、數量多。
醫院是治療疾病的主要場所,也是病原菌聚集的場所,護理人員是與患者接觸最密切的人群,研究顯示,與護理操作不當的醫院感染占30%~40%左右,所以說加強對護理人員的無菌操作技術、消毒隔離技術和感染預防、環境物品的監測工作是護理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直接影響醫院的感染幾率。因此要加強對護理人員的管理,提高感控意識,并掌握相關的知識和技術,保證各項操作的規范化,降低醫院的感染發生幾率。
由此可見,誘發醫院感染的因素有很多,除了護理人員的手之外,還包括物體表面感染、床上物品感染、醫用物品感染等[5]。環境的清潔、消毒和物品的管理和清潔等,帶菌者及患者接觸的環境及物品都有可能成為感染源;護理人員對病人的各種治療和護理操作都是通過手完成的,所以護理人員的手是醫院感染傳播的主要媒介;護理人員工作中缺乏責任心,未按要求對各檢查室、治療室及各使用器械、物品等規范消毒,或將無菌物品與污染物品混放等,導致無菌物品的污染或交叉感染,增加醫院感染的幾率;護理人員的職業暴露主要是因為護理人員自我防護意識差,未能規范洗手或在接受高危人群時未穿戴防護衣等,使病人的血液、體液等經各種渠道進入到機體,引發自身感染;護理工作中的各種有創操作不規范也會導致患者的院內感染,如在行留置尿管時,護理人員未按無菌操作原則執行,可導致患者的尿路感染;臨床中使用的內鏡、新型呼吸機、血液透析機等先進設備,其結構復雜,污染后的管腔應用常規的消毒方法不容易達到滅菌的要求,所以在使用中會引發相應的感染,如呼吸機消毒不達標會導致患者的呼吸道感染。所以在臨床工作中要加強護理管理,規范護理行為,從而有效控制醫院感染。
針對護理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感染因素,可通過加強護理管理制度和加強護理人員培訓、注重工作細節等方面做起。首先要加強護理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制度的制定、執行和反饋三個方面,根據衛生部門要求制定合理可行的護理管理制度,將制度落實到各個科室,由護士長明確分工,執行中做好監督和檢查工作,對出現的不合理或不正確的護理操作應立即改正,不斷完善和不斷改良制度,確保在工作中正常運行。加強對護理人員的培訓工作,注重素質教育,使其在護理工作中遵守醫院的相關消毒隔離制度和強化安全意識,使感染預防觀念貫徹整個護理過程中。做好基礎護理工作,如對醫療器械和物品、環境的清潔和消毒到位;嚴格落實手衛生規范;定期做空氣培養和手培養監測;規范無菌物品的檢查、管理和儲存,需在有效期內使用;如胃鏡、呼吸機等復雜、新型的醫療器械,要由專門經過培訓的人員對其進行清洗消毒對有傳染疾病的病人要做好分類安置工作,原因不明感染、特殊感染的患者要采取單獨隔離,護理人員注意職業防護;加強對患者及家屬的宣教。
因此,控制院內感染也要從上述幾個環節來進行。針對種種感染誘發原因,該研究采取的應對策略為:護理人員使用肥皂對手進行消毒;護理人員使用濃度為0.5%的有效氯溶液對床上用品進行浸泡消毒,對物體表面進行擦拭消毒;護理人員使用紫外線消毒燈進行室內消毒,通過定時通風進行室內消毒;醫院嚴格執行護理人員的教育與培訓,以提高護理人員對護理衛生管理的認知;通過嚴格執行監測制度,以提升護理管理的應用效果。研究結果表明,在護理衛生管理之前,醫院的感染率為9.09%;在護理衛生管理之后,醫院的感染率為1.81%,兩者對比,P=0.00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隨著社會和醫療衛生事業的不斷發展,臨床中對病人的診治及各項有創性操作大大增加,醫院感染的幾率一直居高不下。患者的院內感染不但影響初始疾病的治療,還會增加患者住院的時間和醫療費用支出,為患者及家庭帶來經濟負擔,感染嚴重可危及生命安全。同時也增加了醫患之間的矛盾,導致醫療糾紛等負面影響。所以加強醫院的感染控制可直接影響醫院的整個感染管理質量和水平。
綜上所述,醫院通過開展護理人員知識培訓和加強無菌操作技術和消毒隔離等護理衛生管理能夠有效的控制醫院感染,降低醫院感染的發生率,提高醫院治療的護理質量和水平,所以該護理管理制度具有臨床推廣價值。
[參考文獻]
[1]王洪芹.護理人員手部衛生的干預與預防對控制醫院感染的作用[J].國際護理學雜志,2013,32(8)﹕1829-1831.
[2]徐偉.我國基層衛生院護理現狀與對策[J].醫學信息,2013,9(14)﹕34.
[3]朱潔,吳月鳳,來娟,等.持續質量管理在護理人員手衛生管理中的應用[J].醫藥前沿,2013,12(26)﹕59-60.
[4]蔡林,張可,溫泉,等.護理人員手部衛生與干預對策的研究進展[J].解放軍護理雜志,2011,28(17)﹕45-47.
[5]陳發成.加強護理安全管理對提高鄉鎮基層衛生院護理質量的效果[J].數理醫藥學雜志,2012,25(2)﹕234-236.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YAN Li-xiang,ZHANG Ping
Guangshui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Suizhou,Hubei Province,43272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the role of the nursing management in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Methods Choose 110 nurses from our health care management,implementation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strategy,perform hand hygiene control.Results Before the health care management,the hospital infection rate was 9.09%;After the health care management,hospital infection rate was 1.81%,before and after contrast,P<0.05,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Conclusion The health care management,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risk of hospital infection status.
[Key words]Nursing health management;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Role
[中圖分類號]R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654(2016)03(a)-0164-03
DOI:10.16659/j.cnki.1672-5654.2016.07.164
[作者簡介]嚴莉湘(1976.10-),湖北隨州人,本科,主管護師,主要從事護理管理工作。
收稿日期:(2015-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