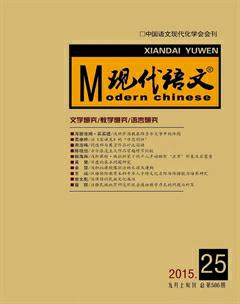立足新課標解讀《顏氏家訓·文章》的作文教學思想
摘 要:《顏氏家訓·文章》集中闡述了顏之推的作文教學理論,本文根據2011年教育部頒布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中有關作文教學要求的描述,從創作主體(嚴謹為文、天賦至上),學習方法(明辨文體、修辭為輔、心懷讀者)和評價標準(地域差異、字樸句實)三個方面來解讀、學習《文章》中值得我們辯證吸收的作文教學精髓部分,以期古為今用,以史為鑒。
關鍵詞:顏氏家訓 文章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 作文教學
《顏氏家訓》是封建士大夫階層訓誡子孫的家教范本。雖受時代限制,《家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帶有忠君色彩的封建落后思想,但其包含的作文教學理論在新課標實施的今天仍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值得被繼承和發展。
一、創作主體:嚴謹為文,天賦至上
寫作在理論研究中常被看作一種實踐活動,“由主體、客體、載體、受體四個部分組成,缺一不可”[1]。寫作主體是指在寫作過程中創造文章的主體,寫作主體的精神氣質和人格品位必然會對寫作產生重要的影響。
《文章》認為寫作主體必須具備嚴謹為文和明哲保身的意識,若恃才自傲,就會得到不好的命運。“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2]若過分夸耀自己作品的言辭精妙,甚至在文章中諷刺別人,就會招來禍患。事實上顏氏之所以對寫作主體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有其時代背景的:顏之推生于亂世,“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3],飽經戰禍之苦的他深知生存的艱難,自然會擔心子孫后代因文章遭遇不測。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以下簡稱“新課標”)也是提倡嚴謹為文的。首先,“嚴謹為文”始于語文思維模式的培養。新課標要求“在發展語言能力的同時,發展思維能力,學習科學的思想方法”[4]。要“寫”得嚴謹,首先就要“想”得嚴謹。其次,“嚴謹為文”具體表現為行文準確,思想健康。這一點與當下的作文評價標準相吻合。與新課標配套的《2014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大綱的說明》就要求學生的作文要“符合題意,符合文體要求,感情真摯,思想健康,內容充實,中心明確,語言通順,結構完整,標點正確,不寫錯別字”。這就說明,寫作不得隨意,行文要嚴謹,要講究基本的規則。
明哲保身的思想不適用于現代的寫作教學。課程改革后的作文教學是為了引導學生合理地表達自我:“要求學生說真話、實話、心里話,不說假話、空話、套話,并且抵制抄襲行為。”[5]一味地規避矛盾也不利于學生的人格發展。
《文章》還強調寫作主體的天賦是寫作的前提。顏之推認為做學問的人有聰明和遲鈍之分,他們寫的文章也有精巧和拙劣之分。“駑學累功,不妨精孰,拙文研思,終歸蚩鄙。”[6]缺乏天分之人,不必勉強去寫文章。這種觀點在當時文壇上是很流行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也表明寫作需要特殊的天賦才能,這就是“氣”:“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7]。天賦至上的寫作主體觀是由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所決定的。當時的人才選拔依據是門第,“士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權和優先選官的特權”[8]。不同于后世寒門學子尚有科考為官的希望,南北朝時期,文章的好壞并不能直接改變讀書人的命運。若無天賦,專攻他法謀生也是不錯的選擇。
天賦至上論并不適合現代作文教學。因為現代作文教學的目標是:“能具體明確、文從字順地表達自己的見聞、體驗和想法。”[9]。現代的教育理念是培養人的能力,發展人的綜合素質。教師應當本著教育公平的原則,既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學生,又應當重視學生的特質,因材施教。
雖說顏之推的寫作主體觀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文章》所倡導的寫作主體應該主動學習主流道德,提高修養,增長學識,做到高瞻遠矚,心懷天下的思想傾向,是符合現代寫作觀對于寫作主體的要求的。新課標在課程的實施建議中反復強調寫作是交流和表達的方式,是認識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因此,教師應當在寫作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思考力和創造力,以此擴展學生認識世界以及認識自我的途徑。在此過程中,教師更應重視培養學生的道德修養。
總之,我們要辯證吸收《顏氏家訓》中的寫作主體觀。
二、寫作方法:明辨文體,修辭為輔,心懷讀者
《文章》的寫作方法觀涉及文體意識、文辭修飾以及寫作主體的讀者意識。
首先,顏之推擁有清晰的文體意識。他認為文章分類始于《五經》,后世的詔命策檄,序述論議,歌詠賦頌,祭祀哀誄,書奏箴銘等都是由《五經》演變來的。《文章》把文章分為兩類,即立足于實用的“朝廷憲章”“軍旅誓誥”和立足于審美的其他文本。顏之推重視前者,因為前者能“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10]。據《勉學》分析,當時社會風氣不佳,作為官吏主要來源的貴族子弟不學無術,他們檐車隱囊,生活奢侈,一旦親族倒臺,就徹底成了廢物。而有“藝”者,可以憑自身技藝在亂世里安身立命。因此,顏之推鼓勵讀書人將讀書看作一門可以謀生的技藝。《涉務》中也提到學習和社會生活脫節的現象。因此,《文章》強調實用是為了迎合時代發展的趨勢,而在寫作前辨明文體,則是為了更好地學習寫作。
現代作文教學經歷過一個“淡化文體”的階段,批判教材開啟了“淡化文體”之門。20世紀80年代的高中教材就以文體組元。到了90年代后期,這套教材遭受了強烈的社會批評。因為這種做法雖有利于訓練學生的基本寫作技能,但有過分重視文章技能,扭曲作文教學的本質之嫌。過度重視行不通,那么只有“淡化”。1988年的高考作文就提出了“文體不限”,而后出現的“話題作文”更是解除了“文體”對學生作文的限制。于是,越來越多的“四不像”作文出現了。所以從長遠角度看,“淡化文體”不利于學生學習寫作。當代的作文文體觀是“淡化文體”,而不是“淡化文體意識”,基本的文體意識必須貫穿在寫作的主題、題材、構思、語言中。“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應用文,是為了便于教學對文體所做的分類,而不是具體的文體”[11]。結合《文章》的經驗,教師應當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需要,逐步培養學生的文體觀念。只有在學生寫作前教會他們明確文體,學生才能更好地表達自我,與人交流。從“新材料作文”的流行趨勢來看,文體意識的培養也有利于學生更好地提高學習效率,應對考試。
在文辭修飾方面,《文章》歸納了“皮膚冠冕”說和“古今本末”說。“皮膚冠冕”說是指文章以義理為心腎,以氣韻為骨,這些是文章的內在部分;典故和華麗的語言則是文章的皮膚和冠冕,這些是文章的外在部分。“古今本末”說是指“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12]。顏之推認為寫作時,古人的體制格調和今人文辭音調都要學習,不可以有所偏頗。顏氏反對當時文章的浮艷之風,但重典故詞藻的浮艷文風已成“時俗”,不可能輕易地被廢除。況且當時文章有音律和諧、章句對偶、避諱得宜的長處;古人文章雖在遣詞造句方面體現出了簡約質樸的風格,但失之嚴密細致。于是顏之推兼取古今文章之優點,作“本末之說”。
新課標的亮點之一就是將寫作教學的要求分段歸納為“寫話”(一、二年級),“習作”(三年級)和 “作文”(初中),這是為了“反對部分學校教學中大搞‘提前量的做法。寫話是“寫心中的話,寫想說的話”[13];習作強調的是語言素材的積累以及書信交流能力的提高;到了作文部分,寫作才強調語言表達的豐富性。新課標的寫作訓練,鼓勵學生逐步提高。這,給了教師兩點啟示:其一,在不同的寫作階段引導學生借鑒合適的范文,可以使學生取長補短,樂于嘗試;其二,選擇范文時應借古鑒今,不得私美。
“讀者意識”是一個文藝界的經典命題。“接受美學”認為文學批評應該指向讀者,朱自清先生也曾表示寫作練習可以沒有假想的老師,但不可以沒有假想的讀者。而現代語文教育中對于寫作的定位是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生活需要的寫作能力。因此,只有在寫作前先明確文章的讀者群,才能寫出符合實際需要的文章。
《文章》的讀者觀念是“心懷讀者”:“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師心自通,取笑旁人也。”[14]寫作時,先與讀者交流,充分考慮他們的閱讀心理、審美習慣和認知水平,然后動筆,可謂善矣。“先謀親友”更體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作文訓練不應當只局限在學校,更應當重視課外。家庭環境與光怪陸離的社會環境相比,更傾向于為生活經驗不太豐富的學生提供較為健康的、較易獲得的教育資源。在“寫話”和“習作”階段,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將自己的文章和家人分享,這樣既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也有利于增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在“作文”階段,教師應該提醒家長與學生保持交流,這樣可以及時發現學生作文中的不良思想傾向,也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配合得更為密切,共同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三、評價標準:地域差異,字樸句實
寫作評價是寫作學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顏氏對這個問題提出了頗具新意的看法,即文章的鑒賞風格和方式具有地域性差異。字樸句實是顏之推推崇的審美方式。
寫作評價具有地域差異是習慣使然,也是政治使然。首先,是否接受他人意見的評價觀就具有地域差異。“江南文制,欲人彈射……山東風俗,不通擊難”[15],江南地區的人寫了文章后,希望得到別人的批評,會主動修正文章中錯謬之處,而山東地區的人則不然,這也佐證了“嚴謹為文”的重要性。其次,南北文壇的審美觀并不同。《文章》中記載了“蟬躁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例子。南朝文人十分贊賞這句詩,甚至認為沒有比這更好的了;而北朝才俊卻認為這根本不能被稱作詩。事實上,輕視北朝文學是帶有政治色彩的必然趨勢。在《洛陽伽藍記》中,陳慶之醉后吐露了輕視北朝文學之語,蓋“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御璽,今在梁朝。”[16]政局不穩,兼之文人的地域流動性,南北文章之正統之爭、高下之較存在著極大的主觀色彩,實在難有定論。
新課標關于寫作評價的審美差異提出了三個解決方法。首先,正視創作主體的地域差異,作文課要自我調節。“要盡可能滿足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不同學生的需求……不斷地自我調節、更新發展”[17];其次,關注因個體差異而引發的學習需求差異,努力開發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學方式;最后,應該設立多樣化的評價標準,“為學生的自主寫作提供有利條件和廣闊空間,減少對學生寫作的束縛,鼓勵自由表達和有創意的表達”[18]。課程標準的改革通過不斷自我調整以促進教學,順應時代發展,而新課標更在固有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設想。
文章評價標準雖有地域差異,但《家訓》所認可的審美標準是固定的,即沈約的“三易”說:“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好文章,用典要明朗,不過度使用生僻華麗的字詞,注意節奏和平仄的搭配。《文章》在用典方面補充了“三易”說:首先,用典要用合適的典故,不能用錯典故。諸如“破鏡賦”“敬同”“恒山之鳥”之類的例子,若使用不當,會使得整個文章顯得可笑。其次,用典還不能背離文章的文脈,切勿善惡通篇。如《齊謳篇》前半部主寫山川秀美,民風淳樸,后半篇卻用典來鄙薄山川,這使文章文脈不順。而追求文章音韻之美,對于作文學習的初學者來說,要求過高,沈約的“四聲八病”說也曾為人詬病。所以,現代的作文教學應強調句子的通順,反對矯揉造作。新課標的作文教學的目標之一是鼓勵學生在學習寫作時寫真話,寫實話,寫心里話,因此,在現今的作文教學中有必要回溯古人的“三易”之法,使作文教學真正地為培養學生能力、提高語文素養服務。
《顏氏家訓》是一部具有教育意義的專著。除了上述歸納的方法,《家訓》還提出了其他可供借鑒的教學原則。比如“博專結合”,教師既要鼓勵學生閱讀與課程有關的專業書籍,又要廣泛地閱讀對學習有幫助的其他書籍,以積累更多的作文素材;比如學生學習的態度要謙虛,學習的動機要純正,不然就是“為學自損,不如不學”,寫作更是如此;比如教師要引導學生做到“勤學”和“博思”相結合,既要刻苦學習,又能對學習的內容和方法有所反思,這樣才能提高作文學習的效率。這些教學原則都是古人讀書治學的優秀經驗,教師應當在實踐中用好這些方法,以促進教學。
注釋:
[1]鄔乾湖:《當代寫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2]檀作文譯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1頁。
[3]檀作文譯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0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
[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6]檀作文譯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8頁。
[7]李道榮:《中國古代寫作學概論》,鄭州:文心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
[8]孫培青,杜成憲:《中國教育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頁。
[9]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10]檀作文譯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1頁。
[11]曾祥芹:《曾祥芹文選》(上卷),《實用文章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頁。
[12]檀作文譯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5頁。
[1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14]檀作文譯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9頁。
[15]檀作文譯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9頁。
[16]曹虹今譯,王伊同英譯,[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44頁。
[1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
[18]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汪澄 江蘇蘇州 蘇州大學文學院 2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