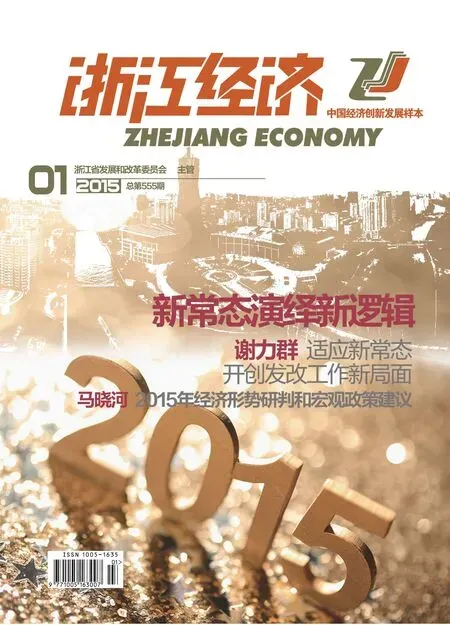適應新常態的“批判性思維”
劉亭
適應新常態的“批判性思維”
劉亭
自去年5月習總書記首提新常態概念以來,中經APEK會議對外宣示,至歲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加以長篇系統闡述,新常態理論漸顯雛形。
何以認識新常態?舉一個剛剛遇到的例子來說明問題。某咨詢機構要做一個有關浙江農民持續增收的課題研究。2014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預計為19400元,至此浙江省已連續30年農民收入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這當然是一段光榮的歷史。分析起來,經驗多多,但其中有幾條還是蠻有點特色的:一是率先推出農村工業化,泥腿子上岸辦企業,先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后經改制民營經濟蓬勃發展,果然應了“無工不富”的那句話,無論是做老板還是當打工仔,票子都“大大地多了”。二是率先推出糧食購銷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由此效益農業也就有了粉墨登場的舞臺。“什么來錢就種什么”——大有點離經叛道的意思,但卻是當時搞活農業生產的一大思想解放。三是率先推出“農家樂”,隨之而來的是生態旅游遍地開花。農村的綠水青山、瓜果時蔬、民俗風情、人文鄉愁、閑適散淡,都成了農民轉戰服務業新戰場的資本,大可以就地生財、坐收漁利。
但是,進入新常態了以后,再促進農民的增收會出現什么新情況呢?我看起碼有三條不可小覷:一是隨著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推開,戶籍制度改革深化,城鄉都要統一為居民戶籍了,那今后你只能實事求是地將真正是在“土里刨食”的純農業人口,記為你要研究的“農民”,再也不能魚目混珠、張冠李戴了。戶籍這張“皮”變了,附在這張皮上的“毛”焉能不變?二是隨著農業生產條件的不斷變化,過往30年大行其道的承包制的正面效應正在“邊際效益遞減”。高度細碎、經常微調、“3860(婦女和老人)”部隊為主耕作的承包地,顯然已難以搭上規模經營、服務配套的現代農業“快車”。承包經營權的自由順暢流轉,成為規模經營和家庭農場興起的必要條件。三是隨著城鄉一體化發展步伐加快,二元結構體制松動,城鄉之間人口的自由遷徙將成為常態,即所謂“讓愿意進城的農民進城,讓愿意下鄉的市民下鄉”。但農民進城要有本錢,買不起房、定不了居算什么進城,又算什么市民化?從這批“農業轉移人口”來看,不把他們原先在農村的“三塊地”——承包地、宅基地、人均一份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上的土地權益能夠量化到個人,并且通過規范的要素市場交易完成價值化、貨幣化和資本化,那“人的城市化”其實是“化不起來的”,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是不會有明顯增加的。
所以,考慮到這種種的“新常態”,今后農民增收的路子,還能夠僅僅只是拘泥于傳統的那幾條嗎?顯然不行了。這就需要“反彈琵琶,功夫在詩外”,由“發展出題目”,讓“改革做文章”。譬如,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削減(純)農民基數。或如當年力推浙江實施城市化戰略的張德江書記所言:“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這一來二往的人口變動,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上,也一定會導致顯著縮小的結果。再譬如,推進農村產權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讓市場對農村的土地資源配置更充分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讓農民得以獲取更多的財產性收入。光有政府對農民的“確權”是遠遠不夠的,關鍵還是能否在市場流轉中“活權”,讓沉睡在兩元結構體之下農村和農民“死的權利”,悄然變身為“活的收益”。有了獲利的機會,才會引來工商資本的投入,也才會進一步引來人力資本的注入,從而造就真正的現代農業。
說到這里,如何適應新常態,首先要從對舊常態“批判性的思維”做起。盡管改革開放的30年(大數)成績驕人,碩果累累,但無可否認,極大程度上那也是以物本主義的高速增長、平面擴張為價值取向和現實表征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做的完全正確。但是到了今天,時勢變了,常態改了,再不與時俱進、改弦更張,再不另辟蹊徑、別開生面,那明天和后天就一定會犯錯!上一輪的改革開放是怎么搞起來的?是靠真理標準大討論重新恢復的實事求是。這一輪新常態下的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再怎么搞起來?還得借助于“批判性思維”帶來的更上層樓的實事求是!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學術委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