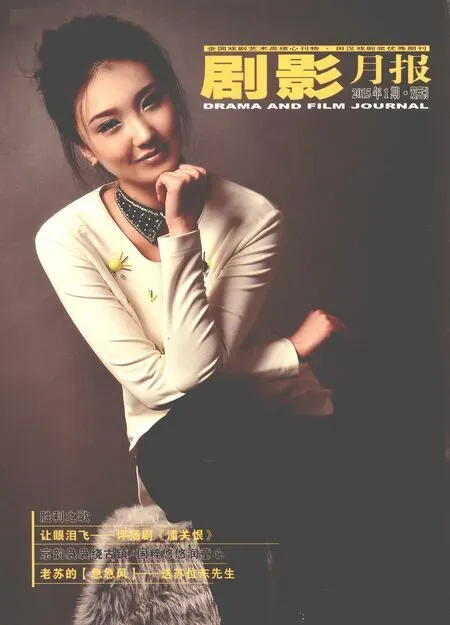民營揚劇團再登高丘
■唐云
民營揚劇團再登高丘
■唐云
黨的十七大后,“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繁榮城鄉基層文化市場的生力軍”的論斷越來越深入人心,文化部先后出臺了《關于構建合理演出市場供應體系,促進演出市場發展繁榮的若干意見》、《關于促進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有關扶持發展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文件。而揚州,早在80年代,民營揚劇團體就已經初現端倪,并且不斷茁壯成長,至今方興未艾。
只見鴻雁騰了空:脫穎而出
說起民營揚劇團,首先要從公辦揚劇團說起。1981年,揚劇事業百廢待興,這一年的9月,揚州市揚劇團實行了兩個演出隊分隊核算。1983年,揚州揚組建了兩個承辦責任制演出隊,當年實現演出870場。這次成功的改革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無疾而終,但這種靈活的機制以及由此帶來的效益,卻對揚州民營劇團的萌芽與崛起影響深遠。
80年代,揚州市先后有一些文化館、文化站成立了揚劇團,這些劇團雖然是由“公辦”,但自負盈虧,實際上是“私營”。終于,在1990年,完全民營性質的聯誼揚劇團脫穎而出。作為揚州第一家民營劇團,除了寒暑季節休息外,該團常年堅持演出,演出劇目主要有《白蛇傳》、《秦香蓮》、《恩仇記》、《珍珠塔》等一批傳統“大戲”,揚州市民營揚劇團體發出的第一聲就是那樣的洪亮與字正腔圓。1996年,已經退休的揚劇演員汪琴組建了“汪琴藝術團”。此后,揚子江揚劇團、德才揚劇團、海派揚劇團、紅霞揚劇團……數十家揚劇團如雨后春筍般紛紛破殼而出。
汪琴藝術團成立于1996年秋,是揚劇表演藝術家汪琴個人獨資的民營揚劇團——1983年,她便是揚州市揚劇團兩個獨立核算演出隊的承包人之一。毋庸諱言,90年代是改革開放之后揚州揚劇最艱難的一段時期,這一時期,揚劇的龍頭老大“揚州揚”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而一些縣級劇團更是舉步維艱,大量人才流失,一些縣級劇團甚至解散或保留建制。而民營劇團卻應時而出,大放異彩。姚恭林、金桂芬、陳惠泉、李造林、張小童等一批揚劇名宿紛紛成為汪琴藝術團的合作者,很多離開公辦劇團但依然懷著一顆“揚劇心”的青年演員,也在這里開始了新的追夢之旅。到了2002年,汪琴藝術團排演的《好人高仁林》參加了第三屆江蘇省揚劇藝術節,并獲得近十項獎項,這是民營揚劇團體首度參加政府舉辦的藝術節活動。三年后,汪琴藝術團又被中宣部、文化部評為“全國服務農民基層文化工作先進集體”。
揚子江揚劇團的發起人王俊也是揚州揚出身,但揚子江揚劇團卻代表著民營揚劇團的另一種模式,她掛靠于揚子江音像公司,與其他民營劇團白手起家不同的是,她一開始就具有相當的實力,并具有較為成熟的企業化管理經驗。汪琴藝術團的很多演員與劇團并無隸屬關系,往往來去自由,揚子江揚劇團與演員簽訂了合同,保證了較為固定的演出團隊。
2001年,高郵市揚劇團進行了公有民營、公退民進的改革探索,首輪由李正太承包、二輪由張愛華承包,這也成為民營揚劇團較為獨特的一種形式。李正太在第一輪承包結束后,于2003年自行組建了高郵市正太揚劇團,并于張愛華承包結束后,再次“帶團”承包高郵市揚劇團。
到如今,揚州市比較活躍、規范的民營揚劇團體有十余家,若再加上一些隊伍不夠穩定、演出不夠正常的民營揚劇組織,揚州有近百家民營劇團團體,從業人員有萬人之眾。在推動揚州建設文化大市、文化名城的進程中,民營揚劇團成為一支重要力量。據揚州有關部門統計,揚州全年整臺的戲曲演出有近5000場,其數據大部分是由民營劇團貢獻的。
手扶胸膛細思量:盛世危言
揚州民營揚劇團體在揚劇發展的低谷期應時而出,為當時的揚劇發展的“灰暗期”增添了一抹亮色。新世紀之后,百年揚劇迎來了復興,民營揚劇團體更是如魚得水,好戲連臺,現在,在揚州的城市鄉村,到處可見民營揚劇團演出的俏麗身影,到處可聞民營揚劇團演出的悠揚曲調,民營揚劇團進入了歷史最繁榮的時期。但“手扶胸膛細思量”,我們依然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繁榮”的背后,也已有衰態。
演出隊伍難以為繼。客觀地說,民營揚劇團之所以在上世紀90年代“逆勢而生”,很大程度上受公辦劇團不景氣所“賜”。除了因為公辦劇團演出減少給民營劇團帶來的巨大市場空白外,更關鍵的是,公辦劇團培養的專業演員大量進入民營劇團。可以這樣說,目前揚州影響較大的民營揚劇團,其臺柱子都是過去公辦揚劇團的骨干演員。如前述的高郵市正太揚劇團,其演員主要來自高郵市揚劇團、江都市揚劇團的離退休演員和離職演員,以及被撤銷的原天長縣揚劇團、姜堰市揚劇團、鎮江市揚劇團的分流人員。即便是2013年新成立的秦淮揚劇團,其相當部分的演員還是來自原公辦劇團。這帶來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演員年齡結構的老化,60歲的“妙齡”小姐、滿頭白發的“少年”書生、身體發福的“俏麗”妹子,在民營劇團演出的舞臺上局見不鮮,一定程度上已經影響到觀眾的欣賞。而隨著公辦揚劇團體的復興,優秀演員已難以進入民營團體。
演出質量良莠不齊。近年來,揚州市民營揚劇團體屢屢亮相省、市藝術展演活動,并每有斬獲,但客觀地說,演出質量還是不容樂觀。一方面,具備一定實力參加省市調演的民營劇團數量較少,以每三年一屆的揚州市專業劇團新作調演為例,幾乎每次參演的民營劇團都是那幾張老面孔。另一方面,民營劇團所得獎項含金量并不算太高,所得的多是劇目獎、演出獎(一等獎為優秀劇目獎),一等獎往往是演員個人的優秀表演獎。造成演出質量良莠不齊的主要原因是演員自身技藝不高,大部分民營劇團除了幾個主演外,其一般演員往往還處于業余水準。而另一個原因則是精品意識的普遍缺失。“創精品=公辦劇團,走市場=民營劇團”的觀念在民營劇團的經營者中占據主流。由于民營劇團普遍沒有“舞臺監督”、“藝術監督”這一設置,演出中演員對演出質量普遍不重視,有時甚至為了迎合觀眾而進行較為低俗的演出。
新創劇目少之又少。翻看民營劇團的演出戲單,映入眼簾的大部分是傳統劇目,這除了觀眾選擇的因素外,主要還是因為大部分民營劇團很少主動新創劇目。民營劇團劇目主要是照搬公辦揚劇團體劇目與移植兄弟劇種劇目,所謂移植幾乎是照搬劇情、道白、唱詞,只是將唱腔改用揚劇唱腔。而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移植劇目是劇團的老演員先看錄像,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用揚劇曲牌唱出,教給青年演員,不僅沒有專業編劇,有時也不請專業導演、作曲。民營揚劇團不進行劇目創作一方面是因為創作成本較高,公辦劇團一臺劇目動輒百萬的成本,讓民營劇團望而卻步;另一方面則是風險較大,公辦劇團由于有政府的扶持,具備較強的抗風險能力,而民營劇團則不具備這一能力,新創劇目能否得到市場認可,他們不敢打這個包票,更不敢冒這個風險;第三方面則是意識問題,在傳統劇目已經能基本滿足市場需求的情況下,民營劇團也就懶得進行創作,正如前文說述,他們認為創精品是公辦劇團的事情,與自己無關。
演出市場令人擔憂。表面上看,揚州民營劇團演出市場一派紅火,但如果認真分析一番的話,揚劇的演出市場存在著買方與賣方的嚴重脫節。具體的說,真正觀眾買票的不多,多為企業慶典、婚喪嫁娶的堂會式演出,觀眾不看白不看,劇團與觀眾不是市場的買賣雙方,一旦第三方的興趣發生改變,比如看電影成為紅白喜事新的時髦,民營劇團脆弱的演出市場必然受到致命打擊。正如有專家所擔憂的那樣,這一繁榮究竟能維持多久?這一繁榮會不會成為“回光返照”。
水鄉三月風光好:新生與展望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民營揚劇團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亮點。一是部分民營揚劇團開始注重新人的培養,如揚子江揚劇團先后從揚州文化藝術學校的揚劇團招聘了幾名揚劇學員,正太揚劇團培養的李華俊等青年演員已經開始挑大梁,德才揚劇團2014年甚至在揚州文化藝術學校開辦了委培班。二是民營揚劇團對演出質量越來越重視,省、市舉辦的新作調演對于民營劇團提升演出質量是一次重要的契機與刺激,很多民營團不僅在移植劇目時邀請專業的導演、作曲,乃至舞美、服裝參與,而且還邀請專家指導評論,甚至,部分民營劇團開始新創劇目,如正太揚劇團先后創作了《生死秘賬》、《淮海悲歌》,汪琴藝術團先后創作了《好人高仁林》、《地平線下的彩霞》,由邗江區文化館建立的祝榮娟藝術團先后創作了《心碑》、《蘆花白》、《心路》等。三是演出力量的加強,很多民營團經濟實力不斷提高,不僅配備了越來越正規的演出器材、道具,有的劇團具備了固定的、具有較高檔次的辦公、演出與排練場次。筆者以為,要促進揚州民營揚劇團的發展,讓民營揚劇團在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必須多方協力。
一是政府的重視與扶持、指導與引導。2009年文化部出臺 《關于促進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的若干意見》,很多省、市也出臺了配套政策,例如蘇州市出臺了《蘇州市支持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獎勵辦法》。揚州市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門歷來重視民營劇團發展,如每次舉行的藝術調演活動都將民營劇團納入其中,揚州市文化局舉行的藝術工作會議也往往邀請民營劇團代表參加。但目前,揚州市對扶持民營劇團發展還沒有系統的政府與辦法,例如民營劇團在豐富農民文化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政府卻幾乎沒有扶持;再如政府在劇目創作扶持中,很少扶持民營劇團,曾受到扶持的正太揚劇團、祝榮娟藝術團都具有一定的“公辦”色彩。今后,是否可以學習美國、日本的經驗,淡化公辦與民營的區別,而以項目制的形式來扶持劇團、劇目?而如何規范民營劇團演出,如何使之成為繁榮舞臺藝術的重要力量,這也需要政府進行指導與引導。
二是民營劇團自身觀念的轉變與認識的提高。在中國的文藝演出歷史上,民營劇團一直是主流,實際上,1949年后建立的各類公辦劇團,其人員基本上來自民營劇團。現在,民營劇團的發展當然不是回到過去,而是進行新的發展。民營劇團的演出不能僅僅是為了盈利,或者僅僅是因為愛好,我們要在繁榮舞臺藝術的進程中以更主動、更積極的姿態出現,發出更響亮的聲音。近年來,歷屆的春晚上,我們都能看到民營劇團靚麗的身影,他們的演出質量已經不弱于公辦劇團,這是揚州民營揚劇團的榜樣。
民營揚劇團大有可為!
——以揚劇為例